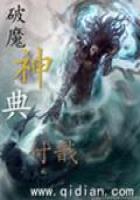一日之间,刘振南便已经将刘振东的尸首运回汴京,刘振东之死在彻夜之间已经飞骑回家报信。老夫人听说之后一病不起,在床上听到消息,一阵惊吓昏死过去,宅中所有老少彻夜痛哭,哀嚎之声彻夜不断。次日清晨管家便差人去购买了大量的白灵麻孝,清香白烛,跑前跑后,忙里忙外,把家里收拾的是妥妥当当。
刘振南用马车拉着灵柩,上面撑起一白色大车棚。四周披满白灵,中间黝黑发亮的棺材,棺木正面写着一个大大的“奠”子,上面一朵脸盆般大小的白花,连着白灵搭在棺材正前头。带头的正是刘振南,头戴白灵,马披白孝,前前后后的人个个戴孝,手持哭丧棒。灵柩周围的人都一手扶着棺木,一手拉着袖子在脸上拭泪。前前后后几十个人一路啼哭,在路上收人也越来越多,大多都是前来吊丧的,都是刘振东的亲朋好友,在落上大多都是头戴三尺白灵,结成了上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的长队。
到了马帮大院,刘振南把棺木停在大门正前方,家里所有的人都已站在大门前等候,扶老携幼。此时刘振东的夫人与刘振南的夫人扶着老夫人才赶出来,老夫人已是颤颤抖抖面如土黄,众人看着老夫人出来,无人不感叹。周围的人看了更是伤心,哭的愈发的悲痛。刘振南赶紧上前跪拜道:“大娘,小儿无能,不曾保护好大哥,才让大哥遭此横厄,恳请母亲大人责罚。”说完便拜扣在地上。
老夫人颤颤巍巍的下了台阶,两位夫人搀着老夫人,下了台阶。老夫人下来去扶起刘振南。一手拄着拐杖用右手弯下腰去扶刘振南,老夫人看着刘振南道:“起来吧!这也不是你的错,你哥哥武已精湛都被杀害,何况是你啊!以后这家业还得由你来照看,快快起来,你也是两天没合眼了,可别跪坏了身子。”说完便立即扶起了刘振南,一群人抬着棺材进了宅院。
所有人都进了大院,把棺木摆放在正堂大厅,管家已经把所有的一切安排妥当,前来的亲朋好友都来吊丧。刘振南命手写的人打开棺木,让家里所有的人都再看刘振东一眼,另外请来开封府衙内的仵作前来验尸。老夫人看到刘振东的尸体痛心疾首,便有当场晕死过去了。众人齐声叫喊也不见醒来,刘振南抱住老夫人掐住人中,也不见醒来。便马上叫人去请郎中,先把老夫人抬了下去。周围的人慌慌张张不知怎的是好,都是痛哭流涕。
正在慌乱之中府衙之内仵作前来验尸,那仵作看了看身上各部,只有脖子上有一条伤痕,仵作用酒水擦拭了伤口,看了看深度和刀迹,不觉得惊异。擦拭完发现这刀痕犹如丝线一般,伤口内部血肉平整,伤口深两寸有余,彻底切断了喉咙和和气管,连同脖子两边的两条大动脉全部割断。那仵作验完对刘振南说:“二公子,这是一武艺高强人所谓啊!功力极为深厚,而且拿的还是还是一把神兵利器,不然不可能割出怎么一条伤口啊!”话音刚落刘振南就焦急的问:“先生何出此言啊?”那仵作说道:“二公子不知,这伤口犹如丝线,脖子内食道,气管与血管都在同一平面上。如果在下推断不错,这一定是在刘帮主不曾防备之时一剑封喉,而且刘帮主在死之前一点声音也没有,你等不曾听到声响。”
身边的人马上过来说:“是,是,此话不假,我等到时,帮主已经躺在血泊之中,没有了气息。”仵作说道:“我虽不在江湖之中,但我也知道江湖上的实物,像这等高手在中原甚是少见,除了当年的乾坤长者,和昔日的武林盟主秋千成外,能达到这种的造就的在武林中不出三人。武功高者确实不少,可这用剑能达到如此出神入化的却没几个。好了,我验尸已毕,就不打扰公子了,庄上好友如此大事要办,在下就此告辞。”刘振南上劝道:“先生到来也不曾吃杯热茶,还是少坐片刻再走吧?”仵作回头说道:“这里还有大事须二公子处理,我也不便久留,况且衙门那边还有事情,我怎可耽误。还是请二公子就此留步,在下这就告辞了。”刘振南说:“既如此先生先且回去,日后刘某一定登门道谢。”说完那仵作便出了大门。
当晚吃过饭后,一家人有痛苦了一场,刘振南跟刘振东的儿子留下来守灵,刘振南一脸憔悴的样子,也确实两三日未曾合眼了。刘振东的妻子到来说:“叔叔也是几日未曾合眼了,今日就让我很浩儿再次守灵,叔叔先去歇息吧!明日还有大事,叔叔切不可累坏了身子啊!”刘振南不肯回去,在嫂嫂和自己夫人两人的劝说下才回去睡觉,灵堂内之剩下两位少夫人和刘振东的儿子刘宇浩三人守灵。
刘振南回到房屋后,看见自己母亲的排位,不由得流出了眼泪,想起从小被人欺凌的日子,便拿起手香炉前的在自己母亲的牌位前上香。也是这刘家的家训,不为正氏,牌位不可立于刘家灵位之上,不但是小妾就是连小妾所生的的子女也一样,所以刘振南从小就受到排斥。每当想起小时候,刘振南便心如刀割,此时的刘振南握紧了自己的双手,说看着灵位说道:“娘!孩儿已经掌握了大局,日后必将出人头地,你老人家泉下有知可以瞑目了。”
马帮帮主刘振东被杀犹如春波四海,江湖上人人皆知。任中义带着刘月兰等人来到金钱帮帮主梁宇,张越看到恩公到此自然尽情招待,随后出钱给店掌柜重开了酒楼,刘月兰跟着任中义就在金钱帮住下。刘月兰已是无依无靠的人了,刘老汉临死之前说月兰并不是自己亲生的,可没等说完,就段气了。任中义也只能现在再此小住几日,还的去帮月兰去找他的亲身父母。
早上任中义拿着一根木枝在院子里练功,月兰起来看着任中义,看不懂,不知任中义为何不用剑。看着任中义步伐硬朗,剑法迅速,身轻如燕。实在闲的无聊便在地上的华池旁捡了几颗石子,有大有小,先扔小的,用手腕的力量弹出。任中义正在空中翻转,感觉突然身后有东西袭来,用内力震起在空中又反转两圈,不想那石子竟然打断了一根花枝。任中义看见了甚是惊奇,没想到月兰竟有如此深厚的内力。
正在练功,便不想收手,看着月兰说:“月兰姑娘,再多扔几个过来,让我看看我这几天功力又没有长进。”月兰又拿了一颗小的朝同任中义胸部掷出去,任中义一动不动,右手持棍,等到石子离自己还有一尺远的时候,右脚下蹲左脚测出,手臂一挥,石子被打的粉碎,只见木枝上面擦破了一层皮。任中义又说:“在扔来两个。”月兰一次掷出去两块,人中义翻了一个转身又将两颗石子打得粉碎,任中义越发的来劲,虽然已是满头大汗,但也不觉得累。任中义手握木枝,左边一道白发直垂如胸,在微风下飘飘荡荡。叫了一声:“再来。”月兰把所有的石头都掷出去了,其中还有一颗坚韧的鹅卵石,任中义定睛看着空中的石子,手挥几下都打得粉碎,正中间飞来一颗鹅卵石,任中义腰部后伸,一个转身打到鹅卵石上,顿时石子粉碎,木枝折断。
月兰在院子里站着,初晨的阳光暖暖的找到院子里,洒在了月兰的身上,一路清风吹来,扇动着月兰的衣服,乌黑的发丝飘洒在风中。月兰越发的娇媚。
任中义收身运气以后走到月兰面前,看着月兰低声地说:“月兰姑娘,你怎么会这等厉害的工夫?真是没想到,你一柔弱女子,不想竟然怎么厉害?”月兰看着任中义转过身说:“我也不知道,从小时候起就一位僧人大师,我也不曾知道他叫什么,他教我如何使用手腕的力量,教我如何使用石子树枝作暗器已备防身使用。可是每次又教我的不同,从现在到摘花飞叶,后来又叫我轻功,在山上教我飞檐走壁,慢慢的就都熟悉了,那位师傅后来跟我父亲就成了好友,将也经常去我家里,有时候也试探我的功夫,就这样慢慢的我武艺也略懂一些。”任中义思量了片刻,人后开始跟你月兰商量如何帮月兰去找她的亲身父母。
天已经渐渐黑了,任中义一个人站在门口一个人,不由得想起以前,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跟着师父什么都不用做,谁想自己正如师父所说:“想在江湖上闯,就比先学会吃苦,江湖就是一脚踩在死人身上,一脚踩在棺材里。”现在想来还真是。
明月已经高悬在夜空中,黑色的浮云不短的飘过月下,任中义抬头看着天上飞的明月。看着空中的浮云一朵朵的飘过,正如任中义的心思,一片阴云一片天。看着这月色不觉得想起酒来,便拿了一小坛子酒跳上房顶。一个人坐在房梁上。一脚踩在房梁上,一脚伸在方坡上,手提着酒壶,看着天空。微风不断在天空吹着,任中义的的那一寸宽的白发,在微风中荡漾。喝了一阵就后,不由得烦恼涌上心头,自己害死了月兰姑娘的父母,本来就很愧疚,月兰的父母临终前又把她托付于自己,现在又的去找月兰亲身父母。很多事还等着自己去做,真是思绪万千,不知向谁诉说。
任中义一手拿着酒壶,一手搭在膝盖上,不由得想起自己以前自己吹的短笛。便把酒瓶放在房顶上,拿出自己的短笛,双手六指吹出悠扬的心思万缕。笛声在现,空中弥漫,声音悠长。月兰也正站在窗前,看着月光,不由得想起自己的父母,不甚的悲伤,又不知道自己的亲身父母在哪儿。不知不觉中,笛声已经传进屋里,给这这笛声的旋律一起伤感,好一会才感觉到有笛声传来。也不知道睡睡吹的,没想到怎么晚还有人跟自己一样心存忧虑。一个人便走出院中,听到笛声从房顶上吹来。
月兰抬头看着房顶,借着洁白的月光,月兰很清晰的看到任中义一个人坐在房梁上,独自吹着短笛。月兰现在的月兰更是睡不着了,纵身一跳飞上房梁之上。一身素白长裙,从地上飘然而起,轻轻地落在房梁上,借着洁白的月光,宛如仙女下凡。止到月兰飘然下落,任中义才感觉到有人上了屋顶,看着一身素白的月兰,在月光的演映下,微风吹拂着月兰衣服,感觉就像仙女下凡一般娇媚。
任中义看见月兰已经站到了房梁之上,才收了手中的短笛,月兰走到任中义前面,任中义立马打起是十二分的精神,站起来。酒坛子随着放坡滚落到地上,只听见“啪”的一声碎了。月兰看着任中义,一脸的忧郁,便问:“不知任大哥为何今日在此,心情如此忧郁,不知所谓何事?”任中义笑了笑说:“今夜月朗风清,只是想起以前的琐碎事物,所以才想起这短笛来。”两个人一起坐在房梁上,任中义便问:“不知为何月兰姑娘为何到现在还不睡觉啊?”月兰底下头我只是想起我的父母,还有自己的身世,所以..”
两人在房梁之上畅谈了许久,但心里的话却似说非说,各有保留,谁也不想触及到对方心里,任中义怕再提起月兰的事惹月兰伤心,月兰也不好意思多说,本来这自己就已经算成了任中义的累赘,现在也不好再去提找自己父母的事了。两个人深夜也无太多话要说,月兰低着头在房梁上坐着,任中义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刘月兰又看了看任中义说:“任大哥,不知你什么时候学会吹短笛的,吹得真是好听,不如你再吹给我听。”任中义也正愁没话可说,听见月兰说这话,倒是感觉给了自己一个台阶下。任中义说:“好,你想听,我当然乐意。”任中义便拿起怀中的短笛,又开始吹奏一曲曲荡气回肠。惹人陶醉。
在房梁上又坐了一会儿才各自回去,吹得任中义也是口干舌燥,只是不敢多说一句话语。也可能是月兰知道这短笛吹时间长了会口干舌燥,所以才说困了,两人才各自回去睡觉。任中义回到房中,端起桌子上的茶壶,那还顾得上用不用杯子,就往嘴里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