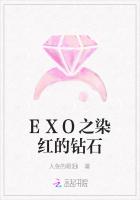我在浴室里待了很久,许是因为水声,我并没有听到有人开门的声音,所以当我从浴室出来看到旭霖一个人坐在黑暗里的时候,把我吓了一跳:“回来怎么不开灯?”
我穿着浴袍,头发半湿着,而我正准备打开灯的时候,旭霖一个健步走过来阻止了我。借着微微的黄光,我才发现他的脸色十分难看,像是生气了,而他身上散发的阵阵酒味让我更加不知所措。
他拖住我的后脑勺,霸道地吻了上来,就算我很努力地想要挣脱他,他就是不给我半点机会:“你怎么了?”
“你爱我吗?”旭霖停了下来。
我想他一定是醉了才会这样问我,但我的犹豫似乎激怒了他,他双手将我抬了起来,继续开阔的他的领域,而本身就穿着浴袍的我使他更是不费吹灰之力褪去了所有的遮蔽。
我并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叫停,过去的几年里每每这个时候,当他碰我的时候,我都是假装一副熟门熟路的样子迎合他,可是那天他说他对脏女人没兴趣。一想到这,我就冷了下来。
旭霖似乎是注意到我的变化,停了下来,然后看着我:“你爱我吗?”
我沉默。
“你爱我吗?”他的语气明显是生气了,而我继续的沉默让他什么都不顾,继续他的原本正在做的事,“说你爱我,这么难吗?”
那般撕裂的疼痛才让我发觉,旭霖这些年对待我的时候是有多温柔、多么小心翼翼。就算我知道,他是醉了,才会这么问我,就算我知道他把我当成了苏昕才会这么问我,可就是当他吼出一句:“有这么难吗?苏昕?”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奔溃了。
我拼命忍住的眼泪最终还是流了出来,我感觉到旭霖僵了一下,却很快恢复了。
那一夜,很长。就算是他最后放过了我,就算那么累,我还是一直睡不着,就那么想事情,想着想着迷迷糊糊地到了天亮。而当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旭霖已经不见了。他留了一张纸条在床头,我就算不看上面写什么,都知道他写的是什么。我摸索着手机,拨了过去。
说来也是,旭霖只要比我早起或是离开家的时候我还在睡,都会放张小纸条在床头或是桌上,而每次都是一样的几个字:醒了打给我。他从来都不叮嘱我什么事,只是酸我几句便收了线。
“这么早?”他很快就接了。
“嗯,”我有气无力地回着,“我马上要去现场。”
“行。晚上庆功宴结束之后,我来接你。”
对于昨天晚上的事情,我还是有些介意,都说酒醒之后或多或少还是对自己做了什么有些印象,更别说我一个大活人躺在他身边。他最后叫的名字是苏昕,让我最奔溃的那一瞬间也许对于他来说就只是在梦里了罢。
我擦掉自己没忍住而掉下来的眼泪,回了旭霖句:“好。”只是我不知道的是,电话那头的旭霖,露出了多痛苦的表情。
一切都进行的还算顺利,虽然中间有些小小的插曲,但在塞缪尔的帮助下,我还算是完美地结束了我的一场系列秀。即使没有收到确切的反馈,但凯文已经收到了很多方的订单。
“心情怎么这么差?”塞缪尔昨天晚上的举动让我还是有些没明白他想做什么,但看着他那样的态度,似乎他只是用了一种本就属于美洲人开放的一种道歉方式跟我说对不起罢了,我也没怎么在意。
庆功宴上,我端了一杯酒,便自己躲到了角落:“没事。”
“你和肖恩到底怎么了?”旭霖跟我一起来的事情我也没瞒着,正好也有借口可以让凯文早点放我回去,“我以为他这次陪你来是你们两个那天和解了。可是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我这一下才想明白,塞缪尔以为我和旭霖之间发生的小事那一晚和解了,旭霖才会陪我一起来这边。但后来几天的相处下来,他似乎觉得不是这么回事,所以昨天晚上才会选择和我道歉。
“没什么。”
“跟那个那天你在咖啡店碰面的女人有关吗?”我虽然不是有意地防备着塞缪尔,但有些事情我根本不知道该不该说。
我勾了勾嘴角:“是我自己以前做错的事情太多。”
“不过,我倒是没想到,肖恩这么粗鲁。”塞缪尔转话题的速度真的比翻书还快,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去,才发现自己手臂上的遮瑕膏有些掉了,一块淤青被完全地展现了出来。
我迅速捂住:“我不小心弄的,跟他没关系。”我找了个借口去了化妆间,想要赶紧在别人发现之前修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