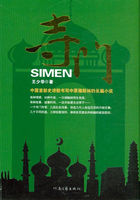随着纪渊与皇甫承沧被姜付仁抛出玲珑大镇,阮顷峰也已有了动作。今夜之事,乃是姬家与神宫的绝秘谋划,自是不会让人将消息传出去,不管这两个少年是何家世,今晚都必须死在这里。
阮顷峰虽已有受伤,可要对付这两名少年自是不在话下,他一掌拍出,眼看便要落在纪渊身上,眼前突然一花,那本该让少年筋骨尽碎的一掌居然拍空。
阮顷峰稳住周身气意,眼神变厉,此时的玲珑大镇居然还有他未察觉之人,阮顷峰心中大惊,然而既然对方此时出手,自是没打算消无声息的离去,他沉声喝道:“谁?给我滚出来!”
有雨落下,淅淅沥沥,却并不让人觉得真切,仿若只是幻觉般,雨渐渐织起一片雨雾,将玲珑大镇与外界隔绝而开。
阮顷峰轻眯起双眼,这般障眼法对他而言自是无用,他早已用气意锁住了那两名少年。
纪渊经历这莫名奇妙的险境,此时跟皇甫承沧不知所措的立在镇外,被眼前纷乱的雨给惊醒,两名少年此时倒默契一致的撒腿便跑。
阮顷峰眉头跳了跳,纵身一跃而起,突然脸色大变,居然又落回了原地。
那飘落无根的雨,在他一跃而起时,竟形成一道雨幕将他拦住,阮顷峰神色凝重,对那隐于暗处之人,多了几份顾虑。他瞥了一眼立在一旁待命的首羊奴,首羊奴得到主人的命令,如山般的身躯突然横撞而出。
无数的雨滴似受如唤般化作一道从天而降的瀑布,将那首羊奴挡住,任凭他如何冲撞,皆不得而出。
阮顷峰面色难看,沉思片刻后,放弃了继续追踪那两名少年的打算,将目光移向了岁河方向。
岁河的岸边,老者缓缓收回手,看了一眼身旁持黑伞的少女,讪讪笑道:“师父平时不是吹牛吧?”
黑伞黑衣的少女宁千鹤望了眼远处狼狈至极的两名少年,想起那一袭红衣的少女,至到此时,纪芸还未出现,她不免有些焦急,听得师父自夸,随口应道:“不过就是挡下个受了伤的阮顷峰而已。”
“走吧,今晚这出戏也看完了,姬家的人要收尾了。”老者说完着便准备动身离去。
宁千鹤没有动,依旧望着远处,她眉头轻拧,老者望了一眼,叹了口气道:“教了你这么多年,真是白交了,这人间之情你不斩断,绝命就依旧是绝命。”老者说归说,宠溺的拍了拍徒弟的肩,伸手指了指,接着说道:“那个红衣女娃儿被君不见给救了一命,拦住没让她入镇去,你就放心吧。”
宁千鹤没有说话,只是转头看向了师父,这个从来都爱跟自己插科打诨的老头子,可最是能骗人,确定师父的话属实后她才缓缓点了点头。
老者瞥了眼岁河,轻轻地摇了摇头,宽大的袖袍一扬,两人消失于原地。
岁河似已失去精气,连浪潮也没了那股气势,水声低咽沉闷,摇晃着那艘楼船缓缓靠岸。
贺印寿面色有些泛白,刚才那番交战他赢得并不轻松,他并没有急着下船,只是望着已化为废墟的玲珑大镇良久。
阮顷峰打量着那艘神宫的楼船,轻眯起双眼,玩味的笑道:“承蒙贺老先生出手,姬王朝定不忘神宫恩情。”
“留武侯还是留点力气养精神吧。”贺印寿冷冷回了一句,转身走回了舱中。
阮顷峰伤得很重,若非姬家王气护身早已命毙当场,他虽强自镇定可却逃不过炼气大家贺印寿的法眼,被这么呛了一句阮顷峰干咳了一声,这转身看着跟随自己而来的首羊奴。
姬家虽然早已雄距神州,可只是强夺天启气运,并非正统,也因此四百年前初代大云也不敢将天启真龙之气运收纳,唯恐天谴姬家。四百年过去,天启王室死绝,天下正统早失,神州气运大半由姬家所掌握,这才有了谋夺天启残留气运的心思,想这神州大地从无两道王气共存之理,若要收取天启残余王气,必然要引天谴下凡,息上天之怒方可。
这首羊奴便是为此而来。
当然也是为死而来!
本能之中对于主人的服从让首羊奴无法抗拒这道命令,他巨大的身躯缓慢而颤抖着向岁河移去,在首羊山经姬家先人调教,他们早就没了自我可言。
经历贺印寿与姜付仁刚才那场大战,三名抽取气运的神官早已被混乱的气运所震,好不容易才缓过了劲来,所幸那抽取气运的阵法并未被波及,省去了不少的麻烦,三名神官略作调息,再次以天地人三位而立,将沉于岁河底的王运之气导出。
这次三名神官却并未向上天导去,而是改变方向,投向首羊奴之躯。
宏大的气运,沉睡了四百之久,被神宫炼气士从河底唤出,而这片天地间早已归了姬家,两股王气的交汇引动天地震响。
强大的气运威压让天地为之静默,连水声也渐渐低沉下去,仿若两名不可一世的君王相对而立,无形的魄力张显于世。
普通人哪里承受得了这样的威压!
在场的虽然不是普通人,可与姬家多少有些关联,能感受到两股气运的交战之景。阮顷峰因为先前受伤,体内还有残留的天启气运,此时最是痛苦,但他毕竟是一国之主,丝毫也未流露于面上。
贺印寿寿眉轻扬,双手闪电般按在那恕方印之上,一股威压由印中释出,如实质般化作一方金黄丝帛缓缓流出船舱,朝那两股王气而去。
身处两股王气相冲处的炼气士已有些承受不住,好在这方金黄丝帛来得及时,稳住了那两股相冲的王气,金黄丝帛如一卷天书般牢牢将两股王气包裹,不让其四散而出,被包裹住的王气争斗却更为激烈,贺印寿双掌再一用劲,金黄丝帛越裹越紧,那两股王气渐渐地平息了下来。
而处于王气相交处的首羊奴则难逃厄运,原本壮硕如山的身体像纸片般胸弱,强大的王气本就不是他这种奴性命所能承受,随着两股两冲的王气被金黄丝帛镇压开始缓缓注入他的体内,他那如铁石般的身躯便开始膨胀了起来。
首羊奴虽一出生便不能言语,从小被药物调理并未启智,但要以身躯作为王气转化的容器却依旧让人觉得残忍。
贺印寿缓缓闭上了眼,他不喜这般作法,却也无可奈何,这趟差使完结,他与神宫所情份也就不剩什么了。
作了首羊奴的主人,阮顷峰却颇为兴奋,整件事都在按既定的方向而行,首羊奴从小便由姬家老祖调教,身上沾染最多姬家王气,虽然由于命格原因并不能承受过多的气运,可天生便是这转化王气的最佳容器。这次主动请缨前来,便是想借这次功绩再为自身添加几份王气,他自知这些年作为姬天子的亲舅,也是姬王朝的打手,他竖敌过多,自身修为如姜付仁所言已无精进的可能,便只能凭借王气自保。
首羊奴的叫声响彻岁河两岸,众人闻所未闻,天地间的暴躁已不似刚才那般猛烈,岁河依旧呜咽流淌。
随着首羊奴最后一声大叫之声,金黄丝帛所包裹的王气散尽,万物寂籁。
阮顷峰一跃而起,也不顾自身伤势,将首羊奴高大的身躯扶住。
此时的首羊奴七窍洞穿,浑身似被蒸透了般冒着白气,他瘫软如泥,虽早已气绝,可那双眼睛依旧不甘的睁大。
“孤谢过神宫。”阮顷峰拱手朝楼船行了一礼。
贺印寿懒懒地抬起了眼皮,重重呼出一口气,没有言语,转身对三名神官道:“开船,回宫。”
月如初,再次照印在这片大地之上,万物如故。
纪渊抬头看了眼天上的月光,一屁股坐了下来,他身后便是皇甫承沧。
两个逃命的少年都已经跑不动了,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究竟跑了有多远,此时有了月光正好看看四周。
“你说那留武侯还会不会追我们?”皇甫承沧几乎被吓破了胆,这会虽然坐着休息,可脑袋没停地四下转着。
纪渊倒坦然了许多,他捶着酸腿的小腿说道:“就是追来我们也跑不动了。”
皇甫承沧有些泄气,想了片刻也有些释然了,学着纪渊的样子按摩小腿:“今晚这出戏,可以让我吹一辈子了,你说谁能亲眼看一眼谪仙,还有那些传说中的人物,更别提初代大云法身了……唉,想着都觉得不真实。”
“活命比什么都真实,只要你能活着,总能像他们那般。”
皇甫承沧瞄了眼纪渊,笑道:“没想到你小子心还不小,居然想以后跟他们那样厉害?”
还有君山要去呢,不变强怎么去呢,纪渊想起韩哑巴,心情又低落了起来。
“别动,有人。”皇甫承沧突然按住了纪渊,眼睛望向了一处草丛,纪渊被他这么一说也紧张了起来。
难道是阮顷峰追来了?不可能,若真是阮顷峰,根本没必要这么偷偷摸摸,难道这附近还有其他人。
皇甫承沧深吸了一口气,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头,纪渊跟在他身后也拾起了一块石头,两人猫着腰朝那树丛摸了过去。
皇甫承沧吞了吞口水,缓缓地剥开了树丛。
“啊!”
皇甫承沧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任谁见到一只突然出现在的眼前的驴脑袋也会被吓一跳,更何况这只驴还一个劲的蠢笑。
“君不见的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