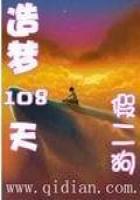第一卷 我的父亲(十五)
这雄委曲空手,回到旅馆,无精打采的。杨小生让她去吃饭,她也不去,只好在外面去炒个几个菜,端进房里。让他吃饭,只道,“小雄,先吃点饭,至于生意买卖,这个年头就这样子。那个作生意的又不被政府找麻烦。好歹比前俩年好,动不动就要坐牢判刑还罚金的,如今也只是没收货物,并不动用刑法。”杨小生见雄委曲不啃声,又道,“生意人也只有委屈求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材烧。被他们没收了也就算了,过些日子又重来。没什么大不了的。”那雄委曲底声道,“小杨,你不明白的。你是单身汉,没有负担,自然可以无所谓。可是我现在有4个孩子要养活,4个孩子——老刘走了,他到轻松,丢了一大群娃娃儿,叫我怎么办,我一个人要养四个孩子......我真的不想活了。”那杨小生,见雄委曲回来就不啃声。好不容易劝了半天,见雄委曲才开始说话,满以为就象往常只消再劝劝就会没事了。谁想到那雄委曲说话时候,突然又激动起来,猛地起身突然撞向了墙壁的凹凸处。杨小生也是眼急手快,一把她抓住,拖了回来,死死按住她在床上。但见雄委曲的额上已经开使流血了,口内依旧大声说自己四个孩子要养,自己没办法养活等语。急得小胡又用手帕去为她揩,又道,“你这么这么傻,你这么这么傻,你如果就这么去了,你家里的娃儿怎么办呢?”那雄委曲早已经泪流满面。只是底声喃喃道,“我真的不想活了......”说话间,额头上已经血流如注。这小生的手帕已经成了血帕。不得已,又扶着她去医院。
旅馆的服务员先听得房里又吵又闹,正准备上来看个究竟。突然见杨小生抱这血流满面的雄委曲冲出来,喊叫着去了附近医院.
幸好只是外伤,逢了几针,包扎伤口,也就没什么大事情。少不了有人要问发生什么事情,杨小生只道是委曲不小心跌了一筋斗。回到旅馆,又劝了一回,那雄委曲的情绪也平静了许多,依然数落自己的眼下的困难。那杨小生只得应承先借些钱给雄委曲,还答应给孩子交学费,又答应借几百快钱给雄委曲做生意。并许诺,只要有姓杨的在一天,就要帮她一天。这里雄委屈才转悲为喜。自此,两个人的关系又进了一层。
没多久,众街坊无不议论纷纷,都说那雄委曲和杨小生怎么样。果然,第二年那雄委曲又添一子,终究还是人言可谓,取名字还是姓刘,并不敢直接取杨。虽然那小生嚷过几次,要子女们都改杨姓,最终还是没有定得下来。又过两年,两个人结婚登记,成为了正式夫妻。原本喜欢议论他们两人邻居,反而不再有什么闲话好说的了.这是后话。
如今再说,胡国香,在家静养了一年半载,身体虽然渐渐得到修养和恢复,但始终不如以前。往年的积蓄因为一家人的生活,再加上自己吃药上医院的缘故,已经快用完。幸好,挺章从唐安友的妹妹那里学了这卖凉粉的技艺,便开始躲在家里,偷偷地卖点粮粉,风声不紧的时候,就挑在大街巷子口去卖,靠着这小本生意,到也能够赚钱养家的。国香稍微有点点闲空就拖着病体,去坐茶馆,打发时日。这日,扶了拐棍,到茶管里去喝茶。往日的茶友纷纷挣着开那茶钱。就有不到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大声道,“你门不要与我争,今天我来替胡二爷开这茶钱。”一边说,一边拉住茶馆的小二哥的手,把钱塞在小二哥的手里。众人方才安静下来。胡国香定睛仔细瞧时,不觉大吃一惊,心想,“这不是那个周卫东。”心下好生奇怪。忙问身边的茶友,才知道,这周卫东已经没有在市管会做事情了。就在茶馆里面做布票,粮票生意,已经好一阵子了。此时,又有茶友在笑那周卫东道,“你过去抓走资派,现在你的身前,身后,满是走资派,我看你是如何抓得完。”大家又是大笑。这里,又有人问胡国香手头可有什么紧销的货物。那胡国香也只得如实相告了自己的景况。那些茶友那里肯信,只道,“瘦死的骡驼比马大,满茶馆都知道你胡二爷,是想得出办法的人。”说话间,那周卫东不知道何时把自己的茶碗移了过来,接过话头向胡国香,“胡二爷,过去有很多对不住的地方,希望你胡二爷大人不计较小人过。”原来这周卫东在**时候参加派性斗争的时候,也算是积极份子,没想到去年被人递了诉状,告他在武斗期间杀人。市管会的现任领导因为过去,大多和他不是一派的,趁机把他开出单位。虽然后来因为证据不足,关押几个月后,释放出来,再想回原单位。单位负责人严昆东等人,铁心咬定他是个杀人犯,不许他回单位。这周卫东又想去找武斗期间自己这派的同事出来说情。那知道,那些同事大多因为过去的罪过或坐牢,或被开出,剩余的这些同事如今惟恐自己被周卫东牵扯上,都不愿意见他。哪里还敢替他说什么情。当面推脱不算,背地里又去落井下石头,向领导进言献好。说那些人多半是这周卫东杀的,现在虽然证据不足,但并不能说他没有罪,而自己在武斗时期的所做所为却推得干干净净的。周卫东自单位出来后,没有了工作,没有收入,过去的同事都不愿意和他来往。他也只好在家里借酒浇愁。老婆见他如今落魄,也不时说些现成话。骂他在家吃闲饭。周卫东又羞又愧。偶而去做点居委会安排的临工,放不下架子,看不惯工地上的工头对他大呼小叫的。自觉得堂堂国家干部,沦落至此,有虎落平阳关被犬欺的味道。因此,周卫东有时候忍不住和工头顶撞几句。那工头就不要他。他也图个清闲,不时跑到茶馆里去,渐渐地也学做生意,倒卖起布票,粮票来。日子一长,他也知道些茶管里的生意场上的秘密,知道哪些人过去是做大买卖的。今见胡国香到来,他也从茶友身上知道这胡国香过去,是做大买卖的人,巴望着日后大家有个照应,挣点大钱。所以他也顾不得许多,争着开胡国香的茶钱。一时候,国香又问道,“你如何也来搞这投机倒把的买卖?”周卫东也只得说了自己的实际情况。又对国香道,“人,活着,要吃饭,不做点生意怎么办?”胡国香道,“我们老百姓说来说去,就是要吃口饭,也没有那一个想做这生意的,都是拖家养口,没有办法,才做点小生意。”周卫东道,“就是,现在我也是做生意的,日后有什么好的货物,还是多多照顾的。”胡国香又道,“生意场上的人都是朋友,讲究的是有路子大家走,有钱大家挣,谈不上照顾,大家互相都要彼此照应的。”这里周卫东又向胡国乡道了歉。胡国香也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这周卫东又顺便,从茶友身上,买了些粮票。从茶馆出来,就准备回家,又害怕碰见市管会的,因为市管会的也知道周卫东成了阶级敌人,有事没事拦截与他。趁机会没收周卫东身上的货物来。这周卫东挨过几次,也就学机灵了,身上有货物就绕道走河边小路,还没走多远,就见前面有两个农村摸样的人朝自己走来,那两人死死把自己盯着,这周卫东心里就有些发毛,忙转身回走。只觉得后脑袋上重重地挨了一下,脚下一软,就载了下去。就听得有人道,“这个傻儿过去这么凶,原来是过不经打的......”等这说话声音渐渐远去。周卫东好半天,才爬起身,脑袋还嗡嗡做响。心里面也知道,过去种下的罪孽,才有此报应。
回到家里,她那老婆又说他是大街不走,走小路。什么不学,偏去学做投机倒把。这周卫东,知道现在老婆已经和他不是同路人。瞧不起他这种投机倒把份子,也不理会老婆的冷言冷语。心中只是猜想应该是什么人干的。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结果。只怪自己过去做事情没给自己留后路,以至树敌太多。现在自己又没有在单位上工作,那些曾经嫉恨自己的人,自然不再畏惧,那里有不报复自己的。又想到头几年自己被借调入县革委会时候,送了多少人进牢房,现在陆陆续续又开始出来了,日后,还有得自己受的。想到这里已经是懊悔不已。自从学着倒买粮票,布票以来,对投机倒把的有了些新的体会,也知道自己这样在茶馆里做的小买卖,也只能赚点小钱的。更何况农村里并不象过去那样生活物资极端紧缺,恐怕日后还更难牟利些,想到此处,更觉得没有什么出路,免不了又唉声叹气一番。
次日,这周卫东又去茶馆,少不了又替大家开茶钱,说好话。多少人也知道他的情况,就不与他理论,还彼此之间传信,让过去记恨与他的,准备找机会收拾这周卫东的,不要在计较周卫东的过去了,好歹莫再去寻周卫东的麻烦。这周卫东才渐渐地为大家所接受。周卫东虽然也做些投机倒把的买卖,但终究是生意越来越不好做,生意场上的新贵知道他的过去的,大多不理会与他。这周卫东也是很不得志,成日里郁郁寡欢,借酒浇愁。终于在80年死于酒精中毒。死时年仅51岁。
却说国香这日,正在堂屋里头坐了,准备吃了药又去茶馆。挺章就带了个年近三十的中年人径直进来,中年人见国香就道,“香表叔!”国香忙抬头,见这中年人穿的旧衣服。蓄了长头发,目光也闪烁不定的。来人又道,“我是何彪,我父亲何成。”挺章听罢仔细瞧了。只是这突然间当年的小伙子已经老了许多,这国香还半信半疑。挺章又在一旁说是何彪,何成的大儿子,国香才回过神来。忙招呼这何彪坐了。挺章也就招呼了何彪在家里玩耍,自去巷子口守自己的凉粉摊。这里,国香,知道他没有吃饭,忙有去锅里头热了冷饭,冷菜与他吃了。国香这才问起何彪的父亲这么长时间没有上街。何彪只说他父亲长期病重,这几年不比得往年的身体,所以想来也来不了。国香道,“我和你父亲看着看着就已经老了。你也有很多年没有来了。”何彪说道,“就是,我看有许多年了吧。早就想来看你的,农村事情又多。”国香道,“你好好地在家种田,只要勤快,也还是有饭吃的。”两人又扯了会家常。这何彪就借故出去了。大约半个时辰。何彪又回来了,拿了一包白糖对国香道,“表叔,我拿包白糖给你烫开水喝。”国香自是高兴,笑着道,“那要得。”说罢也就收下了,顺便放在桌子上。又令何彪坐了。继续问他在农村的情况。这何彪便开始支支唔唔地,前言不达后语。正说着,就见挺章从外面气冲冲走进来,铁青着脸,拿了桌子上的白糖。国香忙问什么事情。挺章道,“什么事情,他这包白糖偷来的。旁边铺子的卖糖的罗大爷的。人家眼睛不是很向堂。他手脚到还快!”说罢,拿了那糖急冲冲的又还回去,只对守摊子的罗老头子,道,“罗大爷,你的糖被贼娃子偷跑了,我去给你撵回来了。”一边说,一边把糖放回原位。挺章前脚走,国香在家里也忍不住立即就训斥何彪,道,“你怎么能够去偷呢,你没有礼信上门,我也不怪你的。”那何彪只道是自己送了东西,却从没有那个人在乎东西怎么来的。没想到国香表叔如此不开通。想要争辩,也不知道如何说起。半天才道,“他自己没收拾好,掉在地上,我顺势从地上拣的,算不得偷——”话还没有说完,又听得国香让自己快回去了,日后没有允许就不可再来的。何彪也只得回去了。过些日子,何成的二儿子来看望,两个人就说起何彪的事情。国香禁不住叹气道,“怪不得这么多年不听你父亲说起过。原来是不学好的,学了做贼。”这何老二又叮嘱道,“日后切莫让他来这里,大哥是走到那里偷到哪里的人。”说罢,何老二又叹气道,“大哥他自己,早年一心想找大钱,就做生意,又被抓进大牢,自从牢里出来后,他总说种田太累,没意思。成日里就开始不务正业。”国香道,“我们小老百姓,有碗饭吃就算了,还想挣什么大钱。”说罢,又问了何成的情况,知道何成病重,可能不久于人世。何老二只说是特地给表叔说,并不需要表叔去的。
原来这何彪在乡下早年卖豆腐,被抓进去关了一段时间后,出来就再也不愿意干什么,成日里在下乡偷鸡摸狗。恰好对面坡上又有两个重庆市区来的下乡知青。这两个知青,原以为这稻谷是树上长的,只消扯下来就可以吃,没有想到这稻谷原来是要经历查秧施肥,多次梨田打坝,打谷脱皮等手脚活路,其间又有多少抬挑等重体力劳动才换来的。这两个知青在大城市呆惯了的,又没有什么劳动力,种不来田,下不得力,自然一年下来,挣不到什么工分。少不了就开始今天偷吃这家的鸡,明天偷杀那家的鸭。一时,闹得四周鸡犬不宁的。不想,有一次,这何彪就去两个知青家里,闯见两个人正偷吃鸡。就装腔做调要去举报。这两个知青忙邀请何彪一起吃了。自此,三个人臭味相投,打成一伙。那邻居渐渐知道了,因为那些知青隔几年,都要走的,大家都来埋怨这何彪,又迁怒于何成。那何成虽然打骂过自己的大儿子,要他老老实实地在乡下种田。这何彪只说自己种田,挣的工分,连饱饭都吃不上,正儿八经地做生意还要坐牢。还不如就这样吃百家饭,也不过是逗得众人恨,并不会去坐牢的。这何成一怒之下,就让何彪自立了门户。何彪自己也就在山对面起了茅屋子,自此和那两个知青更是形影不离的。不想,那两个知青,时间一到,就回去了。这何彪也就成了远近闻名的贼娃子。这几年乡下的左右邻居都偷遍了,他又开始四处游荡,前些日子,他又开始到县城里活动,想找个落脚的地方。这才想起了已经有好多年没有来这国香家里。又害怕自己在乡下的事情,父亲多少已经告诉了国香,自己恐怕不受欢迎,也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空着双手上门。和国香摆了一会儿龙门阵,才知道,父亲爱面子,不愿意家丑外扬的,并未把自己的事情对国乡说过。虽然自己被父亲警告不能上国香家来,如今父亲重病是不能来上街赶场的,自己偷偷来国香家落个脚,也算是个好注意。因想着自己空手而来,就去大街上使出了他妙手空空的绝活来,顺手拿了包白糖想来补个礼性。却不料又被挺章瞧见,愿想在县城里有个落脚的地方,连板凳都还没热,就被逼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