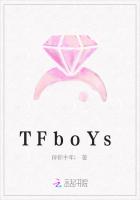看看现在这个家,已经成什么样子了,值钱的东西根本就没有了。
这样的说法好像也不全对,因为这屋子里的,要说唯一值钱的东西,恐怕只有冯列革本人了,只要他敢也愿意为了什么革命事业“光荣”一次,随便就可以给女儿与老婆留下一笔十几万或者几十万的遗产——只是凭冯列革的修养,他是做不出也做不来那样的“大事儿”的。人活脸,树活皮,电灯泡子活玻璃——他绝对是活脸的,毕竟他是个曾经操过社会的人。
屋里收拾得还算整洁,虽有些微的零乱,但总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在这个家里生活的只有一只雄性动物——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屋子里的东西并不多,又能凌乱到什么程度呢?
多年前,房子只是被简单地装修了一下,乳白色的墙上并没有多少装饰物,在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不知道是谁画的骏马图,金黄色的框右下角残了一块,像是被什么重物打残的,又像是掉落在地上摔坏的;正对骏马图的墙上则是一幅字,写着“求真”二字,落款是一个署名静观的人,也不知写这个字的人真名叫静观还是笔名叫静观,反正冯列革并不认识这个名人。
关于这幅字的来由呢,还有那么一段故事:当初渡转市有个高官,非常喜欢字画,于是冯列革就花钱托人去京城里找这个叫静观的人写了三幅字,送到高官手里时,不知道高官是什么原因将“求真”这幅字退了回来。时至今日,冯列革都不明白其中的缘由。再后来,高官在一次运动中落入了囹圄,具体原因冯列革早就没有心思去关心了,但从高官退回的“求真”这二字里,大概也能看出一点端倪。
卫生间的外墙就是客厅的墙壁,估计是水管出了点什么问题,墙壁上老是有一大块水渍的痕迹,有时像倒长的蘑菇头,有时又像风吹乱的云头,曾几何时,冯列革居然能从痕迹里看出张牙舞爪的妖怪来!
这套套三的房子,是早年冯列革与某地产商人有生意往来时,商人作为友情的见证半卖半送让给冯列革的商品房,虽然现在这个小区的房价已经翻了几番,而冯列革手里正缺钱用,但他也并没有打主意卖掉这套房子——因为他清楚地明白,自己现在除了这套房子外已经一无所有了,如果连这套房子也卖了,万一妻子病好了,女儿毕业回来了,一家三口就只能流落街头了!
这个叫都市静海的小区地处渡转市有名的经济开发区的上风地带,背靠有名的龙门山脉,推开后窗就能看到著名的西山云海风景区,而推开前窗,则能看到渡转市的街景,看到这个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小区的住宅楼呈C型排列,在中间的空白区域是一个面积超过一千平方米的人工湖,谓之静海。湖上亭台楼阁豪华飘逸,每到晚上,彩灯闪烁,仙意非常。而湖中则种植莲花,在春天与夏天里,湖面绿意盎然,芳香异常。
而此时的湖面上则是残荷遍布,在秋风秋雨中更显得落拓而寂寞。从北方下来的强冷空气自入秋以来,已经是第三次久久地盘旋在渡转市的上空了。
不管小区的景色如何,冯列革好像从来没有心思仔细去欣赏过。自打没有了企业以来,他本来用不着再去花那么多的心思整天想着如何整顿企业,如何管理员工,也自然就能有时间欣赏景色,调整一下心态,可是,他却并没有停下来,更没有什么好的心情在走进小区时停下来看看荷花,看看在水面上飞来飞去的蝴蝶蜻蜓。
倒是在夏末秋初之时,那些烦躁不安的蝉声引起过他的注意,不过很快他就忘了,蝉子们究竟在哀叹什么,诅咒什么。
要说小小的蝉子能引起他的注意,其实也只是一个偶然。
那一天,他正穿过湖边的柳树阵匆匆回家时,一阵凄厉的蝉鸣声滑过头顶,突然间一只蝉子就掉落在他的头顶上,弹了一下就掉到了他面前的花砖上,又在地上滚了十几公分后,不动了。
冯列革猛然间想起一句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马上抬头在空中及柳条间寻找,希望看到一只嘴里衔着螳螂的黄雀。可是除了开始泛黄的柳叶外,他没有看到任何跳跃的生灵。
看来,这只蝉子并不是被螳螂所杀,而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秋风中唱完了生命的音符。
蹲下身子,看着这只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就生活了至少有三五个年头的昆虫,据说也有在地下生活七年的,还有十三年,甚至更有十七年的,然而他们一爬出地面,在阳光下的寿命却只有短短的两个多月的时间,他心里突然间涌起一种悲凉。
一个夏天,短短的八九十天里,它们要完成从恋爱到结婚到生子,再到回归尘土的整个生命历程,难怪雄蝉从爬出地洞爬上枝头蜕掉老皮后,从第一声呼唤开始就一直在叫“苦——啊,苦——啊,苦——啊”。呼唤哑巴伴侣的过程一定充满了精彩,要不然它们为什么要那么拼尽全力?在黑暗里积蓄了那么多年的精气神肯定就为了完成生命里那神圣的最后一吻!
蝉子动了一下,冯列革以为它又活了,可定睛一看,才发现有几只黑色的蚂蚁已经爬上了它的身子,估计是蚂蚁的撕咬触动了它生命里最后的一根神经。它动了那么一下,就再也没有动静了。
冯列革真想摁死那些蚂蚁!他伸出右手提起蝉子的翅膀,想抖落掉那几只蚂蚁,可是任凭他如何努力,蚂蚁就是咬住不松口。当他伸出左手的食指和拇指准备行凶时,他忽然间起了恻隐之心。
重新放下蝉子,他开始观察蚂蚁要如何处理这巨大的食物。很快有一队蚂蚁从柳树根部的洞里爬了过来,迅速地布满了蝉身,一些开始肢解蝉身,一些就开始往家里拖运。
冯列革觉得脚开始发麻,抬起头前后左右地看了一眼,这是一条过道,来往行人很多,他突然担心这些黑色的小生命会被人踩个稀烂,于是他尖着指头提起蝉子的翅膀,将它放到了蚂蚁的洞口。
两三只蚂蚁爬上了他的手指,狠命地咬着他,一丝轻微的疼迅速地传到了脑海里。
拍掉叮在皮肤上的蚂蚁,冯列革站起身来,最后看了一眼蝉子和蚂蚁,准备离开时,他竟然觉得自己活得就好像那只蝉子一样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