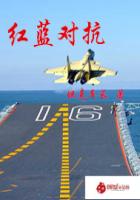逼仄的房间被一股湿气笼罩着,加上前房客留下的淡淡烟草味,我整夜都在半梦半醒间颠倒着。刺眼的阳光执意穿过残旧的窗帘布透射进来,我筋疲力尽,无奈地从忽明忽暗的空间里摸出手机,确认时间:清晨八点半。
如此陌生的早晨,陌生的房间,也许只有手机能沉睡至天明。
从被窝到洗手间只消移动四五步,疲乏的身体却需尽力而为之。洗手间一览无余,酒店可谓精打细算,没有浪费一丝可用空间。我挤出牙膏,一边刷牙,一边看着镜中的自己:眼袋微微隆起,呈青黑色;嘴里的泡沫由白变红——应该是这一年还没洗牙的缘故,我这样安慰自己。
擦完脸,我顺手拿起酒店赠送的茶包,烧一壶开水,泡上一杯清茶——但愿它能消除疲劳。一切就绪,我重回床上,挪动至床头拉开那残旧不堪的窗帘——
尚好的阳光下,弥敦道上早已熙来攘往。路人个个目无表情、行色匆匆:有赶着上巴士中途放弃早餐队伍的,有堵在路上不停低头看腕表的,有左手拎早餐袋,右臂夹公文包,同时右肩还要顶着一部手机能说会道的……总之,个个都是分秒必争。这是他们崭新一天的开端,而我的开端呢?我的开端就是通过欣赏陌生的他们,来熟悉这个陌生的城市。
我的视线停在了三点钟方向,诺富特酒店三楼窗口的一金发女郎身上。女郎无比优雅地点燃一支烟,然后右臂撑在窗台上吐起眼圈来。她应该是个无聊的人,可能比我还无聊。正当我如此想着,一个男人突然从背后揽住她,她回过头,与男人肆意地拥吻。我兴致勃勃地打量着这一切,直到她突然转过头与我四目相对,我方才羞愧地俯身而去。
躺回床上,我闭目养神,过往的残片尽收眼底——
数月前,在北京的诺富特酒店。我对着阿彬喜出望外的脸,残酷地解释道:“其实我们刚刚在玩真心话大冒险,所以——”或许残酷只是我自以为,但我再也解释不下去,倒是阿彬接上去:“我也希望我在玩游戏,可惜我没有……”那天阿彬几乎把几年来闷在心里的话一口气都说了出来,譬如“他当年为何离开杭州”、“当年为何会有那场同学会”、“他又为何会再回来杭州”这类掏心窝子的话。那一刻,即使他曾经再怎么矮小猥琐,又做过再多龌蹉不堪的事,似乎都不是个事。更何况,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剑眉星眼的八尺男儿。可正当我感动涕零,准备献身之际,他却只身离开了北京,徒留我孑身一人在北京的沙尘暴里自怨自艾——我错过的都是青春。这件事对我影响极大——它害我至今仍保持处子之身。也许在上一辈眼里,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可在当今社会,这似乎(不敢肯定)是不值得炫耀的吧?
无论如何,此刻在诺富特对面逼仄的经济型酒店的我,至少是明净的——我跟阿彬是身份悬殊的两类人——若不是我心比天高,久而久之蒙了自己,如此表象也不至于现在才看清。
我呷一口茶,闭上眼又睁开眼:空白的天花板、硕大的行李箱以及卫生间里排风扇发出的呜呼声,无一不在告诫我:你已没了退路。这个城市飞速的生活节奏方才我已领略过,我后怕起来——或许我还没准备好。
这时,手机响起——
我揣摩是分公司打来的——比约定的时间足足早了一个钟头——我打起精神悍然坐立起来,心跳开始猛然加速,我清了清嗓子,拿起手机,心突然沉重得不能跳动——
阿彬来电?
我狐疑不定,手指僵在空中,在接听与拒绝中不知所措。或许我考虑得委实太久了,没等我接听,电话已断线。我立刻回拨,可还未按下拨通键心跳再次猛然加速,又突然停止——
阿彬来电!
我立刻接听。这一次,连手机铃声都没来得及响起。
“喂,是我。你在哪?”他的声音低沉而疲倦。
“香港。”
“我知道,”他说,“我是说在香港哪里?”
“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去过我家?”
“这不重要,”他急匆匆地说,“我这个周末来找你。”
“你一个人过来吗?还是——”滋长在我心里许久的疙瘩此刻急速蔓延至喉咙口,卡得我说不出话。
“什么?”他的聪慧从来不用在揣测我的心思上,我苦笑:“没什么。”
“那我们周末见,你待会把地址发我——”
“找我什么事?”
“有些事,我想当面向你解释。”
“别卖关子了,电话里说吧。”
“有些话只能当面说。”
“太远了,别特地跑一趟了,”我话中有话,“电话里说也一样。”
“两个小时而已,不远;况且——我过来也有事。”
他终究还是出错了——所以,是因为不远,因为顺道。他可以用两个小时的时间飞到千里之外的香港来看我,却无心跨越阻碍在我们之间遥远的鸿沟。
如果我没有欲擒故纵,如果他没有那样说,事到如今也许一切都会不同吧?然而,这世上终究没有如果。女人总是设圈套试探男人,可男人偏偏笨拙无比,自己掉入圈套不说,还拉着女人一起掉下去。当女人发现结果是自己给自己下了套时,往往已两败俱伤。
可悲的是,彼时的我不懂这些,更加不会知道那句甚是突兀的“况且我过来也有事”,也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是借口。更可悲的是,一次试探未遂,我竟执着地进行第二次,并且,这股执拗劲儿竟胆敢将方才卡住喉咙的疙瘩瞬间消化。
“跟李墨一起吗?”我终于说了出口,等待宣判。
“她可能赶不及了,我一个人过来也一样。”
换言之,李墨赶得及的话,就是他们两个一起来看我?翻涌澎湃的心情在瞬间化作一潭死水,我看不清前方,鼻子一阵酸楚。
“这周末我没空。”
“那下周末吧?到时候李墨也能一起来了。”
“你到底要解释什么?有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的?”我说,“我虽然调来香港这边,但我终究还是个实习生,业绩不达标,他们随时会让我卷铺走人的。我现在房子没租,也没报道,眼前一大堆事情等我去处理。”
“你什么时候回杭州?”他终于不再坚持。
“再说吧!我有个电话进来,先不说了——”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总是用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做托辞,可阿彬的回答也永远跟着无关痛痒。他不会心细到去猜测无关痛痒的背后,隐藏的是什么。如果说离开杭州是因为阿彬,那么让我更加坚定留在香港的也还是他。挂断电话之后,我没有一丝伤心。眼前的一切都是扑朔迷离的,可我的内心却无比决绝:明天起必须重新出发。
我一个箭步奔下楼,找了间7-ELEVEn,买了张香港储值卡装进手机。离开时,售货员用粤语叫住了我,通过她的肢体,我揣摩她是提醒我不要忘记取走旧的手机卡。本想潇洒地回她一句“不用了!替我扔了吧!”,但我委实不会粤语,只好默默上前取走旧卡。
回到酒店,我将杭州卡塞进行李箱的隔层,但愿过往的青春就此沉寂吧!
我打开笔记本,开始寻找房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