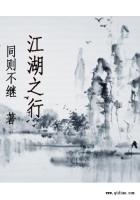意识回到大脑的时候,感觉浑身骨头都似散了一般,回想昏睡前的记忆,心玄那一钹的力道比我料想的更强,只是我竟然没死,而我又在哪里?
我猛然睁开眼,只见眼前飘荡着锦色帷帐,旁边床沿上靠着一人,见我醒来喜不自胜,一语未言,眼泪已盈盈于眶,急忙转过头去。然而我还是看到一双微微肿胀的眼睛,尽快这双肿胀乌青的眼睛略略有损她绝代的容颜,但我还是如此坚定的觉得,这一刻的萧离时如此美丽。
萧离转过身,一只手搭在我的手腕上,竟丝毫不避嫌,半晌脸上终于微微舒展,“你且休息一会儿,我去给你准备一点吃的。”
唉,别走!不能多留一会儿吗?然而我说不出口,终于只是化成一声浅浅的叹息。
不一会儿,一个人掀开门帘,端着一叠东西进来,隔着那么远我都能闻到是我最喜欢吃的五花饭,虽然在醒来之后还能看到他是件开心的事,不过这一刻我还真是想把子超这张脸换成萧离。
“人家亲自给你做的,”子超脸上带着笑吟吟的神情,“这就趁热吃了吧。”
我勉强一笑,想要端过饭碗,身上却一点力力没有,嘴里问道,“青瑶没事吧。”
子超眼中微微一红,“青瑶没有事,只是为了救她,几乎连累大哥丢了性命,我实在——”
“呸!”我一脸嫌弃,“再说这么恶心的话我可是再也不跟你做兄弟了,你要觉得愧疚,以后我俩比武你让我几招——罢了,我才不要你让,怪没意思。”
子超终于忍耐不住,噗呲一笑,我也大笑起来,这一笑不要紧,全身又是一阵疼,只得含了一缕笑意,“现在哥哥给你个报答的机会,喂我吃这碗饭。”
子超一阵忸怩,“大哥,我还从来没喂过别人吃东西。”
我没好气地骂道:“你大哥我算是被谁喂过吗,第一次被人喂吃东西,是你个丑男,我还觉得亏了,有本事去换——”
我一句话戛然而止,原本是骂子超的,不料一句话顺口,竟说出了心事,脸上骤然一红,赶紧转过身去。
“哎呦,我的大哥!”子超语气夸张,“你敢不敢再害羞点,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这么羞涩啊!”
要是身体无恙,我现在绝对一巴掌抽过去,然而我只能打个哈哈,“呵呵,给你个机会闭嘴!”
子超却向我坐近了点,脸上堆满了笑意,我见他笑的如此不怀好意,顿感一阵毛骨悚然,一定是什么吐不出什么。
“大哥,你坦白交代下呗。”果然!
“交代什么?”这个时候我也只有装傻充愣了。
子超显然没有被我一句话遮掩过去,脸上笑容微微收敛,“大哥,你中了那个心玄一记重招,如果不是萧离一整夜输入真气替你疗伤,现在只怕你仍有性命危险。”
竟有这样的事?而我竟然丝毫不知,难怪萧离的眼睑一片乌青,心中感动莫名,夹杂着丝丝甜蜜,耳边又传来子超絮絮的声音,“大哥,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兄弟多年,你的事我也都知道,聆儿——”
陡然听到聆儿这两个字,我心中骤然生出无限温馨,聆儿,你还好吗?多年不见,我真希望你一切安好!
心里在一瞬间竟渐渐凉了下去,子超提及这些的目的我未必不明白,他的话虽然只说了一半,但其中意思我自然懂得,原本我也是这样想的。那些年少时的感情,像是个美丽的童话,而“满目山河空念远”,或许我应该懂得遵循心底的感觉,可是当子超提起聆儿,我才发现,那个纯真的少女在我心中,竟有着这般连我也没有完全懂得的地位。
子超还待再说,我猛然摆手制住,这些天的感觉才像是一个梦,一个我无法一直触及的梦,只要我仍然在脑海里那么深地贮存着那个影子,我便没有资格去追寻这个梦,这一切,或许就是天意。
想到这些,身体感到无限疲惫,我终于含了低沉的声音,“子超,你先出去吧。”
子超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下子变成这样,但他还是什么都没说,放下饭碗出去了。
香味不可抑制地飘到的鼻中,飘到我的心里,我该怎么办?要怎样做才能不伤害到萧离,就如同想要保护聆儿一样,我也一样不想要萧离受半点伤害。
然而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其实我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保护这一个,就必然会伤到另一个,而一切的罪责,最终都会化成绵绵的悔恨,永久地贮存在灵魂里,或许那个,就是所谓成长的代价。
我无力再想,终于沉沉睡去,也许我终究无法躲避,但在这一刻,就让我再逃避一刻。
四匹马驰骋在广阔的路上,青瑶劫后重生的笑容带着分外的美丽,她脸上的神情依然如此坚毅,似乎无论历经多少风霜,她依然可以勇敢地承受。子超曾问及她“天下八部”的事,但青瑶对此一无所知,或许这些只有以后再着力追查了。
秦烈一马当先,面色平静,我不知道他在心里想着什么,他似乎是烈火与寒冰的合体,有时候性烈如火,张扬不可一世,有时候却又像是一潭千年寒冰,难以企及最深处的地方。但他的杀父之仇仍然没报,以他的性子,是绝对不会轻易罢手的,无论是镇南侯抑或是别人。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丝不安,我强行定了定神,抚平了心里的慌乱。
经此一劫,子超和青瑶终于互相敞开了心扉,就此开始他们漫长的旅途。子超说萧离走的时候眼角有一缕掩藏不住的伤痛,她的背影虽然只停留了一瞬间,但仍然能看到这背影蕴含的无限落寞。
只要一想到她独自一人离开,我的心就像是被撕碎了一般,久久无法愈合,我在想起的每一秒,深深地自责和愧恨。然而世间的遗憾之所以是遗憾,正是因为无法弥补,我什么也不能做,能做的只是心底一个虔诚的祈祷,和心底再也难以见到她的无限伤感。
年少时的我们,竟是这样的矛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