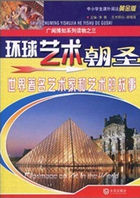秦王泪眼模糊地打量太子一眼,不禁吃了一惊。他那么疲弱,那么憔悴,鬓发已显斑白,瞧上去倒比父皇还老。他知道那白发里就有自己的一份儿;至少眼前的疾病就与自己有关!他顾不得自己泪脸如洗,倒要去擦太子腮上的几滴。哥儿俩便抱头痛哭起来。
哭罢,秦王说道:“大哥呀,你这活命之恩,我是终生难忘呀!”
太子说:“你看,怎能那么说呢?要说恩德嘛,那也是父皇——”
“不不不,我都清楚!我这条命就是你给的!你做的对!我三番五次派人来找你,你一概是闭门不见。急得我撞墙砸窗,亦曾骂过你咒过你。唉!想不到你倒暗暗地为我使劲!替我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却又不叫我知道。特别是那张陕西地图,本是你受了苦累……却把功劳加到我的身上!唉!你让我该怎么报答你呀?”
太子淡然一笑说:“你是谁?我是谁?兄弟之间何言‘报答’二字?”
秦王也笑了:“对对对!常言说‘大恩不言谢’。所以我就什么谢礼都不带。方才你说‘你是谁,我是谁’?你是太子,是明日的皇上。我是谁?我是你的臣下!我就预备着做你的忠臣了!”
他这话倒令太子有点尴尬。既然尴尬,也再无话可说。默了一会儿。秦王知太子有病,不便久坐,便起身告辞。秦王走后,太子又复躺倒。眯上眼,似睡未睡。尴尬慢慢消去了,但另一种情绪——歉疚,或者说羞赧,却代之而起,云雾似地从地下浮起,将他包围。
朦胧中,有一袅袅娉娉的身影从这云雾中渐显出来。
五
向太子袅袅娉娉走来的是秦王的妃子邓氏。
秦王有两位受册封的妃子,一位是元朝时河南王王保保(即扩廓帖木儿)之妹,一位是宁河王邓愈之女。邓愈系开国功臣,战功卓著,洪武帝宠爱有加;但死得早,寿只四十一岁。也许,幸亏他死得早,才未能卷入身后的是是非非,而得以保全名节。
皇太子朱标很相信佛说的“缘”。倘无这次奉旨巡抚西安,他何以进得秦王府?何以见得这位绝世美人?此即所谓:“若此有则彼有,若此生则彼生”也!
为了查清秦王的罪行,那一日他带了扈从官员和兵丁进得秦王府。以他的身份,他可以而且应该各处细细检查。每一栋房,每一条廊,角角落落,甚或花园的每一块石头他都可以而且应该查到。须知大凡要闹事的人,都把很重要的证据——比如谋逆同党们来往的信札,或者“僭越”的器物藏匿在隐秘之处。而且只要看一下宫殿内是否堆金积玉,有没有连皇上都不曾见过的珍宝,即可推定该王会不会非法敛财了。
校尉们早已把王府团团围住。王府外早威赫赫摆好了太子仪仗。什么旗幡伞扇,金瓜玉斧,还有什么金交椅、金脚踏、金水罐、金水盆、金香炉、金香盒、金喷壶、金拂子……不一而足。皇太子从暖轿出来之后,大部分官员自然得候在王府外面,他只带领极少的侍从进去。少不得秦王府的所有妃嫔官吏都得跪迎。太子安排手下的官员与秦王的长史典、簿们忙活公务。看账的看账,查库的查库。他脸上一派严肃。但他在内殿接见秦王的妃嫔和子姪辈时,因毕竟是自家人,言谈便带着些和气了。
这时候他看到的两位王妃,王氏因身世遭遇比较坎坷,所以脸上饱经沧桑,但是神色上显得极是平静;倒是邓妃,别看出身于大家,但可能自小娇生惯养,没经过什么磨难,就显得极是稚嫩了。太子甫说得句“秦王在京里不是被关押,你们不必担心”,那边儿邓妃早已抽咽起来。只见她肩头不断地抖颤,凤冠上的珠翠花蕊随着也摇摆。王妃觉得不是事儿,即用脚悄悄蹴她,提醒她注意“体统”。邓妃就慌慌揩泪,强颜作笑,但脸上的脂粉已被揩洗得一塌糊涂了。
事情就那么怪:弄脏了的脸面应该难看才是,可这张脏面孔却刚好相反,它倒显示了另一种魅力。莫非这便是“梨花带雨”吗?设若这梨花不带雨露,它还会引人注意吗?
应该说太子的宫中不乏姝丽,况且他自己的妃子或也堪称国色。但与这张面孔一比,却是相形见绌。太子心里一乱,竟想不起下面该说些什么了。
陕西省布政使司本已为皇太子——这位最高规格的钦差大臣——安排好了行宫的,那些布政使和参政们经过多番研究,一套套方案比较权衡之后,最终选定的地方是唐玄宗和杨贵妃最喜欢的华清池。但是太子笑微微说句:“华清池好是好,不过,还是留着等皇上来住吧!”他干跪就住进了秦王府。
住这儿既可为国家省些财币,又可减少地方上的诸多麻烦。当他办理公务,特别是调查秦王那些个乱七八糟事情的时候,有时会神不守舍。后来竟意马心猿。邓妃的靓影常常飘然落于他的书案。
他想再见到邓妃。可他和她必须回避。而且,他们单独在一起更是难上加难。
有时候他晨起散步,走到后花园了,即可以透过掩映的花木看到丽影在窗前晃来晃去。他知道那是邓妃。邓妃在夏秋季节是喜欢住在楼上的。在楼上既可御风纳凉,又可凭窗欣赏花园的景致。他和她的目光难免会有所接触。但只在瞬间,丽影便会消失,这反倒增添了惆怅。
每到夜间,太子便觉得十分难熬。没有嫔妃服侍。他也不可能召妓。那些太监又能顶得了什么?那么,每到这种时刻,他便想入非非。在这秦、汉故都,他想到过胭脂水能使“渭河涨”的阿房宫,那“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的景观直令他赞叹秦始皇渔色的气魄;他也想到过能将杨玉环洗得舒舒服服,而令“侍儿扶起娇无力”的华清池。说实话,他的气质与秦始皇嬴政相去甚远,所以他便更喜欢唐玄宗。可惜他现在还不能效仿他。皇帝与太子仅一步之遥,却有天壤之别呀!
有一个夜晚,他就真地梦游了华清池。他亲眼看着杨玉环一件一件剥脱了衣裳,娇睨着他,伸出玉臂说:“陛下你也来呀!”把他也拽入了水中……他不想无谓地折磨自己,便决定做一次唐玄宗。他首先是站在后花园里那株石榴树下徘徊。石榴据说是唐玄宗时代从番国引进的。杨贵妃很喜欢吃。而且他和她还曾亲手种过两株,并发出“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誓愿。恰是石榴成熟时,那石榴一只只将皮儿炸开,露出粉红的籽儿似对人微笑。他摘下一只,掰一粒籽儿尝尝,果然不错,甜入心里。蓦地他想到这石榴籽儿颇似美人的乳头。心里就腾地一热。手中的石榴掉落地上。
他捡起石榴,往楼上的那扇窗户一瞅,又见靓影一闪。人虽瞬间逝去,而窗幔尚在飘拂。他知道那石榴是可以摘的了。
经过审慎思虑,他决定亲自召见秦王身边的人,包括王府长史司、王府护卫指挥使司的主要官员、太监,以及两位王妃。召见是挨个儿单独进行的,而且窗帘严严遮着,闹得人心里惶惶,却又不敢唧咕。究竟秦王爷犯了什么事儿呢?终于轮到邓妃了。邓妃淡扫蛾眉,并未着意地打扮。袅袅娉娉地过来,低着首拜过,便坐到指定的位子上。太子却一声都不吭。邓妃虽低着首,却能看到太子的眼光在她身上热热地扫。
太子说:“烦你沏碗茶过来,可好吗?”邓妃便给太子沏茶。捧着茶过来。轻轻放于桌上。
也许是太子的气息惊吓了她,便有些慌,将茶汁洒出了几滴。此时太子顺势将她的手指抓住……按照太子的预料,邓妃极可能会惊叫一声。那他便会用另一只手去堵她的嘴。接下去邓妃或许会挣扎。这挣扎可能是拼命的,亦可能是半推半就的。他希望的当然是后一种。但如果是前一种,估计亦无大碍,谅她也不会张扬出去的。
但是邓妃既未惊叫,亦未挣扎,而是猫儿似地扑到了他的怀里。倒叫他一时无所措手足。而按照他的打算,他准备比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更具趣味。比如,他可以指一指旁边摆着的石榴果,说一声“妃子,你不请朕尝一口石榴吗?”那么,当她取过石榴的时候,他就可以说,“不,朕说的是你的石榴儿!”最后他就会把她的石榴儿衔在嘴里……然而无须这样的繁琐。当他把她揽入怀中的时候,她已经面团儿似地软了。他尽可以为所欲为了。他就将手径直穿透她的衣裳。去摘石榴。
这次的收获不能说是完美的,但却是成功的。时间不长,恰到好处。况且,因为邓妃戴了凤冠,不便于亲吻,故而鬓发未乱粉面未损,便不会惹人疑惑。
邓妃离去之后,他又觉得意犹未尽。他就计划着第二次的收获。但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比如,他须代表皇上到处巡视、抚慰,不可能每晚都回王府。回想起他与邓妃的巫山之会,除去上面的那回,一共还有三回。但一回比一回缱绻,一回比一回销魂。他真没想到邓妃会玩得那么有趣儿,玩得那么癫狂。她藏有春药,亦有《春宫图》。谁知道哪儿得来的呢?
或许真如俚俗所言:“家花莫如野花香。”吕妃与邓妃一比那可真是清汤寡味!当然,邓妃亦非野花,她同样是御花园中的一朵。他和邓妃缱绻的时候,他也曾抚着邓妃的肚腹说,这也是吾家的土地。而邓妃则说,日后如有生产,也是你家的龙种呢!
于是他便许诺,将来他登基之后,迅即将邓氏接去册为贵妃。邓氏说,这怕是不行吧?太子说,如何不行?这比唐玄宗又算得了什么?朕说行就行!这么一说,邓氏反倒安静了。她把春药和《春宫图》都收起来了。她抚着他瘦削的脸,轻轻摇头说,但愿能有那么一天。“难道真会有那么一天吗?”皇太子朱标从陕西回来之后,大概这是头一回想起他对秦王妃的许诺。现在想起这句话,感觉是那样的不真实,似乎是梦中的呓语。而且,他也相信在西安的王宫里,邓妃同样会感到那是一场春梦。他们没有任何的信物交换(即便交换了信物,又有何用?),因之谁也不会负谁。再说,邓妃是用自己的身子换取了对秦王的宽宥哩。这么一想,皇太子朱标也便不觉得欠了秦王什么了。因此他也便不会因秦王说几句感激的话而感到歉疚和羞赧了。
他倒是觉得应该对自己的妃子吕氏怀有歉疚。尤其吕氏为他喂药的时候,这种歉疚便显得特别沉重。
太子这么想着,迷迷糊糊地听帘外塞率有声,知道吕妃又要来催他吃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