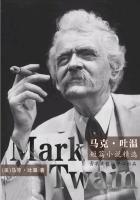如果是我让他出发的,他这颗鼻子会如同谴责般折磨我,会令我愧疚不已的。听到要他出发的命令后,他只说:“是的,司令。”“是,司令。好的,司令。”他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是,鼻子却违反了他的想法,不由自主地发亮。他能够控制自己脸上的表情,但却没能控制鼻子的颜色。鼻子的发亮,流露出他的内心世界。鼻子在无意中向司令表明了它的主人对命令的强烈反对和对生的渴望。
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司令坚决不肯命他以为受到预感困扰的部下执行任务。预感常常是不对的,但战争时期,上级的命令就是对执行命令的官兵的判决书。而亚里亚是军官,不是法官。
军士T 的情况也是这样。
伊斯拉厄尔勇敢无畏,而T 军士胆小怕事。他是我所有认识的人中惟一的胆小鬼。接到上级命令后,他立即头昏眼花,就像有人给了他当头一棒,他会全身僵硬,面无表情,眼睛发亮。
T 的表情与伊斯拉厄尔不一样。当伊斯拉厄尔意识到死亡的来临,受到刺激,鼻子发生异常。T 没有这些变化,他嗓音变了。听完长官的命令,他的不安从眼睛蔓延到脸上,他的灵魂好像脱离了他的躯体,阳世与他之间有了一片毫无感觉的沙漠。我从未见一个人像他那样精神不集中的。
“那一天我不该命让他出发的。”后来司令自责地对我们说。
那一天,司令对他下了命令。T 虽脸色苍白,还微微地笑。当刽子手高举屠刀的那一刻,受刑的人的笑大概就是这样吧。
“你如果身体不适,我代你去吧。”“不,司令,既然已经轮到我了,就该我……”
T 在司令面前直挺挺地站着,目光直视着他,没有任何动作任何表情。
“如果你精神恍惚……”“轮到我了,司令,轮到我了。”“T,你再考虑考虑……”“司令……”
T 就像个木头。亚里亚说:“于是我就让他走了。”
后来发生的事让人难以理解。
T 是机枪手。德军战斗机曾试图冲他们开火,但敌机的机枪出了问题,掉头走了。与T 一起出发的开员和T 之前还谈过话,开员也没发现有什么反常,就在离陆地只有五分钟的时候,他没有接到T 的什么回话。
晚上找到了T 的尸体。飞机的机翼砸碎了他的脑壳。他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全速跳伞。当时他们在盟军的领土上,是没有任何危险的,看来敌军歼击机的偶然出现使他丢了魂,他身不由己地去了。
“你们去换衣服吧。”司令命令我们,“五时三十分准时起飞。”
“再见,司令。”司令做了个动作。因为迷信吗?
我的烟灭了。我在口袋里掏火柴,没找到:“为什么你总是没火柴?”
这倒是真的。向司令辞行后我出了门,问自己:“我怎么总是没火柴?”
度特尔特对我说:“这项任务困扰着司令。”
我想:“他才不会在意呢!”我心里想的这句赌气的话,并不是针对亚里亚司令,我被一件摆在面前、但无人承认的事实困扰着:“精神”的生命是断断续续的,惟有“智慧”的生命是永恒不变的,或基本是这样。我的分析能力几乎从未变过。“精神”不观察事物本身,它观察联系物体间的感觉。比如通过观察人的面相。“精神”从充满幻想走到绝对的盲目。爱产业的人,当他只看到不协调的物体连在一起时,他的末日就到了。爱女人的人,如果在爱情中只见到烦恼、拘束、困难的时候,也就是他的末日了。喜欢任何音乐时,他的末日也就到了。就像当我不再理解我的国家的时候,我的末日到了。一个国家不是所有地区、风俗、事物的总和,不是我能把握的。它是大写的人。当我不理解这大写的人的时候,我的末日来临了。
亚里亚在总司令那儿过了夜。他们进行了只有逻辑性的争论。纯粹逻辑否定了“精神”的生命。然后他筋疲力尽地回来了,遇到了无法疏通的堵塞。回到机组又是无数物质上的匮乏。这些困难折磨着你,就像人无力控制山体倒塌的种种结果。他把我们集合起来,命我们执行一项很难完成的任务。我们是松散的。我们对于他来说,不是圣埃克苏佩里或度特尔特——具有物体的观察事物的,或不观察它们的思考的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人。我们是大物体的板块,需更多的时间、沉默和后退才能装配在一起的。我为怪癖而烦恼,恰好亚里亚只注意怪癖,他只派有怪癖的“画面”到埃勒斯地区。在解不开的问题面前,在混乱中,我们被分成了板块:嗓音、鼻子、怪癖。然而板块是不会表达什么的。
这里说的不仅仅是司令,包括所有的人。埋葬战友的时候,我们爱死人。但和死神没什么关系。死是一件庄严的事。死是与死人的新的关系网。死重新安排了世界。表面上没有什么改变,实质上什么都变了。虽还是和以前一样,但意义不同。要体会死亡的滋味,体会失去战友的感觉,我们就必须想像我们需要他们的时候,但缺少这时候。想像需要我们的时候吧。但已经不再需要我们了。想像互相友好往来的时候吧,却发现它无任何意义。我们必须看到生活的希望。但在埋葬的那天,根本就没有希望,也没有时间。在埋葬死人的那天,他的尸体是残缺的。我们只顾着顿足,和认识与不说认识的朋友握手,考虑丧葬的具体事情,无法集中心思在死人的身上。第二天,我们才在沉默中怀念死去的人。他完整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又完整地离开我们。为了这死去的、我们无法挽留的人,我们号啕大哭,伤心不已。
我讨厌战神的图像。冷酷的战士弹了一滴眼泪,用粗暴的俏皮话掩饰心中的感动。这话说错了,冷酷的战士并没有掩饰,他想讲的确实是俏皮话。
人的素质不是其中原因。如果我们一去不复返,亚里亚司令会十分伤心,他比任何人都要痛苦。只要关系到我们的生死,而不是各种琐碎的东西;只要通过无声能让他重建。因为如果今夜问题雪崩般出现,把我们的死往后延迟,亚里亚司令会忘记为此难过。
因此,我执行任务时,没想过西方激烈的战争,我想的是当前的小事。我想到飞达埃勒斯七百米高空的荒谬、我们想得到情报的虚荣心,想到不慌不忙地着装、打扮好去刑场的事。然后想到我的手套。我到哪里去找回我的手套?我的手套丢了。
我再也见不到我居住的教堂了。我穿上飞行员的服装是为了效劳死神。
3
“快,我的手套在哪儿?……不……不是这一副……到我的公文包里找找……”
“找不到,校官。”“你真笨。”
他们全都是笨蛋。包括找不到我的手套的人和那些决定低空飞行任务的人。
“我向你要一枝铅笔已有十分钟了……你没有铅笔吗?”
“有的,校官。”这一个还不笨。
“用线把笔捆上,线钩在这颗纽扣的孔里……喂,机枪手,你好像一点儿都不急嘛……”
“我已经准备好了,校官。”“哦!好。”我扭头冲观察员说:
“准备好了没有?度特尔特?什么都有吧?你计算航向了?”
“已经计算了,校官……”好,他已经计算好了。一项要作出牺牲的任务……我问你,是否忍心为了无关紧要的情报牺牲机组人员?如果我们有一人生还,带了情报回来,但又传达不到任何人手里……你怎么办……“参谋部应聘请招魂巫师……”“为什么?”
“为了今晚我们能通过,在转动的桌子上,把情报转给参谋部。”
我并不爱唠叨,但我还是小声道:“参谋部,参谋部,让他们去执行毫无意义、白白送死的任务吧!”当执行的是让人失望的任务时,着装的仪式便显得费时很长,我们是在认真谨慎地打扮,送给人活活烤死。费力地穿三层厚厚的重叠装备,穿可笑的服装,接通氧气、暖气、机组成员之间的通讯装置,看起来像旧货生意人。我戴上面具吸气。一根橡皮管像脐带一样把我和飞机联系起来。它是不可或缺的东西。飞机里的温度很热,飞机和人接通了联系。他们还给我和我的心添加了部件,我一分钟比一分钟更臃肿而难以活动,我努力地转身,只要一动,我的关节就劈啪地响,以前骨折过的地方还很痛。
“给我另一副面罩。我已经向你说过很多次了,我不要我的那副面罩,它有点紧。”
因为,不知什么奇怪的原因,到了高空,在地面上觉得合适的面罩,在高空就像铁钳一样夹着骨头。
“校官,我已经替你换过一副了。”“呀!很好。”
我还在一直唠叨,而且一点也不觉得内疚。感觉不公平才要喊出来嘛!再说发发牢骚也没什么。这时我们正穿过那儿,我说过的那里的沙漠中心,这儿只是残余。我一点儿都不感到羞愧地希望奇迹出现,以改变下午要执行的任务。比如说喉头送话器有了问题。喉头送话器是经常坏的!劣货!它坏了,我们就不用执行送命的任务了。
维津校官板着脸向我走过来。他向我们每一个人走过来,在我们绷着铁青的脸准备执行任务之前。维津校官是我们这儿负责与敌机的警戒组织关系的,他负责告诉我们敌机的动向。维津是我喜欢的朋友,可只要看见他我就有不祥的预感。
“老兄,这任务混蛋!混蛋!混蛋!”他对我说。他掏出一些纸,然后迟疑地看着我:“你从哪儿出去?”
“阿尔贝。”“啊!真是混蛋!”
“别说废话了,怎么了?”“你不能出发!”
我不能出发!……太好了,维津!他从上帝那儿找到了喉头送话器的问题!
“你过不去。”“为什么?”
“因为德国的歼击机在阿尔贝上空分三班轮流执行任务。在六千米,七千零五米,一万米上空各有一班。接替的飞机没来,任何一班都不离开天空。遇上敌机马上歼灭。你这是自讨苦吃。而且,你看!……”
他给我看一张纸,他在纸上涂了很难让人理解的说明。
维津最好还是让我安静。“马上歼灭”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它让我联想到交通红灯,违警罚款。而在这儿,违警罚款就意味着死亡。我尤其憎恨“马上”,我感觉我已经被人瞄准,成了靶子。
我努力地冷静下来。敌人为捍卫他们的方位从来就是“立即”、“毫不心疑”的。这全是废话……而且我藐视歼击机。当我降到七百米的高空,D.C.A.就会攻击我,它不会放过我!我突然冒火了!
“你急忙赶来,就是要告诉我,德国的飞机布下天罗地网,我出发是错的!快去通知司令吧……”
维津本可以轻松地让我放心,只要他说上“阿尔贝上空出现敌人的歼击机……”但意思是毫无差别的!
4
一切准备就绪。我们上了飞机。只剩下试喉头送话器了……“度特尔特,你听见我讲话吗?”“听得很清楚,校官。”“你呢,机枪手,可以听见我的话吗?”“我……是的……很清楚。”“度特尔特,你听得到机枪手的声音吗?”“清楚,校官。”“机枪手,你能听见度特尔特的声音吗?”“我……是的……很清楚。”
“你为什么总说:我……是的……很清楚?”“我在找我的铅笔,校官。”喉头送话器没有问题。“机枪手,瓶里的空气压力正常吗?”“我……是的……正常。”“三个瓶子都正常?”
“对。”“准备好了吗,度特尔特?”
“准备好了。”“机枪手,准备就绪了吗?”“准备就绪了。”“好,可以了。”
我起飞了。
5
不安的情绪来于失去真正的身份。在等待我的未来是幸与不幸的消息时,我有种被人抛到虚无中的感觉。事情未解决,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我的态度和感情只是暂时的伪装。时间一点点过去,我却没一点成就,就像时间不能令大树成长。一个小时后,真正的人将进入我的躯体。这陌生的人冲我走来,从外面,像幽灵似的。于是我感到不安。维津的坏消息带给我的不是不安,而是痛苦——痛苦与不安是两个概念。
当然我的时间不再白白浪费。我的作用终于得以发挥了。我不再揣测无法预知的未来,我不再是一个被困在灾害中的人,我对未来又重新充满自信。我用一个个实际行动充实未来。我检查罗经,使它保持三百一十三度,调节螺旋桨的桨距,加热油。这都是眼下要做的有用的事情。就像做家务,白日琐碎的事可让人忘却衰老的失落感,房子也因此变得整洁明亮了,地板也光亮平滑了,空气也清新流畅了。我现在真的在检查氧气是不是流通。因为我们上升得非常快:六千七百米。
“度特尔特,氧气可以吗?你感觉怎么样?”“可以,校官。”
“机枪手,氧气行吗?”“我……是的……可以,校官……”“你没找到铅笔吗?”
我又恢复成了那个按S 键钮,A 键钮,检查我的机枪性能的人,还要……“喂!机枪手,在你的投弹区后面是不是一座很大的城市?”
“呃……是的,校官。”“好,试试你的机枪。”我听见机枪扫射的声音。“没问题吧?”
“没有。”“所有的机枪都没事?”“呃……是的……校官。”
该我射击了。我在想我们胡扫乱射的子弹到哪里去了。在盟友的乡间,它们不会杀人,因为大地是辽阔的。
这样我的每分钟都过得很充实。我现在没有不安的感觉。虽然,我周围的飞行条件会改变,会有不同的问题出现。但我已投入建造的未来中。时间慢慢动作,塑造我,磨炼我,使我成形。孩子教老人时耐心,也不害怕。他是孩子,他玩孩子的游戏。我也在玩游戏,我点算我的世界里仪器,操纵杆,手柄,按键。有一百零三件机件要检查,操控(我几乎在作弊,机枪有两根操纵杆,还有安全销)。今晚我要让留我住宿的农夫感到惊讶。我要问他:
“你知道今天的飞行员检查了多少机件吗?”“我怎么会知道?”
“没关系,说个数吧。”“你要我说多少?”我的这个农夫一点也不聪明。“随便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