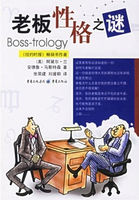经济学家喜欢开自己的玩笑。有个笑话是这么说的:
一个经济学家在路灯下边东找西找。有个好心的路人过来帮忙。路人问经济学家:“你在找什么呀?”
经济学家说:“我在找我的钥匙。”
两个人找了半天,还是一无所获。路人最后忍不住问经济学家:“你肯定钥匙是丢在这里了吗?”
经济学家说:“不是啊,我好像把钥匙落在车库了。”
路人奇怪了:“那你怎么在这里找啊?”
经济学家说:“因为只有这里才有灯光啊。”
经济学家只喜欢看他们能够看得见的东西。遗憾的是,这个世界并非仅仅依靠经济学就能完全看清楚的。
刚上大学的时候,我读到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萨缪尔森说:“要领悟经济分析的优美结构,仅仅需要有逻辑感,和能够对于经济学这样的思维体系竟会对整个世界上亿万人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感到惊奇。”我仍然能够记得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如遭雷击的震撼感觉。从那之后,我就开始不停地学习经济学。
学习经济学,既给我带来了智力上的愉悦,也给我带来了内心的宁静。
我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策划过一套经济学前沿译丛。在丛书的序言中,我写道:
走进经济学的神殿,人们不禁生出高山仰止的感慨。年轻的学子顿时会感到英雄气短,在这个美仑美奂的殿堂里做一名工匠,付出自己一生的辛勤努力,哪怕只是为了完成窗棂上的雕花都是值得的。
我也给《经济学家茶座》写过一篇短文,叫《脑力锻炼》,里面写道:
学习经济学让人乐观而平和。经济学家相信“看不见的手”,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利,在一定条件下,反而能促成社会公利的增加。尽管有“在一定条件下”这一限制,但是我已经觉得这是我见过的社会思想中最乐观的了。学习经济学,让人觉得所有的事情总会有解决的办法,而且这解决的办法不用我们煞费苦心地设计,只要承认人们追求利益的正当性,同时又善于引导人们的逐利行为就行了。经济学充满了机智,它让我们这些平庸的人们充满信心,并且快乐。
但是,当我努力亲近经济学的时候,现实的世界却离我越来越远。读博士期间,我曾在哈佛做过两年访问学生。去哈佛之前,我以为所有的经济学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自由放任”。到哈佛之后,老师才告诉我,所有的经济学问题只有一个答案,答案是:“It depends”(视情况而定)。当时,我仿佛一个刚上岸的水手,踩到了岸上,却感到陆地在颤动,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才算是真实的感觉。数年之后,依然青涩的我到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任务是协助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卡德(Olivier Blanchard),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可是,我越是努力地想用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和教授对话,他越是感到烦躁。他想让我告诉他,中国经济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我却对此一无所知。
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之后,我主要做政策研究。这个工作让我眼界大开,我不再仅仅是在书斋里读书,还要学会去认识现实世界。我在国内到处跑,去过北大荒的农场,下过山西的煤矿,看过东莞的小工厂,也参观过没有一个工人的全自动化车间。我能够和政府官员一起讨论中国面临的问题,如何判断形势,如何设计政策。在这种时候,往往是我向身处一线的同志们学习,他们所掌握的信息量、思考问题的深度,都令我深深敬佩。我在世界各地到处跑,跟各国的财政部长、央行行长一起开会,也向全球顶级的投资经理请教我根本看不懂的衍生金融产品。今天在迪拜,明天在古巴。但当我的兴奋劲过了,想找回经济学,想真心诚意地用经济学的理论解释我所见到的现实世界,却发现经济学已经从当年的朝气蓬勃、乐观自信变得暮气沉沉、犹疑不决。
雾霾越来越浓。路灯昏黄而枯槁。我怎么也找不到钥匙。
算了,我不找了。
我开始了漫无目的的阅读。
我读历史,为的是从历史中看清现在。克鲁格曼(Krugman)曾经说过,经济学家只有一个样本,那就是历史。但历史读得越多,和我的初衷越远。我发现自己找不到一种令人信服的历史规律,反而迷恋上了历史中的偶然性。历史的道路没有交通标示,到处是交叉小径。你可能会看到隐约中有相似的地方,但是,阅读历史的真正收获不是让你感到,原来自古如此,而是让你越读越觉得熟悉的东西是陌生的,简单的东西是复杂的。阅读历史学,能让你更加多思、审慎。
我读心理学,为的是更好地认清自己。随着年岁的增长,你会觉得经济学里那个得意洋洋的“理性人”假设是那么的浅薄。行为经济学在经济学领域突然流行,相信也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感到原来的“范式”太过粗鄙。行为经济学的背后,是脑神经科学的飞跃发展。人们对自己的认识逐渐清晰,但也更加深切地看到,我们的认知模式有那么多的缺陷。过去的自大狂妄,让我们羞愧难当、面红耳热。阅读心理学,能让你更加谦卑、自省。
我读地缘政治学,原本是当做一个副业,想在国际政治领域也有所涉猎。或许纯属误打误撞,地缘政治学和主流的国际政治理论其实格格不入。地缘政治学不是沙龙里外交官和贵族们的学问,它是风尘仆仆的旅行者的见识。如同我初读戴蒙得(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一样,我这才明白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和无助。拿破仑那么不可一世,他可曾战胜俄国的寒冬?中亚草原上的匈奴骑兵被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这条鞭冥冥中在何人之手?
我自许为职业读者,和职业运动员每天都要训练一样,读书是我每日必做的功课。尽管阅读的范围看似漫无边际,但读来读去,我发现,有价值的阅读似乎只是为了教导我们要更加虚心、更加谦卑。
读得多了,我也曾经想把自己的心得写成书。其实已经有了写作的计划。我计划写一本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书,以国际金融为窗口,眺望历史的风景。我也想过写一本关于地缘政治的学习笔记,记录下来我对地缘政治的理解,并通过写作,把我感到陌生的一些地缘政治热点地区了解得更清楚。我还想过写一本颠覆理性人假设的书,但我深知这一命题的宏大,远非现在的我所能驾驭,也许要再等十年二十年才敢动笔。
我还算是一个勤奋的写作者,这些年已经动手写了一些类似素材的东西,零零星星地发表在《SOHO小报》、《信睿》、《财经》等杂志上。原本希望当素材的量足够多了,就把它们串起来,写成书。我曾经在《财经》上写过一篇《半生缘》,透露过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和写作计划。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我仍然一本书也没有完成。
人生已经过半,除了一如既往的浑浑噩噩,我已经开始感觉到一些紧迫感。之所以把以前写过的一些素材类的零七碎八的东西攒在一起,出这本书,也是因为我不知道何时才能完成自己的写作计划,想起来就觉得非常焦急。这本书只是一个半成品的仓库,堆得乱七八糟。对我自己而言,它时刻是个提醒,让我想到还有那么多许诺没有兑现。我把那篇《半生缘》也收录在这本书中,做本书的跋,好让自己每读一遍,就惭愧一次。
这些年来,我写的应景式的财经评论其实也不少,但那些都是浮云,我就全部弃之不顾了。我会继续自己的探险式的阅读,一任海风把我这艘没有桨的小船带到未知的目的地。我会回来的,因为我依然深深眷恋着经济学。这里是我的故乡。但希望岁月切磋琢磨,让我能有改变,经济学也有改变。
如果你遇到经济学,请告诉她,我出门远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