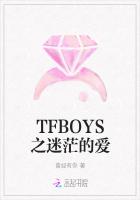看完烟火,景澜揣着一颗无比崩溃的小心脏护送一人一狐回了白苏的阁楼。躺在床上硬生生睡不着。
而另一边,玩了一晚上的花明幽很快就抱着小狐狸进入了梦乡。床上的小人儿刚刚睡着,小狐狸就睁开了双眼,一团紫光闪过,漓止就出现在了床榻上,轻手轻脚的把花明幽抱进自己怀里,唇角勾起一个温暖的弧度,柔和的眼神落在她的脸上,只有她还真真实实的在自己怀里,他才相信她真的回来了,而不是自己的一场美梦,梦醒了,她就不在了。现在,她安安静静的躺在自己怀里,身上淡淡的馨香传入鼻翼,让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心。
清乐姨说,在神界,自他离开,她忘了他之后,就一直喜欢浅碧色的衣裙。如今她虽然没了记忆,这喜好却是没变,活波精灵的性子也与当年一样,看到他自己才又活了过来。不再和她消失的千年里一样过的如同失了灵魂的木偶。
那千年里,他亲自动手种了一大片的扶桑花,传说日出于扶桑之下,拂其树杪而升,因谓为日出处,可他在扶桑林呆了千百年却没有感觉到丝毫的温暖,只是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冷冰冰的,只是偶尔他醉酒的时候,能在梦里见到他的阿音,小时候调皮可爱的阿音,琴瑟殿前不认识她的阿音,殒神台下决绝跃下的阿音,还有那一声带着泪水的“玥玥,对不起。”他伸出手,却只抓到一手冰凉的空气。然后惊醒,看着满地红如鲜血的扶桑花瓣发呆。
那片扶桑林,除了他,也就只有几人可以进来,那里是他为她造的,承载着他对她的回忆,他不许无关紧要的人来破坏,也是他给自己造的牢笼,把他自己一关就是千年。
千年里,他讲妖界诸事都交给了景澜和凌九,凌九主内,景澜主外。凌九是外公交给他的人,才能十分出色。他扔下了担子,做着挂名的妖王,偶尔出现在妖族的大型庆典,然后又回到扶桑林,兴致来了便吹吹竹叶曲。
在扶桑林里,他不问世事,几乎什么都不关心,什么都不在乎,只是景澜来的时候会告诉他一些事情。景澜说在他自甘成妖离开神界之后,陌桑也离开了神界,去了万佛山,再也没回去过,百花仙子挽泱成了名存实亡的二皇妃,被天帝软禁在她自己的宫殿,连陌桑的府邸都不允许她踏入。
据说挽泱曾求了天帝让她去万佛山找回陌桑,天帝允了,挽泱去了万佛山,却被陌桑拒之门外,挽泱在山下苦苦等了整整十年,每日都去万佛山求见陌桑,后来,陌桑终是见了她,可当挽泱带着惊喜见到他的时候,他却面无表情的告诉她,他已经决定放弃神界二殿下的身份,遁入佛门,已经写好手书,请她带给天帝。
当面色苍白的挽泱独自归来,还带回了陌桑的手书呈给天帝时,天帝神色不动,不辨喜怒,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既然神界已经没有了二殿下,二皇妃也没有必要存在了,轻描淡写的剥夺了她费尽心机的来的身份,讲她送回了王母身边,只是,从此以后,她也不再是百花仙子,不过一个普通神女罢了。
而风音的师傅清乐上神大战归来,听闻此事,便闭门谢客,放出话来,若是挽泱神女见到她,请务必绕道而行,不然发生了什么可别怪她。他父君岚述也从此幽居宫中,陪着冰棺中的母亲,不问世事。
听到这些。他也没什么反应,挽泱神女,他并不同情,若不是她自私的为了天音石害了阿音,伤了这么多人的心,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阿音身殒魂灭,她还活着就该烧香拜佛了,他还觉得这惩罚太轻了,现在他却觉得天帝做的很好,他要挽泱好好睁大眼睛看清楚,阿音一定会幸福快乐的。
阿音当年时时刻刻带在身边的疏风剑,清乐姨本想自己留着,后来却托了一位叫东泽的小神君,万里迢迢的送来了妖界,亲手交给了他。
东泽来的时候,漓止正侧躺在一地的扶桑花瓣上,支着手发呆。
那位小神君说,他是阿音的朋友,似乎是知道了他和阿音的事情,絮絮叨叨讲了很多他离开的两万年里有关阿音的事情,他说阿音曾经偷偷挖走了八重天玉池里的好几株洛桑,可惜都被她养死了;她很喜欢吃碧烟果,自己在琴瑟殿里种了好多棵果树;她喜欢舞剑,经常拉了人和她切磋;她喜欢捉弄自以为风流潇洒想和她结为连理的神君,总是把他们弄的灰头土脸,自己乐的哈哈大笑;她睡觉的时候最讨厌人打扰;她对紫色和扶桑花有一种很复杂的东泽自己看不懂的感情;她喜欢美食,偶尔会偷偷溜下神界去人界的酒楼大吃一顿;她心情不好的时候会不说话,一个人窝在某个地方;她喜欢看星星,过几天就会爬上房顶躺着看星星,有时候还会拉个人陪他,然后看着看着就在房顶上睡着了;她还喜欢吹叶笛,吹的曲子也好听……
东泽小神君讲的时候,景澜也在,两人默默的听着他细细说着那位神女的点点滴滴,说了大半天,那位神君才停了下来,又看了眼面无表情的漓止,道:“清乐上神说,其实你才是最喜欢风音的,只是不能够陪着她成长,错过了她很多东西,我想,这些你都不知道,可是我觉得,你是想知道的,所以,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疏风剑已经给你了,我也该回去了,岚述上神让我转告你一句,他跟你母亲现在很好,可以一直在一起,你一个人要好好照顾自己。”
漓止沉默着点了点头:“谢谢你。”顿了顿,又道:“景澜,替我送送他。”
带景澜领着东泽小神君离开了,已经看不见了,漓止脸上才涌出一抹深沉的悲色,一滴泪水从眼角钻出,划过脸颊,落在他黑色的衣袍上,消失了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