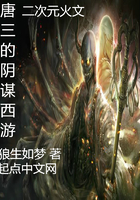爱的一方,永远是被作践的一方。被作践,却甘之如殆。
在外人看来,这就是智商为零的行为。
大街上的人来来往往,步履匆匆,我坐在街边的石凳上,榕树撑出一把巨大的绿伞。我的眼泪一直流,有行人好奇地打量我,有人直直地走过。
我拿出纸巾,把泪水擦干。我擦了一整包纸巾,却都没能将泪水擦干。我曾经那样的挣扎过,可终究还是陷了进去,就像一个错入沼泽的人,当双脚刚沾到泥的时候,误以为抬脚就跳出来了,却是左脚抬起来,右脚深陷了几寸,知道情况不妙,慌忙挣扎,却越挣扎得厉害,就陷落得越快,终于淹过腰,漫过心脏,封住嘴巴,堵住鼻子,终究再也透不过气来,眼睁睁地,灭顶消亡。
我直接坐地铁,回了家。在爸妈面前,我若无其事,该吃饭就吃饭,该睡觉就睡觉。玩了四天后,决定回Z市找实习单位。毕竟要写毕业论文,要回学校答辩。其实也并不是因为这些,言毓他现在让我滚,但他又说过期限是毕业,所以我并不敢滚远。
我知道,其实都是我的一厢情愿罢了。
这几天,每天晚上我都会做噩梦,那场与歹徒搏斗,让我深受刺激,白天我没觉得怎么样,但睡觉后,总会做着同样一个噩梦。也不都是完全一样,场景会变幻,连歹徒的模样也不尽相同,甚至梦里面浩林都没有出现过,唯一相同的就是,刀光剑影,言毓将我死死地护在身后,血液横飞,他一次又一次地倒下,我几近崩溃地哭醒。醒来的时候,却是更加哭得肝肠寸断。有多少次我差点没忍住就跑上医院去,只是方澜澜说得一点都没有错,我足足两次,害他差点丢了性命。一个人只有一条命,能经得起多少次这样的折腾。或许言毓也是怕了,他可能希望我有多远滚多远。
我在姐姐家,用手提电脑,上人才网找实习单位,姐夫让我去他公司实习,当文员。我一点也不感兴趣,而且我性格丢三落四,不适合当文员。
对于我和言毓,姐姐始终希望我给她个交代,我觉得其实也没什么好交代的。或许她是担心我,我简单明了:“我们在一起了。”
或许也只有这句话能够掩饰一切。
“姐,我希望你暂时不要告诉爸妈,也不要干涉,指不定哪天我和他就分手了。你知道的,年轻人,说分手就分手的了。”
“你们要在一起,我不阻止,既然在一起了,就好好珍惜,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闹分手。他的家人是不是不同意你们在一起?”姐姐叹了口气:“看什么时候带他过来,和我还有你姐夫一起吃顿饭。”
“我和他要是决定结婚,再带过来和你们吃饭。”我觉得疲惫。
之前暑假的时候我有去过英语培训中心当助教的经验,我在网上看到北州区那里有见小明星英语培训中心招助教。但我只是实习半年,不知道他们愿意不。因为学校要求,实习单位要填写实习报表和盖章。
我拨通了培训中心的电话,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他们中心极度缺乏人手,立刻就答应了,当我们在商谈什么时候面试,我电话响了一声,我看了一下,是秋姐的来电。
我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我想都没有想,手已经直接断了培训中心的电话,接通了秋姐的。
言毓满身都是血的画面,充斥着我整个脑,我突然心里十分恐惧:“喂,秋姐,什么事?”
“易丫头,你在哪里?现在能过来医院吗?”秋姐声音十分焦急和疲惫。
“好,我马上过来。”我拿起包包就跑。
要灭顶就灭顶吧,反正我现在也难受得半死不活,与其这样,不如趁早了结,要痛就痛个干脆。反正我是失过一次恋的人,心肝脾胃肺都痛上一轮,只要熬过去了,天空还是那么蓝,海水依然那么绿。或许我现在只是被爱情的荷尔蒙,蒙蔽了心智,好比在北极,零下三十度,舒服地泡在热意融融的温泉里,谁会介意起来时,那短暂的冰寒刺骨?只是当起身时,承受冰刀剜肉的寒意时,谁不埋怨曾经贪恋泉水的温暖?
人就是这样的矛盾。
就像我现在,悲喜交加。一想到要见到他,突然心里就喜滋滋的甜,可是想到秋姐那焦急的声音,我却又愁肠百结。
我直接开了姐姐的车到医院。
去到,发现左右门神依然守在病房门前,我准备进去,没想到他们将我拦下来了。
我十分焦急,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连忙说:“秋姐叫我来的。”
那两位门神像是没听见我的话一样,昂首挺胸,面无表情。
我只得打电话给秋姐,可是秋姐竟然挂断了我的电话。来看,秋姐是偷偷给我打的电话。那秋姐为什么打电话给我,之前阿建扛我出医院,我挣扎着抓住椅子把手不放,秋姐还帮着掰我手。她的立场很明显!到底是出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才让她连立场都变了,来偷偷打电话给我?
是言毓出了什么紧急状况吗?可是出紧急状况应该叫医生,打电话给我干什么?难道是他病危了?怎么不可能!不可能!之前言毓手术过后我问过主治医生,医生说他身上的都是皮外伤,不过背部的伤口比较深,他晕倒是因为失血过多,总的来说并无大碍。
只是心里那个可怕的念头,让我失去了理智,明知是以卵击石,仍然扑上去和保镖厮打,他们抓住我,就像捏住一只蚂蚁一样轻松,我张开嘴要大喊大叫,其中一个保镖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死死捂住我嘴巴。
突然门就打开了,竟然是老爷子,他脸色凝重,夹杂愠怒。他身后紧跟着是方澜澜,她却是面如死灰,像受到了极为沉重的打击一样,我的心猛地一沉,瞬间泪水就哗哗地流,嘴被严严实实地捂着,只能发出‘唔唔唔’的模糊声,我激烈地挣扎着。
老爷子终于抬眼看我,这是他第一次拿正眼看我,他目光冷冷的,带着莫测的深意,扫视了我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