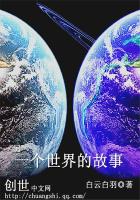我被青石板刺骨的寒意冻醒,期望的美梦是没做成,在梦里依旧瘪着肚子找吃的。
那群和我一样露宿的迁客也陆续醒来,太阳使大地渐渐回暖,新的一天开始。可这于我并非好事,我宁愿夜再长一点,我宁愿不醒来,这样我就可以多苟延残喘一些时日了。除此,在梦里是能找的吃的的,大饼想多少有多少,即使不能充饥,能看到也是不错的。
新的一天去哪里呢。继续向南?去天国?我布袋里的大饼怕是支持不了我到下一个城了,我不要死在荒野喂豺狼,万一死了,我可不一定能像遇袭时罹难的那三口之家一样有幸,能遇上一群好人,挖个好坑让我好好安息。我下定决心不走了,死也要死在这繁华胜地。我也幻想过,要是那家师傅收学徒或者茶楼酒肆收伙计,只要能给口饭,我肯定会使出念经的十倍力气好好干的。只可惜这真的只能是幻想了,这朝不保夕的年代,到处缺粮闹饥荒,还好这鄂地算是富饶之乡,没有遍地灾民,但谁家又愿意凭白多出一张嘴来分享本来就紧巴的米缸。
先走走吧,或许天无绝人之路,天上掉馒头未可知也。就像昨天的那条邋遢狗,它肯定也没想到狗shi运撞到它头上吧,在剩饭残羹都没有的年代里竟然捡到一个大米饼。
我从东向西走,太阳照在脊背暖到心房。去过的没去过的街道都去走走看看,反正一切都是那么新奇那么好。
我在荒郊野外飞机袭击时没遇险,反倒在这昌平盛城,和谐街市上被绑架了。
在我正细细品赏这略带古韵的旧城时,两个穿着灰布袍子的汉子迎面走来。起初我倒是没在意,光天化日下,敢在闹市街头打劫不成,再说,我一个穷到食不果腹的贫僧有什么可打劫的,莫非是看上我口袋那一个半大白饼子了,看那两人的行头,倒不至于是为了个大饼的亡命之徒。
他们一步步靠近,这下我才看的真切,他俩人的目光一直都是聚焦在我身上。这时我心来开始发怂。我把我的木棍攥的更紧,原来想着这木棍也就用来打打野狗,做做手杖,也算是物尽其用了。没想到它真的要顶梁算数上阵当武器了,而且首战就是两个恶茬。
它没能伴我大杀四方,首战告捷。相反的,我被一招制敌了。
两人逼近我三步之内了,高个儿给略微矮胖的男人点了示意,我也用运力准备挥棒出击。俗话说先发制人的,可我是先发了,但没有制人。我的一棒用力向着那个矮胖子腰间挥去,我想着以他笨拙的身躯,怎么也是躲不了我这出山首招第一棒的,可事实是他根本就没打算躲。一棒打在他腰间上,他那层厚厚赘肉倒是充当了保护层。他顺手一掣,再一使劲,我的武器也被掳去。
就这么一招被制,我怎能服气,好歹我也是跟着师父苦练三年呢。看来我又是给师父丢脸了。可讲实话,我就这样乖乖被擒并不是打不过那两人,是真的饿汉难挥无力之拳啊,真正要是我肚里有两个大花馒头顶着,我岂会被这种小脚掳去。再说,即使我是双拳难敌四手,我还有腿不是,我还能跑,就这货色能追到我吗。可现在别说连跑的力气没有,就是跑的欲望都饿没了。
正好呢,他们既是抓我,看来我还对他们有用。那我还愁什么,他们肯定不会让我活活饿死,我这也不就解决了伙食问题吗。
高个子从袖里掏出一块黑布,揉个圆团就塞到我嘴里。两个一左一右,反手架起我的胳膊拖着就走。
我就这样被绑架了,我想喊的,但是想想他们敢在大街上公然绑我定时无所畏惧的。他们堵我嘴也定不是因为怕我喊叫招来麻烦,想必是嫌我喊叫烦躁闹心。看来倒是行家老手,颇有经验。
我很配合,不吵不闹的被他们拖行到目的地,也好省了我走路的力气。
不巧的是,这里我来过。可这次是被人当成俘虏押来的。
又是永兴当铺!
我被两人从后门拖进去,上台阶时一阶一阶的青石板磕破了我的脚踝。更令我雪上加霜的是,我是被反吊起来审问的,脚被绑起来吊在横梁上,头朝着地,这样一来绳子绑我的触点正巧挨着脚踝的伤口。就这样吊着倒是不怎么打紧,只是反悬着晕到恶心发吐。他们用皮鞭抽在我身上,这也不打紧,我在我的土坑里摔了三年,这点鞭子还不至于让我喊娘。要命的是,鞭子抽在身上,我的身体就在空中乱晃,而粗脏的麻绳就跟着这节奏在我伤口上一轻一重的摩擦。
一开始我只是被吊了起来,并没人理我。我开始自己慢慢适应着这倒栽葱的感觉。恶心,眩晕,在这迷乱里我看到了那个赏我大饼的伙计。我看着他,他也看到我了,瞥了一眼就过去干自己的事了。
此刻被悬在横梁上的我竟对那圆帽的伙计没有丝毫仇意,他只是个伙计吧,绑架我肯定不是他的注意,实施绑架他也没来参与。我就这样没有丝毫根据的笃信他是这帮恶人里那个善心未泯的好人。仅仅是因为他赏我的大饼吧,即使缘由此因,那我还是应该感谢他的,不然我现在连活着被倒挂的机会都没了。
我是饿晕疼晕抑或是恶心到眩晕,我不得而知了。但我清醒知道我是怎么醒的,一桶凉水从我裆部灌下,伴着冲刷了衣服和我身上垢污的浑浊液体流到头上。比起早上从青石板上冻醒,这凉意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凉在身,更寒于心。昨日柳树下我吃大饼时还想着来点凉水,这下真是来了,一来就是一桶。
我此刻是真的清醒了,这是我此生为数不多的几次正真彻悟心扉似是能洞察万物的清醒时刻。我没想就知道肯定是跟我昨天送的药有关,莫非是混了脏污的药吃出问题了。我一转念,肯定不是,这里狼窝哪有什么卧病的老母亲。
审我的人到了,倒映进我眼帘的人,令我惊异但也是预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