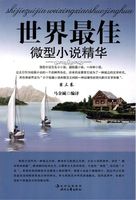余世杰摇身一变成了余老板。他从政府公务员蜕变成了一个商人。
做商人与做公务员截然不同。公务员要克己奉公,收敛自己。最紧要的是守纪律和本分。
不该问的事不问,不该说的事不说,上面让干啥就干啥。
要从思想深处意识到自己是庞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不能越雷池半步,举手投足都要中规中矩。只有这样,才能在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中获取升迁的机会。
商人则必须张扬,自己也是要推销的一部分。要学会包装。只有予人信任,才能取人钱财。干任何事情都要出奇制胜,不能循规蹈矩。领先一步,才能比别人赚更多的钱。商人还必须有永不满足的性格。征战商海,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旦安于现状,就会被时代所抛弃。余世杰里里外外像换了一个人,作为公务员的余世杰已经不存在了。
他所有的服装都从香港的名牌专卖店订购,衬衣永远熨得服服帖帖。每天早晨都让发型师把头发吹得一丝不乱。
人要衣装,佛要金装。
余世杰变成了一个风流倜傥的商界大亨。
余世杰认为金钱不过是银行账号上显示的数字,总不能打开保险柜让客户看自己有多少钱。只有显示出实力,做生意才能事半功倍。他从不吝于花钱,商人就是要能挣会花。一台全新的奔驰500黑色豪华房车更是增加了余老板的威仪。车牌号码是广东人认为最吉祥的五个8。
龙口电子厂使余世杰迅速完成了原始积累,但要凭这点家底实现余世杰的抱负,却是杯水车薪。
任何商业活动都是一种资本再生的过程,要想取得超常的发展,必须有打破常规的思路。
因为,任何一个行业的暴利阶段都很短,残酷的竞争会使很赚钱的行业很快变得不那么赚钱,直到勉强维持。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小商贩终其一生只能守着一家小杂货店苦熬,而不能发展成为连锁超市的原因。
余世杰深谙其中的奥妙。他从来都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并且不只用自己的鸡生蛋,还是惯于借鸡生蛋。
余世杰的第一步棋是向银行借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银行的审贷手续非常宽松。
凭着龙口电子厂的商誉,货如轮转的繁荣和余世杰在鹿港金融界的关系,源源不断的贷款流到了龙口电子厂的账户上。
长袖善舞,多钱善贾。
有了钱就有了一切,余世杰也有了大展宏图的资本。
余世杰的第一个目标是在鹿港建一家五星级的大酒店。
当时的鹿港已经撤县建市。但城市的功能却还相当脆弱。
一座城市代表着文化,更代表着历史,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鹿港因其发展速度太快总显得有些土头土脑,不能完全洗掉暴发户的痕迹。
偌大的鹿港连一座像样的涉外酒店都没有。
余世杰认为星级酒店是现代城市的一种象征。
每次余世杰出差,都要住当地最高档的酒店。
其实酒店是人的居住环境的一个大倒退。
人自从走出山洞以后,对居住环境的私秘性要求越来越高,人所追求的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是背山临水,是独门独院。
但酒店却把有钱的旅人赶到一块儿,让他们像蜜蜂一样门对门,家挨家。只是提供两张床,一些摆设和家具,一些生活用品,却收取每天数百元乃至上千元的高额费用。
但余世杰觉得发明豪华酒店的人简直是商业天才。
酒店的不可替代,不在于它为人们提供了餐饮和娱乐的场所,而在于它为商人提供了表明身份的名片,提供了社交氛围。
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有办事处,商人的商务活动也大都是安排在酒店进行的原因。
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余世杰在天坛东里的一家地下人防工程改建的招待所挨过了三天两夜,每天早晨,他走出房间,仿佛老鼠钻出地洞,来到大街上,才有一种回到人间的感觉。
但当余世杰以余老板的身份再进北京,住进北京贵宾楼饭店,清晨拉开窗帘,遥望长安街上的车水马龙和天安门广场猎猎飞舞的国旗,则令他平添指点江山的气概。
人的处境不同,对世界的看法也会不同。
乞丐会对冰天雪地充满幽怨,富翁则觉漫天飞雪诗意盎然。
“看来,只有中产阶级眼里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余世杰深有感触。
余世杰建酒店走的是一条捷径。他瞄上的目标是在建中的鹿港华侨大厦。
华侨大厦曾经是鹿港市的市长工程之一,雄踞鹿港市最繁华的中山大道。
第一届鹿港市华侨恳亲大会举行的时候,散居世界各地有钱有势的鹿港侨胞都衣锦还乡,他们看到鹿港市没有一处像样的接待场所,便向市政府当局提出建一座华侨大厦,作为鹿港市华侨的永久性活动场所,平时也可向客商和旅游者开放,建成一座涉外旅游酒店。
各地华侨富商认捐了两千万港币。
市长现场办公立即拍板,土地由市政府无偿提供,资金不足部分由市政府交际处向银行筹借。
谁知好事多磨。
华侨大厦的地上工程刚建了两层,国务院就发出了明令禁止各地党政机关以各种形式参与兴建楼堂馆所的通知:立项的必须撤销,在建工程一律缓建。
华侨大厦变成了烂尾楼。
矗立在市中心这一堆钢筋混凝土垃圾,仿佛是鹿港脸面上一块难看的伤疤,任凭雨打风吹,成了鹿港市各届领导的一大块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