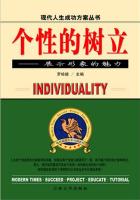受过一些心理学训练的医生和所谓身心学家发现的东西会多一些,对于正常一词的使用也会少得多。的确,许多精神分析家甚至说没有正常的人,即,没有绝对没病的人。这就是说,没有什么是完美无瑕的。这种说法相当真实,但于我们的伦理学研究却无多大帮助。
受过一些心理学训练的医生和所谓身心学家对于“正常”一词的使用会少得多,因为他们发现的东西会多得多,还不能说它已经很明确或者有确凿的证据的可靠支持。相反,应该说它是一种发展缓慢的概念或理论,似乎越来越有可能成为未来发展的真实倾向。
关于正常这个概念的发展前景,关于一般化的,广泛人类的心理健康的某种形式的理论将得到发展,它将适用于整个人类,而不管人们的文化和时代背景如何。无论从经验还是从理论方面来看,这种情况都正在发生。新的事实、新的资料促使了这种新的思想形式的发展。
德鲁克发表这样一种观点:自从基督教创史以来,有大约四种连续的观点或者概念一直统治着西欧。这些观点表达了寻求个人幸福与健康所应采取的方法。其中每一个观点或者神话都竖立了一种理想的典型人物;并且设想,如果效仿这个理想人物,个人的幸福和健康一定会实现。中世纪时,圣职人员被视为理想的典型,而文艺复兴时期则换成了有学识的人,然后是实用主义和英雄主义交替上场。
但是不管怎样,所有这些神话都失去作用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新概念正缓慢地在最先进的思想家和新概念的研究者心里发展着,并很快成熟起来。这个新概念就是心理健康的人,或者具有真正灵魂的人,实际上也可称为自然的人。德鲁克提及的那些概念曾对他们的时代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并且,这个概念将对我们的时代产生同样深远的影响。
我们来简要地阐述心理健康的人的实质,虽然这个新概念刚开始或许有些教条化。
首先,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念:人类有自己的基本性质,即某种心理结构的框架,可以像对待人体结构那样来研究、讨论它;人类有由遗传决定的需要、能力和倾向,其中一些跨越了文化的界线,体现了全人类的特性,另一些为具体的个人所独有。一般看来,这些需要是好的或中性的,不是罪恶的。
第二,我们的新概念涉及到这样一个观点:完美的健康状况以及正常的有益的发展在于实现人类的这种基本性质,在于充分发挥这些潜力,在于遵循这个暗藏的模糊不清的基本性质,在于充分发挥这些潜力,在于遵循这个暗藏的模糊不清的基本性质所控制的轨道,逐渐发展成熟,这是内在发展,而不是外界造型的过程。
第三,一般的心理病理学现象很明显是人类的这种基本性质遭到否定、挫折或者扭曲的结果。根据这个观点,无论什么事物,只要有助于向着人的内在本质的实现有益地发展,就是好的;只要阻挠、阻挡或者否定这种基本性质,就是坏的或变态的;只要干扰、阻挠或者改变自我实现进程,就是心理病态。那么,什么是心理治疗呢?或者干脆说,什么叫治疗?无论什么方法,只要能够帮助人回到自我实现的轨道上来,只要能够帮助人沿着他内在本质所指引的轨道发展,就是治疗。
这一概念表面上类似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和斯宾诺莎主义者的理想。的确,我们必须承认,这一新概念和过去的哲学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对于真实的性,我们远比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了解得多。总之,我们足以理解他们的错误和缺点是什么。
各种流派的心理分析家,特别是弗洛伊德,发现了古代哲学家们所缺少的知识以及他们的理论中具有致命弱点的知识。我们已经特别从动力心理学家,还有动物心理学家以及其他心理学家那里,获得了大大扩充了的关于人的动机,特别是无意识动机的知识。其次,我们拥有非常丰富了的关于心理病理学及其起源的知识。最后,我们从心理治疗家,特别是从对心理治疗的目标和过程的讨论中学到了许多东西。
我们可以同意亚里士多德关于良好的生活在于按照真实的人性生活的假设,但也必须看到,他还不了解真正的人性。在描绘人性的这种基本性质或固有结构时,亚里士多德全部能做的,就是观察自己周围的情况,研究人,观察人们的表现。但是,谁要是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只从表面来观察人,他最后就一定只会得到静态的人性的概念。
亚里士多德所能做到的唯一事情,就是描绘出一幅属于他自己的文化和时代的良好人的图画。人们还记得,在亚里士多德关于良好生活的概念中,他完全接受了奴隶制的事实,制造了致命的错误的假定,即,仅仅因为一个人是奴隶,这就成了他的基本性质。从而,作奴隶就是他良好的生活。这完全暴露了在建立什么是良好人、正常人或健康人的观念时,依据纯粹表面观察所具有的弱点。
如果我来总结、比较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和K·哥尔德斯坦、E·弗洛姆、K·霍尼、K·罗杰斯以及其他人的概念,我所要坚持的基本区别是,我们现在不仅能够看到人是什么,而且知道他可以成为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能看到表面,看到现状,而且也看到实质。我们现在更加了解人们隐藏的情况,以及被压抑、忽略、忽视的状况。我们现在能够依据一个人的可能性、潜力以及可能达到的最高发展,而不是仅仅依靠外在的观察来判断他的基本性质。
我们从这些动力心理学家处学得,单凭才智或理性是不能达到自我实现的,这也是我们与亚里士多德相比的另一优点。大家都说,亚里士多德为人的能力排列了等级,理性在其中占据首位,并且不可避免地随之提出一个概念:与理性相对立的是人的情感和类本能的性质,它们一直在相互冲突、厮杀。
但是,通过对于心理病理学和心理治疗的研究,我们必须大大改变我们对心理学意义上的有机体的看法,平等地尊重理性、感情以及我们本性中意动或者愿望和驱动的一面。
而且,对健康人的经验研究向我们证明,这些方面之间根本没有冲突,不是对立的而是协作的。健康人完全是一个整体,或者说是一体化的。只有神经病人才与自己不一致,理性与感情才发生冲突。这种分裂的后果是,感性生活和意动生活一直误解和曲解了理性。
正如E·弗洛姆所说:“理性由于成了看守自己的囚犯——人性——的卫兵,它本身也变成了囚犯,因此人性的两个方面——理性和感情——都是残缺不全的。”我们不得不赞成弗洛姆的观点,他认为,自我实现的发生不仅依靠思想活动,而且取决于人的整个人格的实现,这个完整的人格不仅包括该人的智慧能力积极表现,而且包括他的情感和类本能的能力的积极表现。
我们如果对于人称为好的某些条件下可能成为什么状态拥有很可靠的知识,并且假定,只有当一个人实现了自我,成为他自己时,他才是快乐、宁静、自我认可、坦荡、身心一致的,那么就有可能也有理由谈论好与坏、对与错、有益或有弊。
我们凭经验就可以回答那些技术哲学家的反论,如幸福未必比不幸福更好。因为,如果我们在相当多样的条件下观察人,就会发现他们自己而不是观察者,会主动地选择幸福而非不幸,选择舒适而非痛苦,选择宁静而非担忧。一句话,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选择健康而非疾病(然而条件是,他们自己进行选择,而且当时条件属于后面要讨论的一种)。
这也解释了众所周知的关于手段与目的价值命题的一般哲学缺陷。如果你要达到目的X,你就应该采取手段Y。“如果想长寿,你就应该吃维生素”。我们对这个命题有一个不同的解释。我们依照惯例也能知道人需要什么,比如,需要爱、安全、幸福、知识、长寿、没有痛苦等等。那么,我们可以不说:“假如你希望幸福,那么……”而说:“假如你是一个健康的人,那么……”
下面有一些完全符合事实的经验之谈:我们随便地说狗喜欢肉,不喜欢色拉;金鱼需要清洁的水;花在阳光下开得最盛。由此我坚决认为,我们说的是描述性、科学性的话,而不是规范标准的话。
好多有哲学思想的同事们,他们对我们现实的状况与我们应该达到的状况加以严格区分。但我要说,我们能够成为什么与我们应该成为什么,前者这一用语比后者要好得多。请注意,假如我们采取经验和描述的态度,那么应该这个词就根本不合适。例如,如果我们问花或者动物应该成为什么,显然很不合适。应该一词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一只小猫应该成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以及答案中所包含的精神也同样适用于人类。
用一种更有力的方式来表达同一个意思:我们有可能在某一时刻区分一个人目前是什么和他有可能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人的性格分为不同的层次或者不同的深度。无意识与有意识的东西并存,尽管它们可能会发生矛盾。一个目前存在(在某一意义上),另一个目前也存在(在另一较深层的意义上)并且有一天将有可能上升到表面,成为有意识的东西,于是便在那个意义上存在。
如果这么考虑,大家也不妨认为,性格深处蕴藏着爱的人却可能有行为上的劣迹。假如他们努力实现了这种泛人类的潜能,就变成比过去健康的人,并且在这个特殊意义上,变得更正常了。
人与其他生物的重要区别在于:人的需要、偏好和本能有着微弱的、含糊的残余,有怀疑、犹豫、冲突的余地;它们极容易被扼杀在文化、学习以及他人的爱好之中,进而消失得无影无踪。许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惯于将本能看成单义的、明确的、牢固的和强大的(如同动物的本能一样),以至我们从未看到弱本能的可能性。
我们的确有一种类本能的倾向和能力的朦胧的骨架结构和性质。但是却很难从我们身上认清它,做到自然、自发、了解自己的本质、了解自己真正的需要,这是一个罕有的高境界,它虽然极少出现,但却伴随着巨大的财富,并且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长期的艰苦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