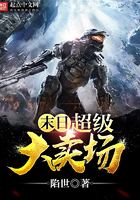宫里头寂静的很,苏沫尔挂下了纱帐。
香烟隔断,慢慢在房里头积聚起来。
“儿臣给皇额娘请安,皇额娘身体安康。”福临始才进宫,恐是孝庄怪罪,先就不及待作揖请安。“儿臣将乌云珠引了储秀宫歇息,未能适时过来请安,还望皇额娘见谅。”
一来二去地寒暄了数句,就落了正题上来。
“皇帝啊,平日里头哀家同你说,你也悉数不爱听,如今出了这样大的事儿,即便是哀家肯缄默,人鄂硕也不答应。你瞧瞧,好好的硬是把人给弄进宫里来了,搅得紫禁城天翻地覆的,为这事儿,太妃面上都险些挂不住了。哀家算是给你担下了,原是想你心里头有人家,哀家总是该足了你这份心。可你倒好,把人晾着,又瞧上别人了,哀家也给你担着,平日里头好使的,好吃的都差人给送了一份去,人家本是个香饽饽,得,进了宫反倒成了寒冰了,你心里头没她,哀家也就不逼你,想着你身为一国之君,这些年来,不想做的,不能做的事儿也都遂大家伙的愿做了,哀家知道你咽下了不少苦。若是成就了另一个娜木钟,哀家这心里头可不是添堵么?那丫头知书达理,哀家是那心眼儿里欢喜。她在宫里头受了这样那样的委屈,可是在鄂硕跟前可是没少说你的好话,明眼人这就看出来了,她欢喜你,可总是也沉在心里头。哀家瞧在眼里,也怪对不住人家的,可你这眼里,除了兰烨还有别人么!哀家方是寻思着让她多是同哀家一道,免得一个人在南院里头伤春悲秋,那孩子,别瞧着人前是乐的,什么苦都往心里头……”
“皇额娘……别说了。”福临攥着的茶盏,热了又凉。干裂的嘴唇渗出一点一点的血丝来,他沙哑的,打断了孝庄的话语。
“唉。”孝庄叹了口气,“要是往常,你还不得嫌哀家啰嗦,也只有这种时候,你才会好好听哀家说。也罢,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说来无益。皇帝,你该要给她一个名分。”
寂静了一阵,杯盏重重砸在了桌上。
“皇额娘。朕确有此意,只是,日子……”
苏沫尔上来给福临添茶,“太后娘娘未雨绸缪,早就差使人算好了,近年的八月初六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吉日……”
“苏沫尔。”孝庄有些欲盖弥彰的张了张嘴,喝斥一般的叫住了苏沫尔。
苏沫尔回望了一眼福临,讪讪退下了。
“皇额娘若是无非议,那就定了八月初六了,朕一会儿就谕礼部草拟诏书。”
承乾宫
日轮沉,清晓觉衣冷;此夜眼未合,梦寐方觉醒。
兰烨坐在外头的石凳子上斜斜倚着,呆望着灰蒙蒙的浓云。
原以为,这一天不该来的这样迅猛。这是天随人愿,还是天不遂人愿?
出了这档子事儿,倒是硬生生的把乌云珠给按进了福临尔今没着没落的心里头。
“主子,地上湿气重,小心着凉了,奴婢给您取了软垫子,放了再坐吧。”绿翘怀里揣着几张棉布垫子,疾步行来。
“到不至的那般精贵,我自己来就成。”兰烨起身抽过垫子,由着绿翘帮着拂去裙袂上的尘埃。“听说昨儿个皇上在乾清宫披了一整夜的折子,只粒未进,滴水未饮。今儿个天蒙蒙亮,就有人瞧着吴公公踉踉跄跄去了太医院……”
兰烨手中一滑,软垫子滴溜摔了地上,扬起了一片胡尘。
绿翘不动声色地捡起了垫子,放置好了扶着兰烨坐下,“奴婢冒昧问了,您猜怎么着?”绿翘瞅着兰烨煞白焦急的脸色,倒像是刻意放缓了声调,“是吴公公打翻了皇上的宁神茶,又怕皇上怪罪……”
“你……”兰烨的脸色腾地转红,故作举手要打的模样。
福临听罢,转身望向身旁早已战战兢兢离了远处的吴良甫,低低举了举拳头。
“皇上?皇上!皇上吉祥。绿翘眼尖,得了救星般的雀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