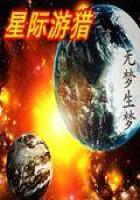1972年2月1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乘“空军一号”飞机,开始了他意义深远的北京之行。
就在这之前三天,2月15日凌晨2时20分,一生致力于中美友好事业的埃德加·斯诺,在瑞士日内瓦他的家中悄然逝去。
斯诺是不幸的,不少中外朋友为他惋惜,因为他本来是最有资格去北京采访中美关系解冻这一历史性场面的。随尼克松访华的记者团有87人,在这87人中,有谁能像斯诺那样,同毛泽东、同周恩来无话不谈?有谁能和斯诺相比,早在40年前就对中国赋予了深深的爱!
斯诺在旧中国生活了13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三次来访,累计逗留时间近一年。如果把他成年前的时间略去不计,在他的记者生涯中,他在中国居住了14年,在瑞士居住了13年,巡游世界各地4年,而在自己的祖国只工作生活了12年。斯诺一生中共写出重要著作11种,其中,有8种是关于中国的,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案头上放的是未及完成的《漫长的革命》。
斯诺是个爱国主义者,但在美国,他长期得不到政府的理解。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一切与新中国有联系的人都遭到迫害。斯诺的夫人找不到工作,斯诺自己也不能出版他的著作,只得迁居瑞士,因为瑞士是西方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1960年、1964年他两次重访中国,是那个年代里唯一能够往返中国、报道新中国情况的美国记者。他写出的报道和书籍,引起全世界的重视,唯一美国的报刊不予登载。斯诺对于当局的做法甚为苦恼,但他没有因此而终止促进中美和解的努力。1970年他最后一次访问中国,带回了两条重要信息,一是毛泽东欢迎美国的左、中、右派人士访华,二是毛泽东就中美间的问题要同尼克松会谈。
斯诺的努力终于收到了成效,他为中美关系的松动和解而高兴。他答应美国《生活》周刊,在尼克松访华时作为记者前往中国采访,人们也都期待着斯诺再写一本像《西行漫记》和《大河彼岸》那样的传世之作。可惜,斯诺在尼克松访华的前三天逝去了,因而他是不幸的。
然而,斯诺又是幸运的。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看到了一生所致力的中美友好事业有了希望,他的努力得到了普遍的承认。
美国国务院把他的《西行漫记》列为了解中国背景的20本最佳著作之一。在为尼克松准备的有关中国情况的简介材料中,就有斯诺著作和文章的摘要。基辛格后来回忆,他曾极其仔细地阅读了这些材料。有消息说,尼克松打算聘请斯诺做他这次中国之行的顾问。他致信斯诺:“……你杰出的一生博得了尊敬和赞赏。”
更使斯诺欣慰和激动的是,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刻,他的老朋友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
斯诺患的是胰腺癌。1971年12月15日,在瑞士洛桑的医院里,医生为他做了胰腺切除手术。手术时,医生发现他的肝脏有一个像网球那样大的转移癌,但无法切除。为了挽救斯诺的生命,他的家人和朋友们做了种种努力。人们劝说尼克松总统将斯诺接回他自己的国家,将他安排到华盛顿附近的贝特思达医院进行治疗。然而尼克松只回了一封简信,对所提出的要求表示遗憾。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斯诺夫人将他生病的情况告诉了中国。
中国方面迅速回信了。斯诺的好友,中国卫生部顾问马海德建议斯诺到北京去。周恩来委托驻瑞士大使陈志方去看望斯诺,并捎去了慰问信,在信中转达了毛泽东和邓颖超的问候。“这封深情厚谊的信对躺在病床上的埃德来说,好像那个阴暗的早晨顿时出了太阳一样。”斯诺夫人后来回忆道。斯诺口述回信,对毛泽东和周恩来邀他去中国治疗和休养的建议表示感谢。
1972年1月22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派遣由马海德医生带队的医护小组从北京动身前往瑞士接斯诺来北京。医护小组途中经过卡拉奇和罗马时,和当地的中国使馆安排好回程中为斯诺提供紧急住院的准备工作,以便必要时可以让斯诺在途中得到治疗。
在北京,日坛医院已经准备好一套病房和一个医护班子等待斯诺的到来。这套病房是陈毅元帅住过的,也是日坛医院能提供的最完备、最舒适的一套病房。
但是,当中国医护人员在瑞士看到斯诺时,他的腹部膨肿,在腹部的右上力,凸凹不平的肝脏隔着腹壁隐约可见,且已扩大到肋缘下达10厘米,质硬而且有压痛。斯诺疲乏地躺在床上,眼珠和皮肤发黄,神志恍惚,说话断断续续,声音低微,呼吸相当费劲……情况表明,他已经经不起远途颠簸了。
马海德俯下身向斯诺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问候。斯诺沉思良久,才慢慢地说:“我完全理解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美好心意,他们对于我当前的困境提出的具体援助的建议使我极为感动。我知道在中国土地上我会得到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能得到的关怀和爱护……我热爱中国……我不愿意作为一个病人到中国去……我不愿给中国增添累赘……”
遵照周恩来的意见,中国医护人员把斯诺在瑞士的家变成一所家庭医院,又增调了几位医护人员,开始对斯诺进行最后的医护。
斯诺的病情每两三天向国内报告一次,中国驻瑞士大使陈志方经常带来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问候,这些在精神上给了斯诺莫大的安慰。但是,他的病情仍在继续恶化。
2月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专程到日内瓦探望斯诺。他和马海德站在斯诺床前凝视着,脑海里翻腾着战争年代他们陪同斯诺在保安采访毛泽东和苏区的情景(黄华是斯诺在燕京大学教新闻学时的学生,当时叫王汝梅,后来他在斯诺苏区之行后不久,也到了延安。斯诺当时的夫人尼姆·韦尔斯访问延安时,黄华曾为她客串翻译)。斯诺醒来,意外地看到黄华,显得非常高兴,握着黄华和马海德的手,思绪又回到36年前的保安。他语重心长而又幽默地说:“咱们三个‘赤匪’又见面了。”他笑了。
这几乎是斯诺一生中最后的话语了。此后一周他一直昏迷不醒02月15日,他在睡眠中安静地死去。
当天晚上,毛泽东即刻发来了唁电,周恩来和邓颖超发来唁电,宋庆龄发来唁电……
毛泽东的唁电说出了斯诺的所有中国朋友痛失良友后的心里话:
“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2月19日,世界各地的朋友聚集瑞士日内瓦郊外的约翰·诺克斯会堂向斯诺致哀。与此同时,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有几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
3月27日,美国纽约也举行了一个追悼会,黄华第一个发言。
1973年5月16日,遵照斯诺遗言——“我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我有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生前一贯的那样。”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举行了斯诺骨灰安放仪式(他的另一部分骨灰葬在美国哈德逊河畔),毛泽东送了花圈,周恩来扶病亲自参加。廖承志在讲话中说:“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无论是在中国革命艰苦的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几十年如一日,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一生是中美两国人民诚挚友谊的一个见证。”
斯诺夫人也讲了话,她说:“这是一次真正的‘复始之旅’……他又回到了他曾从头就亲眼看到一场革命的这个国家,这一革命不但解放了中国人民,而且继续成为全世界世世代代的希望的灯塔。”
斯诺安息在太平洋两岸的土地上了。诚如廖承志所言:他的一生是中美人民诚挚友谊的见证。同时,他还是中国人民挣脱重重枷锁、赢得自由解放的见证人。不仅如此,他还直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同中国革命领导人毛泽东等的深厚友谊一直被世人所称道。
人们赞誉斯诺为“最了解中国和毛泽东的美国人”。他是当之无愧的。
自1936年夏斯诺进入陕北苏区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始,他们一生共有五次相见和分离。而每一次会面,恰好都在中国历史的紧要关头,其结果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国与世界。
1936年7月,中国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夜,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发动了侵占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东北沦亡、热河失守、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此时也正处于一个艰难时期。两万五千里长途跋涉的征尘未洗,又面临着蒋介石驱使下的各路大军的封锁“围剿”。如何站稳脚跟粉碎国民党的重重包围,如何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的抗战,是当时毛泽东千思百虑的问题。为此,他做了种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