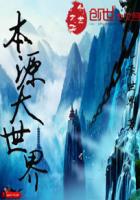大耿四十五岁,老爹早亡,与老娘徐氏相依为命。据说十几年前,大耿曾娶妻生子,后因某一事件离散,自此一心侍候老娘。徐氏年过七十,黑发红颜,除嘴里因嚼苞谷花儿硌掉一枚板牙外,从头到脚健壮如同少年。村人自诩善相面者,与人打赌说徐氏此生必过百岁,若在九十九上丧故,愿抵土房一间。
大耿生性耿倔,对村人时有触犯,人皆惧他蛮力,当面忍耐.,偶尔却在私下传出故事,不仅针对他,而且涉及其母。故事乍听离奇,细想却又合些情理,时间地点人物全有。说是四十多年前,徐氏被一红毛野人背去深山古洞住了半年,逃回家后生过一野人娃,因不食人间烟火,野性不改,一岁半上焦躁而死。
讲得栩栩如生,有八说当年亲眼见过那红毛野人,徐氏当时正在村前那条小河洗衣,男人指天发誓要打死野人。又有人争鸣说那野人娃不是自己急死,而是被徐氏男人活活打死的。众说纷纭。但有一则已被数人确证,徐氏男人是腰挂利刀,肩扛火枪,到一深山古洞去打野物,从此杳无音讯,不知是他打死了野物,还是野物打死了他。
男人走后,徐氏才生下大耿。
这个故事仅在背后讲讲而已,任凭大耿如何耿倔伤人,亦绝无人敢当面披露。十几年前唯有一次,村中有长舌妇与大耿媳妇闲说家私,无意间将这段故事透出,大耿女人自觉屈辱,某天同男人斗嘴,气极骂出此话,大耿一拳将她五颗门牙血糊糊打落在地。女人入夜悄然出走,一去永不再回。此后村人若再论及,越发谨慎。
然而毕竟传得家户众多,时日久长,终于传出村,甚或传出乌山。
某年春,有两人骑单车径奔林村。林村建于深沟,村前曲曲小径细如羊肠,只可行人不可行各类车辆,来人掏一条花链将车锁在大道旁一株古柳上,徒步进村,问明徐氏住处,便一头钻进那三间矮房。
大耿在家劈柴,老娘亦在,来人双双自称是县上派来的,有特殊事情调查,要大耿出去一下,只与其母单独谈谈。大耿心中狐疑,不认二位头衔,非但不出去,反而连柴亦不劈,搬把黑木凳子横坐屋中,听他们如何调查。二位相对苦笑,只得作罢,一个从兜里掏出钢笔小本,摇摇手腕,摆开速记的架势,一个专事问询。但开口一提起四十多年前红毛野人背其母入洞并生野人娃之事,大耿勃然立起,呼呼两拳把二位打将出去,关门上栓,任凭拍叫决不开门,只向窗外伸出一颗涨红脑袋,厉声大骂:
“红毛野人曰过你的老娘!”
满村男女藏在各自屋里,透过门缝窗孔,窃窥县上人狼狈形容,纷纷掩门而笑。
夏初复有人来。小鳖车开到春上县里二位锁单车的古柳边,依然向林村步行。这番一队五人,比上回整洁阔气,一色头戴小盘遮阳白帽,眼扣墨镜,腿着细裤。拢得村口先不进徐氏家,却先找村中白发长须老者,循循善诱,最后才问到四十多年前的事。每人并不掏钢笔小本,仅由一个小个子从随行大包中取出一瓦灰色长方铁盒,一按脑盖,只管从容聆听老者叙述,气氛庄严肃穆。这样问过几人,方才提起铁盒去了大耿家。村人捏一把汗,在身后遥遥观望,等待好戏。
徐氏母子又在。五人中有一头儿模样的,掏一黑皮小本让大耿看,说是省里下来的,了解山风民俗,笑哈哈扔一支白烟,还亲自为大耿点火,自搬黑凳坐下,并不开门见山,亦不要大耿出去,相对大说一阵生产,直到天色麻黑,方试探提及那事。大耿正等着问,勃然变色,从嘴里拔下那支燃了半截的白烟向头儿斜打过去,正中鼻脸。头儿愕然,见大耿气咻咻直奔铁盒,忙捂脸大叫抱走。五人鱼贯逃出,大耿这次不关门上栓,竟追出村去,昂首叉腰立于场中,厉声大骂:
“红毛野人日过你的老娘!”
村人掩门关窗,藏在屋中,耳听省里五人逃出村口,脚声仓皇杂沓。
深秋又来了人。停在古柳边的是一大盖车,一连跳下十好几个,男女兼半,脸上多数有眼镜闪烁照耀,男的长发披肩,女的短发裸耳,一胖大肚子带队,余者肩扛黑箱、白棒,浩浩荡荡,过步兵队伍也似的奔向林村,路径甚为熟谙,仿佛以前来过一般。在村口扎下阵脚,与前两番方式迥然相异,不直去徐氏家,亦不先访老者,却指挥卸下黑箱、白棒,瞄中村前那条小河,有女人按动某个物件,霎时生出若干个太阳,光辉耀眼,黑箱徐徐转动,光熄声止。胖大肚子挥手再行,停在徐氏那三间矮房前,又以黑箱、白棒对准,照耀扫射一阵。
村人发一声喊,尽皆出来观看稀奇,徐氏母子不明究竟,亦夹在人丛之中张望。胖大肚子态度极好,并不喝散围人,与每个老少男女逗趣,且叫那女人弄亮太阳,把黑箱向围人脸上转动扫射,自己则悄悄拉住一白须老者,请他暗中指点谁是四十多年前被红毛野人背进深山古洞的老母。老者颤巍巍以手指了,胖大肚子便叫黑箱重点对准徐氏。只听声响不见转移,村人觉得蹊跷,一时猜测议论,忽有人说一个“哦”字,对八耳语一句,顷刻引起半圈围人鼓掌哗笑,夸胖大肚子用的好计。
闹过一阵,胖大肚子掀衣揩汗,摇手说是休息一下,找口水喝,明日再干,便就近择了徐氏家,一干男女收拾黑箱、白棒相跟进去。胖大肚子与徐氏母子扯起家常,说他老太爷有亲戚在乌山,和这儿人算半个老乡,又说他在中央干事,这回专门下来拍照乌山独特风俗。大耿心想中央人到底比省里、县里人懂事,不逼人招供,正去取碗倒茶,不料大肚子趁他离开,话锋一转,竟然问起四十余年前事,那女人早又弄亮太阳,黑箱偷偷对准老娘,心中顿时全然明白,不禁怒从心起,飞奔过来,照着大肚子就是一脚,且顺手捞过竖在屋中的一根白棍,横扫乱打,来者纷纷抱头。女人叫男人快抱住他,男人则叫女人快跑,有身手敏捷的冒命拖了。胖大肚子,抢得几样残破家伙,冲出一条生路。大耿挥棍穷追,厉声大骂:
“红毛野人日过你们的老娘!”
村人眼见一行十好几人踉跄抢进大盖车,一溜烟儿开得没了踪影,便躲在屋中咧嘴咂舌,悄声议论这野蛮家伙,连中央人也敢骂敢打,恐怕也是那红毛野人的种。又说胖大肚子吃了大亏,不再佩服他用的好计了。
冬里没人再来。
翌年春亦没人再来。
但大耿每见村中来了生人,便厉声大骂:
“红毛野人目过你们的老娘!”
几乎每夜梦见来人,每梦必在梦中厉声大骂:
“红毛野人日过你们的老娘!”
越骂越觉每人言谈举止可疑,日夜不安。这年盛夏某个深夜,大耿背了两床被卷,挑了简陋家什,挽了老娘,悄然搬出三间矮房,在乌山一垭豁上落脚。垭豁距林村约两里,极荒僻,垭下原有几亩烧荒山地,种过几季苞谷,收获季节防人偷掰抑或野物偷吃,地的主人在垭上搭有一间尖顶草棚,每夜在棚中睡守。后见耕种得不偿失,便扔下山地和草棚,不再看垭豁一眼。
徐氏母子就住那草棚,就种那荒地。大耿白天不警惕来人,夜里亦不梦见来人了。
垭豁对面两箭之地,就是传说徐氏四十多年前被红毛野人背去住了半年怀下野人娃,男人挎枪持刀在此失踪的深山古洞。倘若山雾退尽,天气清明,站上垭顶,还可隐约望见洞口。
徐氏时常登峰去望。她两眼敏锐如同少年,望得见洞口,却望不见背她入洞的红毛野人以及寻杀野人的男人。野人和男人大约都死了,抑或健在,那就证明与她一样能活百岁。
然而入冬徐氏便死了,尚未达到七十二。林村里与人打赌者输了,输一间土房;但无人真要,徐氏母子三间弃房尚且闲着。村人尽皆叹息,那苦命女人命未活够。对于死因复又众说纷纭,有说大耿怨老娘常登山望古洞,有说大耿嫌草棚荒地孤远,有心住回林村,故对老娘饮食刻薄,言语粗劣,徐氏死时本是一碗姜汤即可灌活的。
大耿大哭一场,埋了老娘,果然搬回林村。村人察其变化,皆说日间不对生人厉声大骂“红毛野人日过你们的老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