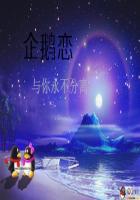倒是秦安石,从来没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万众瞩目?自己肯定也不会适应。修习武道?其实也并不怎么感兴趣。
而且他跟陈东厢其实还是很熟识的,平心而论也算是两小无猜。
打秦安石记事情起,印象中就已经开始有了陈东厢的影子,倒不是说什么情根深种,都是小孩子,那时候哪有那么多的心思,就只是单纯的印象。
因为小时候,两个年龄相仿的小孩子都住在各自家中的老宅子里面,而秦陈两家的老宅子凑巧离得并不远,自然而然的,对彼此来说这唯一的同龄人就并不算凑巧的经常碰见,一来二去也就玩耍在一起了。
至于发现了两个孩子关系的各家族,都是生活在京畿中,算是善意竞争,还没剑拔弩张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也就听之任之,反正到了年龄,总归是要分开的。
于是这种关系,很欢乐的一直持续到了两人六岁那年,直到陈东厢被家族中送去了北海灵犀宗修习,而秦安石恰好被一个叫做陈敬亭的中年道士收做徒弟,才算断开。
这一断就是三年。
直到今天,再次回到这京畿,秦安石才算是再一次的听见了儿时玩伴的消息。所以当被问到陈东厢那边声势浩大,自己这头却人稀物薄,难道不觉得难受不觉得嫉妒时,他很自然的认真开口道:
“不觉得有什么嫉妒,因为她武道修行真的很擅长呢……”
这话在他看来真的是天经地义很自然的事,他是真的见过她是多么的刻苦,也是打心眼里佩服。
谁见过一个女孩子就是为了练体,冰天雪地的时候就只穿一层单衣跑出去?更何况,当年她还只有五岁。
不过听进秦家派来接家中次子的几人耳中却是另一层意思,暗地里忍不住的叹息:这二公子看来是真的没什么大的出息了,不光是武道修行没什么进展,现在看来三年时间让他把斗志都给丢了。同样是七大家的直系子弟,就算是麒麟子再厉害,也不能不敢拼比,反倒去称赞对方吧?这也实在是太丢脸了。
难怪这家伙明明作为秦家的次子,地位不差,可离家三年,却没谁在意,也没听谁提起过,更不用说这次归家,就只派了他们三个不重要的杂役过来。
不过好在,这三个杂役还算本分老实,虽然难免会有些小心思,但还算收敛,碍于秦家的严厉家法,没什么不耐烦的情绪表露在脸上。
只是小小年纪的秦安石,不知怎么还是看出了这几人的态度,除了礼貌用词外,也不再开口说话了。
于是这一行四人,很是安静平稳的进了京畿,有意避开了陈东厢一行人的行进路线,七行八拐的回到了秦家老宅,秦安石从小到大居住的地方。
三个杂役把其实没什么东西的行李简单的放下,就对秦安石告辞了,看样子是一刻都不愿多呆在这里。
临走前,秦安石很郑重的对他们道谢,反倒让他们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不过也没多说什么。
这栋老宅子秦安石熟悉,承载了他从小的记忆,能够再次回到这里,他心中很是愉悦。
这种情绪让他面对这宅子因为长时间没有人居住,也没清理打扫,变得荒草丛生,灰尘四起的麻烦时,也没能影响了他高兴的心情。
秦安石四处的走了一圈,没发现有人在,知道这回家族应该是没打算给他配个下人之类的帮手,也就不再纠结,开始自己动手。
在西山上生活了三年,他没学得什么奇书异能,也没能解决一身废脉不能修行的问题,倒是养成了一切自己动手才能丰衣足食的好习惯,锻炼了他一身自我生存的实用技能。
而现在,正是这些技能大显身手的好机会。
秦安石简单搜罗了一圈,找到了一大堆的清理工具,脑子里简单的勾画了一下行动计划和大体方向,便付诸行动了。
于是,能看到一个有趣的景象,一个破败的老宅子里,从正午到傍晚,一直有一个个头不高身材瘦小的孩子,像是一头老黄牛一样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忙里忙外,从除枯草到清洁,从打水到摆放桌椅,一样样都是小孩子咬着牙,流着汗一点点完成的,让外人看到好阵的心酸。
然而,辛劳了一下午的效果是明显的,最起码已经能让人下脚,不会认为这是个没人居住的破房子。
但清理房屋这种事情,特别是像秦家这种大宅子,根本就不是一个人花费一个下午能够干的利索的,特别是他还只不过是个九岁的孩子。
秦安石一直是个诚恳的孩子,就像是他那对很直很正的眉毛,而且性格稳重,所以他的道士师傅给了他半山的号,就是形容他的沉稳,踏实。
可稳重踏实这样的词语对心态并不成熟的小孩子来说真的是不合时宜。
秦安石气喘吁吁地坐在厅内的凳子上,看着眼前的杰作心满意足。只是这种满足劲儿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当他视线偏转开去,看到的却依旧是一堆的杂乱。这让他其实不大有什么负面情绪的内心都有些难过跟纠结,心想:这宅子也实在太大了些……
京畿今年冬天并不是十分的寒冷,雪也没正经的下过几场,老宅的大院子里只是留下几点斑白,除了那冻人的寒气,真的没多少冬日的味道,让城中的孩子少了许多冬日的乐趣。
残血一般的夕阳早早的落下,只留下一抹的余晖,洒进秦家老宅的院子,浸泡在枯草跟残雪之间,映的院内血红。
忽的,像是秋风吹过,只剩枯枝的亭树摇晃着飘下了几片早就枯萎的叶子,叶子晃晃悠悠的跌落在地上,变得粉碎。
风声从屋内未关的门窗内呼啸而过,凄厉尖啸,吓得房顶的野猫一个失足摔了下来,溅起了星点的残雪。
野猫摔落的惨叫传的老远,惊到了树枝上的几只灰色麻雀,它们唧唧喳喳的叫嚷了几声,便扑闪着翅膀飞走了。
秦安石疲惫的坐在厅里歇息,身上青色的棉道袍被汗水打的湿淋淋的,青灰混杂,经冷风一吹,整个人猛地打了个哆嗦,好不狼狈。
头上的道髻因为一下午的劳作早就歪歪扭扭,散落下来。
很奇妙的,在这个时候,在秦家老宅里,此等惨景配上如此狼狈的人儿,竟然平白的生出种凄惨悲壮苍凉的感觉来。
只不过这此间此景没人注意到罢了,至于身在其中的秦安石,毕竟是个孩子,就算是再如何沉稳踏实,也没这阅历足够体会到这种感觉,有点对牛弹琴的味道。
随着天色暗淡,老宅本就不算繁华的四周变得更加安静,只有风吹过残破窗纸的哗啦沙响,门轴因为老旧出现的吱嘎,井水口残留少许水滴滴落井下。宅子外面偶尔响过一阵急促的车轴,从远到近又从近到远。
安宁而又平静。
疲惫的秦安石沉静在这种安宁中,忽然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生出。
他竟有一种迫切回到西山的冲动,回到那个不常说话但温和耐心地师傅身边,回到那个虽然常常发脾气但对他真的很好的小白菜师姐身边。
甚至觉得,就这样呆在他们身边一辈子,听他们骂自己笨,而不是这个秦家的次子该有多好。
这样就不用受别人的冷嘲热讽,嬉笑怒骂。
秦安石这个不过九岁的孩子,虽然踏实诚恳,可四岁就能看懂武泰安书的家伙,哪里会笨。从他记事起他就明白,自己永远不会是被宠爱的那个,不会向别人一样有任性撒娇的权利,也早就明白旁人看自己的眼神,那是嘲笑,是嫌弃。
所以,他一直悄声无息,一直不愿意说话,不愿意让别人注意到自己,也正是这样,他才会在四五岁的年纪跑到离家远一点的地方去玩,才会有机会碰到同龄的陈东厢。
好在,他六岁那年被接走,上了西山,有了三年在他看来算得上惬意舒心的好日子,那段日子他是打心眼里开心。
可如今,那种不用看人眼色,还有人关心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一想到这里秦安石心中就涌起一股巨大的难受。
特别是回来之后,自己那个当秦家家主的父亲连一句问候都没有送来,就像是自己这个儿子并不存在世上一样的不闻不问,更让这心中的难受难以忍受。
继而秦安石再想到了西山上虽然单调,但无人打扰,平静欢喜的日子,一种莫大的伤痛席卷而来。
继而,这股伤痛化作眼泪,如决堤之水,势不可挡的流淌。
寒冷跟悲伤同时席卷着秦安石,世界之大,却终归只能孤身存世的巨大孤独感如同一道巨大的黑幕,遮住了孩子眼前一切的光彩。
看着这个不过九岁的可怜孩子蜷缩在凳子上哭泣,任谁都会心疼爱怜。
心中定会猜测,这是受了多大的委屈,才让孩子被迫学会了思念?
不过,秦浇水可不这么想,也没那悲天悯人情怀,他只是右手拎着烧鸡的站在门口,目瞪口呆的看着厅内,看着蜷缩在凳子上的秦安石,心里像见了鬼一样大叫:
“这是谁家的熊孩子,没事儿跑这儿哭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