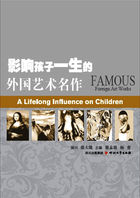·麻国钧
在古代亚洲,大约有这样一些演出艺术,即伎乐、舞乐、散乐以及后来的目连戏,贯通亚洲间各个民族,在历史上留下蛛丝马迹。当它们走进一个新的民族中间的时候,也同时把不同民族文化串联起来,以在不同程度上改变自己的方式,使之积淀并融合在另一个民族文化之中。
伎乐,这条千余年前从印度出发,沿着丝绸之路一路东游,犹如一条横穿亚洲大陆的艺术之舟,把亚洲大陆连接起来。在这条艺术之舟上,所承载的是古代亚洲各国所构成的文化圈中不同民族的文化与艺术。丝绸之路是古代亚洲文化圈形成的重要渠道。佛教的传播,佛教文化的一路东渐,则是伎乐传播的媒介。
伎乐,一作“妓乐”,原本出自佛教经典,意思是由菩萨演奏的供养佛的乐舞。在流传过程中,它的宗旨与内容,甚至连名称,可能都在变化中。
早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就留下关于伎乐的蛛丝马迹。中国古代文化曾不断地被其周边民族所受容,同时中国也在接受着、吸纳着别种文化的有益成分。佛教传来之后,佛教中的护法神也被很快地纳入到中国固有的傩仪中,成为驱鬼逐疫的主神。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十二月八日为腊,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出,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
公元6~7世纪,朝鲜半岛及日本先后从中国传入了“伎乐”艺术。这种所谓“伎乐”,是在当时的中国发生变异之后的样态。同时也可以看到,在南朝梁代前后的荆楚大地,古老的傩仪因受到佛教影响而改变了古风古貌,或者至少可以说,荆楚大傩仪不再仅仅是黄金四目的方相氏以及神兽之类,在这个队伍中,有戴胡人假头者,也有装扮成佛教护法神的。
当时伎乐的风貌已无从详知。但是依据现存之物以及文献记载,我们仍然可以窥知其大貌。味摩之传伎乐至日本之600余年后,日本的乐书《教训抄》对该时的伎乐有所记述。此外,日本至今仍然完好地保存着7~8世纪的伎乐假面。这些都为我们透视古老的行进演艺——伎乐,提供了难得的研究资料。
伎乐是典型的装扮出游的艺术形式。据《日本书纪》载,日本钦明十五年(554年)百济三个乐人把百济乐传到日本。推古天皇二十年(612年),百济人味摩之把他从中国的吴地学到的伎乐又传到日本。比起百济文化艺术,中国文化艺术是更加高级的文化,完整而成熟。当日本人见到吴的乐舞后,颇为惊异,立即迷恋于斯。
2001年10月下旬,我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中日韩戏剧节期间,在东京上野公园内“东京都美术馆”参观了“圣德太子展”。展品中有数幅《圣德太子绘传》,作为“重要文化财”,该绘传实属难得一见。其中两个版本的《圣德太子绘传》均为14世纪镰仓时代的作品,其一为茨城妙安寺藏本,一为东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本。在这两个版本的长卷中,都绘有圣德太子41岁时,味摩之传授伎乐给日本宫廷艺人的场面。同时展出的还有两副伎乐面具,第21号展品标为“太孤父”,第22号展品标为“力士”。“力士”、“太孤父”都是伎乐中所使用的面具。这两幅面具都是日本奈良时代的物品,也是“重要文化财”。其中“太孤父”保存尚完整,而“力士”面具则仅存其半。两副面具造型奇特,刀法极其苍劲流畅,让人顿生爱不释手之感。尤其是“力士”面,线条夸张,高鼻深眶,怒目圆睁,令人望而生畏。不想在同一个展览中,见到四件与伎乐相关的文物,真是可喜,有幸。
百济(前18~660年)原是朝鲜半岛汉江一带的小国,后来灭掉马韩,从而作为名副其实的王国登上历史舞台。在南下的高勾丽和西进的新罗夹击下,三迁其国都,渐次南移。其国所处的位置便于与中国的吴地交往,吴的文化很自然地被其国吸收。伎乐便是其中之一。
有趣的是,日本的这种伎乐多少有点像南朝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所记载的金刚力士以及戴着胡头的行进傩队。传入日本的伎乐多少应该保存有6~7世纪的吴地伎乐的风貌。南朝梁建都于建业(今南京),日本古籍说味摩之从吴地带去了伎乐,其所谓吴地当然应该包括梁代都城建业一带。这一点,还可证之以《隋书·音乐志》记载梁代普通中(520~526年)宫廷设乐,其中第44伎,曰:“设寺子,导安息孔雀、凤凰、文鹿、胡舞,登连《上云乐》歌舞伎”。由寺子(即狮子)导引的动物假形、胡人舞蹈以及接连《上云乐》歌舞伎的演出形式,就应该是全部或部分被味摩之带到日本去的伎乐。
《荆楚岁时记》所说的“戴胡头”是泛指,举凡西域形象的假头或假面都可以这样称呼,按理它应该是复数,绝不止一两个假面。
此外,伎乐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行道”,其二是继此之后的演技。行道是一支行进的队伍,其顺序为:狮子、踊物(舞踊)、笛吹(笛等吹奏乐)、帽冠(戴着帽冠者)、打物(打击乐)。详细一点,其队伍大致为:治道、狮子儿、狮子、吴公、金刚、迦楼罗、婆罗门、昆仑、吴女、吴女从、力士、太孤父、大孤儿、醉胡王、醉胡从等。队伍中的“治道”,是戴着高鼻子面具、手持长兵器的开路先锋角色。后来,这个角色被凶恶的“天狗”或“猿田彦”所取代,变成了日本的开路神。紧接着“治道”的是狮子。无论是“治道”,还是狮子,都具有咒术意义,是驱魔的角色。在这里,不是嗅到了伎乐的“傩”味儿吗?于是我们是否可以做这样的判断:伎乐是继承了《荆楚岁时记》所记载的“逐疫”一类队列表演,而又丰富了它,并进一步趋于世俗了。今天,在日本的神奈川县镰仓市坂下,每年9月18日,御灵神社照例举行祭礼。祭礼中的一项节目是面具行列,队列以两头狮子为前导,后面跟着九个戴着异国情调面具的人,他们排成一列绕村而行。在这里,古老伎乐的影子尚依稀可辨。
如果伎乐仅仅停留在“行道”一项上,似乎还不至于引起我们的格外关注,若是,也就消损了它的艺术价值。不,不是的。在“行道”之后,恰恰接续着演技部分。演技部分的构成,据《日本艺能史》一书的分析,有以下三类:
(1)狮子舞(狮子和狮子儿);
(2)戏剧性模拟(吴公、吴女、金刚、迦楼罗、昆仑、力士);
(3)模拟(婆罗门、太孤父——太孤儿、醉胡王——醉胡从)。
在伎乐的演出中,第一部分的狮子舞,同样具有清场的作用。狮子舞之后,一连串的模拟性艺能登场了。
首先是狮子舞,在它处于行进的状态时,目的在于清道。一旦停下来,则舞态百出。狮子或一头,或两头,每一头中,一般有两人共舞。另一个叫做“狮子儿”的,则由一位美少年担当,他持纲引狮而舞。综观中、日、韩三国历史上出现过的乃至迄今为止仍然流行在东亚这块大地上的狮子舞,可谓异常丰富。但是,它一直没有向戏剧转化,而停留在舞的阶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