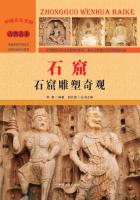·丁明拥
徐渭的成就主要在诗、文、书、画、戏、曲等领域,出入三家,精于音律,专于史志,旁及医术、对联、灯谜、制茶、酿酒、剑法之事,三教九流,均有涉猎。他天资超凡,似乎在任何领域,都可以取得骄人的成就,并对后人形成重大影响。徐渭的杂剧《四声猿》开明代杂剧之风气,创新了杂组剧一剧多折衍多个故事的新体式,影响所及明清两代几百年的戏剧史。《四声猿》自问世和被袁宏道重新发现以来,留下了一些难解之谜,如:作者为何将这四部颇不相干的剧作命名为“四声猿”等。前人学者在论述徐渭及其作品的时候也兼论及了这一问题,但囿于一两家之说,还不能够从社会环境、结集出版和场上演出进行全面阐释,更多的是仅凭一两个古人的笔记传说而揣测臆度,说服力明显不足。笔者查阅各类相关资料,专题就《四声猿》命名来历进行考察综述,提出“四声猿”命名新说。
一、“四声猿”命名的提出及有关学者的质疑
徐渭把自己所作的四部戏曲集取名为《四声猿》出版以后,很快就招致了一位倪姓者的攻击。徐渭的这位同乡倪某曾作诗讽刺他以“四声猿”为剧本命名不妥,大意是说他“妄喧妄叫”。徐渭立即赋诗反驳:“桃李成蹊不待言,鸟言人昧枉啾喧。要知猿叫肠堪断,除是侬身自做猿。”《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4月版)第三册第854页有“倪某别有三绝见遗,一以谓《渔阳三弄》杂剧内有黄祖,乃讽我即是黄祖特无权耳。一因我《红莲》剧内油葫芦有‘花葫芦一个圈’之句,而寓圈韵以讽。一因四剧名‘四声猿’,谓为妄喧妄叫。我亦次韵答三绝句,附书于此。”“其一:世事茫茫射覆然,都从黑地料青天,汝南月旦君如准,好握山中宰相权。其二:宿世拖逋且一圈,今生杀虎为牛缘。旁人不信无边被,不在吾家被里眠。其三:桃李成蹊不待言,鸟言人昧枉啾喧。要知猿叫肠堪断,除是侬身自做猿。”于此可见徐渭对自己作品寓意高深的自鸣得意。倪某的原诗虽不可见,但仅从“妄喧妄叫”这四个字来推测,倪某对徐渭还是非常了解的,对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和行文不按规则体例、胡乱用典的行为表示不满和讽刺。徐渭回赠的三首诗意思是:我作自有我深意,子非鱼安之鱼之乐?也基本上是为自己用典进行辩解,而未能说明“四声猿”的另有出处或更高明的见解,也许是有所隐私和个人感受无法对外人道,所以理不直气不壮,诗的意境上毕竟显出气沮来了。
之后有王定柱在《后四声猿序》中说:
徐青藤以不世之才,诧僚不偶,作《四声猿》杂剧,寓哀声也。《正平三挝》,沉痛不待言,其《红莲》、《木兰》及《女状元》皆以猿名,何哉?论者谓青藤佐胡梅林平徐海,功由海妾王翠翘;海平、翠翘失志死。又青藤以忿使梅林杀寺僧,后颇为厉。青藤继室张,美而才,以狂疾手杀之。既痞,痛悔,为作“罗鞋四钓”词。故《红莲》忏僧冤也;《木兰》吊翘也;《女状元》悼张也。此皆以猿名,固宜。
对于王定柱此说,后世学者多不认可。王说此四剧俱是徐渭沉痛、悼悔、寓哀声之所作,显然有穿凿附会的嫌疑。拿作者的经历说事是古往今来评论家的通用法则,岂不知历史事件或者现象更多的时候是受偶然因素所激发;作品也不例外,虽然有类似的生活阅历也会在相关作品内有所涉及,但绝不是一一对等的,有的痛悔心路历程,作者未必敢于触及,更不要说非要写出类似的作品了。
再之后,有清代的顾公燮首次提出了徐渭四剧是因为猿丧子,啼四声而肠断,文长有感而发的新观点。至于为何是“四声猿”而不是“三声猿”、“五声猿”,王骥德在他的《曲律》中是这样解说的:
先生居,与余仅隔一垣,作时每了一剧,辄呼过斋头,朗歌一过,津津自得。余拈所警绝以复,则举大白以酹,赏为知音。中《月明度柳翠》一剧系先生早年之笔;《木兰》、《祢衡》得之新创;而《女状元》则命余更觅一事,以足四声之数,余举杨用修所称《黄崇瑕春桃记》为对,先生遂以春桃名古段。《绍兴府志·文苑》徐渭传后,附载王骥德事迹:“王骥德字伯良,渭弟子,居隔一墙,渭填词,每辄呼伯良骑墙读之。”
以上就是“四声猿”命名考证最有代表性的几个观点。后世学者在考证“四声猿”来历及命名时也多来源于这几家学说,未见有新的观点。他们在论及《四声猿》时,主要还是注意到这四部戏与作者生活的时代、身世、经历有密切关系。在剧名问题上,仍然普遍认为“四声猿”的得名,是因为四剧所发皆悲声。但是,在认真分析了四部剧作之后,我们并不能发现这四部剧有断肠之悲。《狂鼓史》可引为千古快谈,《翠乡梦》更无一丝悲痛,《雌木兰》和《女状元》的剧情也只能给人以欢快愉悦之感,因此认为“《四声猿》这个题目不能涵盖四剧的思想内容”。那么,“四声猿”命名的真正含义在哪里呢?
二、对《四声猿》命名中“猿”字的考证
综合历代评论家对徐渭《四声猿》命名的质疑和考证,基本上是根据作者的生平经历进行的推测,旁证不足,很容易推翻。尽管如此,大家在质疑“四声猿”这一称谓上还是对“猿”字的来历达成了共识,即猿啼是悲伤。但是,这些研究者没有考虑到,猿啼的悲伤是为了丧子,徐渭又没有丧子,何来这样的悲伤呢?徐渭尽管可以在数字的“三”、“四”上显示与众不同,但是他不会胡乱用典。这样一来,徐渭答倪某的诗句也就大有不足以为外人道的蕴意了。其潜意识中确实是为了自己的儿子悲伤。
清代顾公燮对于王定柱的生活阅历与作品一一对应说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此说虽出王定柱,然无所依据,亦不可深信。且《渔阳》一剧未尝论及,其言亦未完全。不如勿深考之为愈也。与其凿空,不若阀疑。”顾公燮又说:“(文长)又作《祢衡骂曹操》、《月明度柳翠》诸剧,名《四声猿》。盖猿丧子,啼四声而肠断,文长有感而发,皆不得意于时之所为也。”
顾公燮在这段话里,首先否定了王定柱关于《四声猿》四剧和徐渭的生活经历一一对应说,然后首次提出了徐渭四剧是因为猿丧子,啼四声而肠断,文长有感而发的新观点。这个观点已经接近正确了,所以后世论者均袭此说。但是,顾公燮紧接着又总结说,“四声猿”的命名是因为徐渭不得意于时代环境的缘故,就又将问题引向了歧路。
也有学者根据顾公燮的说法,进而考证《水经注·江水注》中所引古民谣“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及杜甫《秋兴》诗“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而加以阐述发挥,于是顾说遂成定论。现代学者研究《四声猿》也都是从这个意义上进行分析阐发,认为《四声猿》中的四剧都是写作者无可奈何的哀伤,寄寓作者的悲痛,而没有进一步解释《四声猿》四剧内容与题目不合,剧作内容为何并不悲伤。
对于猿声哀子说的考证,据刘义庆《世说新语·黜免》记载:
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缘岸哀号,行百余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破其腹中,肠皆寸寸断。公闻之怒,命黜其人。后来,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说,三峡“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世说新语·黜免第二十八》。
这是猿声哀子说的最初出处。之后,无论是杜诗还是徐剧均袭此说。也正是因为如此,徐渭着眼于猿的哀子悲啼才给自己的四部戏剧作品取名为《四声猿》。后世徐渭的研究者也才认为《四声猿》蕴涵着极度悲伤的感情,认为作者以此命名是有切腹之痛的感同身受。徐渭绝非胡乱用典之人,理应深知猿啼跟哀子有关,并不是什么痛悔悼亡之作,那么徐渭感同身受的哀子悲痛来源于哪里呢?
根据《徐渭集·畸谱》和王俊考证的《徐渭年表》来推断,徐确实有这样切腹的哀子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