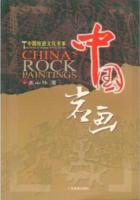·刘家思
布·马修斯指出,戏剧的效果的产生是故事本身,靠确立情境使之一个个似乎是自然而然产生,靠人物之间鲜明而尖锐的对比。事件是戏剧情境构成的重要因素。任何一部戏都离不开事件,一个人物的戏剧动作总是基于一定的事件而做出的,任何戏剧的冲突总是围绕一定的事件而展开的。一个优秀的戏剧家总是擅长并十分精心地选择具有戏剧意义的事件来构思创作,因为“一个选择得当的事件,不仅在戏剧结构中是组织冲突的纽带,而且是引起冲突爆发的导火索,是加速人物行动的推进器”,它容易造成一种尖锐的戏剧情势,为戏剧预设一种紧张而诱人的情境。当然,不同的作家总是有不同的事件选择与处理的方式。但是,总体说来,优秀的戏剧家都能以慧眼判断出事件在戏剧中价值的大小,并能独特地处理事件,最大限度地去彰显事件的戏剧意义,从而形成戏剧的剧场性张力。这也成为剧作家不同创作风格的一个基本点。曹禺是戏剧大师,写人是他戏剧创作的出发点,他总是选择那些最能造成和加强戏剧的逼人情势,对人物的生命存在和生命追求构成严重威胁,直接撞击人物的情感和心理的紧急事件来形成一种支配人物行动的强度,激起和强化矛盾冲突,从而产生强烈的剧场性张力。
一
一个事件是否有戏剧意义,其价值的大小如何,不是取决于事件本身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影响,而是取决于事件对剧中人物的心理影响与行为支配力的强弱。一个细小的事件,如果它能激起人物的情感波澜和心理反应,并影响他的行为走向,那么就有戏剧意义;如果它对人的心理与情感影响很大,导致人物做出一些对抗性或有意味的动作,那么它拥有的戏剧价值就很大。在戏剧中,事件本身对人物的影响度是检验它是否具有潜在的戏剧价值的唯一标准。一个事件,如果对人物的心理、情感不构成影响或影响不大,那么即使社会影响再大,社会意义再突出,都是没有戏剧意义的,起码是意义不大的。正如弗莱塔克所说:“戏剧艺术的任务并非表现事件本身,而是表现事件对人们心灵的影响。”曹禺戏剧的事件总是危及人物的生存与命运,以迫在眉睫的紧急情势影响和主导人物的心理,使人物进入一种悖论式的对抗与斗争的困境之中,始终处于尴尬与自如、无奈与主动、压抑与反抗、束缚与解放、沉静与追求、希望与绝望、抵抗与妥协、激烈与紧张的复杂的生存状态之中,不仅像一口“残酷的井”使剧中人物呼号却难以逃脱,也使受众的心态极其沉重,又无法舍弃,具有强劲的艺术导向性。因此,无论是《雷雨》中周萍要离开周公馆到煤矿上去,还是《原野》中仇虎来焦家复仇,或者是《北京人》中杜家要曾皓的棺材抵债,或者是《胆剑篇》中吴国入侵越国,都给剧中人物带来了巨大的危机。
在戏剧中,事件有多个事件与单个事件之分。有的戏剧由多个现实事件构成,有的戏剧只有一个现实事件。多项事件一般有主要事件和次要事件之分。主要事件统摄次要事件,次要事件服务于主要事件。《雷雨》的现实戏剧事件有三件:一是周萍要离开周公馆到煤矿上去;二是鲁侍萍要到周公馆来;三是鲁大海代表煤矿工人来到周公馆找董事长周朴园谈判。这三件事情都潜伏着一种危机,影响着剧中人物的现实生存状态。在这三件事情中,最主要的事件是周萍要到矿上去,它贯穿戏剧的始终。鲁侍萍到周公馆来是由它引出来的,而鲁大海的到来只是为了推动它而设计的。周萍要离开周公馆,危及剧中两个人物的生存状态。一个是蘩漪,一个是四凤。蘩漪18年前嫁给了周朴园,获得了丰厚的物质享受,却过得很不自在,很不愉快。周朴园的专横、冷酷、自私剥夺了她作为人的权利与自由,失去了人类幸福的情爱,随之又失去了人格尊严,失去了独立与自由。渐渐地,她似乎失去了正常人的思想和情感,丧失了正常人的需要与欲求,变成了石头一样的人。蘩漪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太太,年仅35岁,尽管她受到“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但是封建伦理道德束缚着她,使她不敢有非分之念,只能听任丈夫的摆布。而周朴园则是一个鬓发斑白、微微地伛偻着背的老人。从生理学的角度看,在过去的岁月里,蘩漪的情爱欲望是日益旺盛、越来越强烈的;而周朴园在这方面的要求却日趋衰退、越来越淡漠。
并且,周朴园是一个资本家,满脑子里装的是钱,为了钱财,他总是在外面不停地拼命奔跑。年纪越大,越是如此。因而,他只是将年轻的妻子禁闭在周公馆作为观赏物和看家的工具,无暇去满足她正常的需要。这使本来就无法和谐一致的爱情生活又添上了更多的不幸。于是,蘩漪的爱欲长期被压抑着,只是静静地等死。但是,在她心里,对正常人的生活的渴望是不会消失的。三年前,周萍从乡间来,那种奔涌的热情和燃烧的欲望,使她那种潜意识哗啦一下就上升到了意识领域,并且一下子就烧出了熊熊的烈火;她获得了久违的情爱,本来打算静静等死的她又产生了希冀,充满了幻想,便把整个的性命、名誉都交给了周萍。可是,周萍要离开周公馆,她将再次陷入生命的困境之中。黑格尔指出,“女子把全部的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或推广为爱情,她只有在爱情里才能找到生命的支持力;如果她在爱情方面遭到不幸,她就会像一道光焰被一阵狂风吹熄掉。”于是,她极力阻拦周萍的出走。这就引出了一系列矛盾冲突。她以为周萍的出走是因为四凤,于是,她要鲁贵将侍萍带到周公馆来,让她带走四凤。而侍萍的到来,不仅重逢周朴园,四凤与周萍的事情也东窗事发,加速了周萍的出走。正是她的强力阻止,使周萍的身世不断显露,使全剧走向悲剧的结局。
《北京人》贯穿在戏剧中的现实事件包括三件:一是逼债;二是愫方的婚嫁;三是曾文清的出走。在这里,前两者是贯穿性事件;后者是穿插性事件,是为主要事件服务的。曾家已经完全败落,债台高筑,中秋佳节,债主盈门。拿什么还债?能不能还债?是影响曾家上下老小的重大的生存危机。于是这就形成了一种紧急的情势。债主杜家是个暴发户,他们老太爷快不行了,看中了曾家老太爷曾皓苦心经营十几年、漆了几百遍的楠木棺材。在曾皓心里,这口棺材就是他的生命,是他的生命追求,也是他的生命的理想与归宿。他一心想保住这口棺材,用钱去还债;掌管着这个家的太奶奶曾思懿因为没有钱还债,一心想用这口棺材抵债。围绕着这口棺材的去留,曾皓和曾思懿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愫方是曾皓的姨侄女,由于父母早逝,遵母遗嘱,寄居在曾家。姨妈曾老太太在世时,愫方总是她的爱宠;曾老太太去世后,她又成了姨父曾皓的拐杖,时时侍奉在他身边,成为曾皓生存的依靠。她与表哥曾文清青梅竹马,互相爱恋。她十分了解整日在沉溺中讨生活的曾文清,哀怜他甚于哀怜她自己,她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愿意为他承受巨大的痛苦。她现在已经30岁了,却还是孤身一人。对于曾文清来说,愫方不仅是他心灵的慰藉,也是他生存的苦恼;对于曾思懿来说,愫方又是一个情敌,是她的心头大患。可以说,愫方的婚嫁问题,不仅是直接关系到她本人的幸福问题,而且关系到曾思懿、曾皓、曾文清的生存问题。在戏剧中,曹禺巧妙地将它与还债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恼人的戏剧情境,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如果说,《雷雨》、《北京人》是以多个现实事件来构成的代表,那么《原野》和《胆剑篇》则是单项事件构成的典范。《原野》的现实事件比较单纯,就是仇虎的复仇。仇虎坐了八年的牢,腿被打瘸了,生命受到极大的摧残,但有着很强的生命意志。他从监狱里逃出来,直奔焦家复仇。似乎那种不可知的神秘性在主宰着焦母的神经,她只是听说仇虎越狱,乘火车逃到了此地,还没有到焦家来,就感到大难临头。于是就派常五去找回刚刚出去不久的焦大星,并通知侦缉队来捉拿仇虎。她说:“虎子一天不死,我们焦家一天也没有安稳日子。”同时,仇虎的到来,与未婚妻金子相逢,使金子的生命拥有了活力。她说:“现在我才知道我是活着。”这就加剧了金子的反抗性格。可以说,仇虎的到来,直接影响着剧中人物的心理,支配着他们的行动。这样,它就为戏剧创设了重要的戏剧情境。《胆剑篇》中,吴国入侵,越国战败,国破家亡所形成的生存危机自然更不需多说。
可见,曹禺戏剧中的事件总是以其对剧中人物的生存带来危机而形成一种逼人的戏剧环境,以紧急的情势引导人们做出行动的选择。可以说,一个事件,只有危及人物的生命与生存,才能强化人物命运的关涉性,才能迫使人物做出对立与反抗的行动,才能彰显人物的性格,才能形成一种剧场性牵引力。因为观众在接受过程中,最关心的是人物的命运进程与遭际。如果一个事件与人物的命运不相关涉或者关联性不强,那么,这样的事件是不能产生动作的、缺乏戏剧意义的,当然也就缺乏情境经营的价值。
由于曹禺戏剧总是赋予现实事件一种强大的潜在危机,因此这种事件一出现就产生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艺术效果,立刻能作用于人物的心灵,形成强烈的情感冲击波和情绪控制力,使人物奋力行动,产生了巨大的剧场效应,充满艺术张力。无论是《雷雨》中周萍的出走,《日出》中方达生的劝走,还是《原野》中仇虎的复仇,《蜕变》中梁专员的巡查,《北京人》中的逼债和曾文清的出走,《桥》中何湘如的到来,等等,都放射性地对剧中人物注射了兴奋剂,形成了驱动力,催生了强烈的戏剧动作。同时,这些事件所导致的行动往往又天生地带有悖论式的品格。无论是周萍的出走和蘩漪的反出走,方达生的劝走和陈白露的不同意出走,还是仇虎的复仇与焦母的反复仇,等等,都具有各自可行的理由,能够被人们认可,于是曹禺的戏剧也就具有了强大的阐释空间,造就了广阔的“内基域”,能够满足不同的期待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