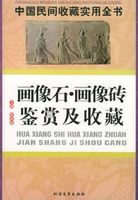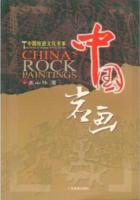——兼论梅兰芳访日公演成功的艺术因素
·袁英明
梅兰芳于民国时期两次访日公演(1919年、1924年),赢得了日本学界的高度评价。除了一致称赞梅兰芳的“美”之外,他们也普遍注意到中国的京剧与日本的“能”酷似——尤其在“象征主义”方面。如吉川操认为:中国传统戏剧与日本的“能”,“不是相似而是相同”;“中国戏剧和‘能’的源流也相同”。丸尾长显则认为:“说中国京剧和‘能’类似是有道理的,都是非常象征化的艺术。”戏剧通福地信世也认为:京剧的舞台构造不分幕,表现形式上是歌、舞、剧(指夸张的表演)的综合,和日本的“能”相似。
一、相同的戏剧源流
从历史上看,汉唐以来,中日两国文化交往频繁,因而在古典戏剧形态及其审美理念上相互接近,也就不难理解。公元7世纪末、8世纪初(相当于中国的唐代),散乐传入日本,与当地的民间演艺形式(艺能)渐渐融为一体,转化为“猿乐”。12~13世纪的室町时期(相当于中国的宋元时期),在中国宋代大曲和元代杂剧的影响下,猿乐走向成熟。14~15世纪的室町幕府时期(相当于中国的明代),能在猿乐、田乐和其他民间艺能的基础上,加上文学因素,渐渐定型,即能和狂言。其中的关键人物是14世纪平安时代的观阿弥、世阿弥父子,被认为是将“猿乐”、“田乐”、其他艺能以及文学融为一体的能的始作俑者,狂言也随之诞生。“能”被称为日本最早的古典戏剧,中国的散乐则是孕育能的温床。
最初,“能”的剧本只有三千字左右,舞台也极小,它的定型是在17世纪以后(相当于清代)。室町幕府时期已基本定型的“能”有贵族化倾向,主要追求古典诗词中闲素典雅的古风,带有人生的感伤情调,甚至空虚、哀怨的情绪。它遵循所谓“主角一人主义”,一出戏只有一个主角,即“仕手(シテ)”。主要配角叫“胁”。间或添加一两个次要人物,基本上没有多少戏。能的演员都是男的,扮演女角须戴假面,而且,只有主角(仕手)用假面,其他配角一般不用。
能的演出以歌舞为中心,演员动作非常细腻、洗练。评判演技的标准主要着眼于舞姿、身段、步态和歌唱技巧。在演出能的间隙,则穿插狂言,相当于欧洲的幕间短喜剧。
能的表演,动作、台词、舞台美术都限制在很小的范围,演员以简单的身段对应特定的行为,身段动作是程式化的。比如:在狭小的舞台上绕走一圈,表示已走了较长的旅程;面具朝下,用一只手蒙面,意味着哭泣;没有舞台装置,只有扇子等小道具;小巧的舞台时而是原野、时而是大海、时而是宫殿,通过激发观众最大的想象力来创造戏剧性的世界。这种程式化的表演与京剧如出一辙。
能摒弃写实,呈现的是极为抽象化的、极端程式化的舞台。其简洁的表演形式即使在现代也是在世界戏剧中程式化最为彻底的古典戏剧之一。在内容方面,其主题更多的是趋向死亡的热情与恋情。尤其是它所表现的禁欲主义,意味着以佛教为媒介的美的价值的转换,其中对主人公他界(死后)的兴趣,源于佛教彼岸(来世)思想的浸透。
力主邀请梅兰芳访日的日本文学家及庭院学家龙居松之助将梅兰芳的演出形式与能作了比较:
其一,舞台性质相同。两者舞台都向观众席突出,观众可以从三面观看。演员都是从舞台正面左右手的出入口(出将、入相)上下场。
其二,在舞台设置方面,京剧舞台只在舞台后位的正面挂一幅带有象征性的图案(例如梅兰芳剧团用梅花图案的“守旧”),有的甚至只挂一块单色天幕。这和日本能舞台上镜板的性质完全相同(京剧天幕的位置放置一块画有松、竹、梅的壁板)。也就是说,整出戏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舞台背景,不用写实布景。
其三,京剧的“听戏”时代,唱为首位,剧本方面不像西方戏剧那么严谨,有的甚至只有个大概,因演员而异。因此与其说它是西方概念上的戏剧,不如说是接近于歌剧,这方面也和日本的能乐近似。龙居松之助说:“京剧的剧本酷似日本的‘谣曲’,而且许多场面都是舞台上一个角色作吟诗般的独唱,其他演员无所事事地站着,无所配合,这一点和日本的能乐酷似。”
其四,京剧对丑行的巧妙运用和日本能乐中幕间滑稽剧(狂言)的作用类似,其串场和承上启下的作用也一致。
其五,京剧的砌末与能乐更相像,“可以说完全和能乐的舞台道具一样”。确实,京剧舞台不用幕这一点和能乐是一致的,中小道具的使用如城墙、桥、轿等砌末和日本的能也非常相似。在毫无装置的舞台上,演员从通往舞台的桥廊走入前台,进入剧情;结束时又通过桥廊迅速走入后台。这一点对习惯于西方戏剧的外国观众来说可能不习惯。但是正因为不用幕,所以演员随身携带小道具,以上下场的方式流水般地叙述剧情,这方面能与京剧出将、入相的上下场手法异曲同工。
由此可见,日本剧评家从表演形态的角度认为梅兰芳所带来的京剧“酷似”日本的能。二者作为古典戏剧和传统戏剧的共性,能够使日本观众在观赏京剧时产生文化的亲近感和认同感。
进一步探究其中的深层原因,不妨分析一下能所蕴涵的美学理念。
二、能的审美理念——“花”与“幽玄”
日本学界普遍认为,能的美学理念以及审美标准的确立者是这一戏剧形态的集大成者——世阿弥(实名为观世三郎元清,1363~1443)。此前,关于日本中世纪古典戏剧艺术的理论流传下来的极少。除了歌论以外,世阿弥的《风姿花传》是唯一涉及能的艺术的最古老的论著。全书由七编构成,第一至第三编著于1400年,第四和第五编于1402年、第六和第七编在1412年完成。《风姿花传》是“能”的传家秘传,最初并未公布于世,直至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才由吉田东伍博士发表了《世阿弥十六部集》。
世阿弥是14世纪室町幕府时期的能演员,他既体味过能演员在社会上的卑贱,又与武士贵族阶层有很深的接触。世阿弥父亲观阿弥是“能”的演员和剧作家。世阿弥童年就开始舞台生涯,20多岁已是著名的“能”演员。14世纪的当时,“能”演员的身份极其低下,观、世父子受到执政者、武士的最高权威——足利义满将军(1368~1394年在位)的宠爱,不单是由于世阿弥的“能”和出色的“连歌”才能,更主要的原因是其俊貌抓住了将军的心。义满和世阿弥之间的关系超越了资助者和艺术家的私密关系。义满死后,继位的义持将军(1394~1423年在位)开始疏远世阿弥。义教将军(1429~1441年)在位时,“能”遭到冷遇。世阿弥于1434年被赶出都城,流放佐渡,79岁获释回到京都,81岁死于京都。他认为,研究“好”与“美”的要害,首先在于如何抓住观众的心。为了生存,世阿弥苦苦思索如何用演技去讨得贵族的欢心,这关系到能演员的生机和命运。《风姿花传》是世阿弥继承其父、能的创始人观阿弥的遗训而撰写的。它不仅是能的艺术理论的总结,也是涉及所有日本古典戏剧的表演理论,是衡量日本传统艺术美的标准尺度和法则。
这部论著的关键在于“花”和“幽玄”的美学观念。从“花”和“幽玄”,既能看到能在舞台上体现美的具体方法,也能理解日本人对传统艺术的美的意识的深层探求。
“花”
在世阿弥的能乐理论中,从最早的《风姿花传》(1412年)到最后的《去来花》(1433年)之间,包括《花镜》(1424年)、《拾玉得花》(1428年)等等,书名中含“花”字的就有六种。这说明世阿弥对“花”的重视程度以及在探究“花”的方面所下的工夫。
《风姿花传》别名为《花传书》,其中最重要的词语也是“花”。日本古典戏剧中对“花”的概念有多种解释,界定含糊暧昧,没有明确的定义。细品《风姿花传》,笔者认为这部论著所谓的“花”,是指演员在舞台上的光彩、风姿、艺术魅力。
在《风姿花传》第三编的〈问答〉中,世阿弥指出:“花是心,种是艺”。此处所说的“心”,笔者认为是指演员永不懈怠、无止境地追求的恒心、决心、悟性。“种”,指花的种子,即技艺、诀窍。“花是心,种是艺”,旨在强调能的演员要从小训练,要积累多方面的技艺和素养,要有全身心地奉献给能的精神和恒心。即使功夫已达到顶点,也要懂得如何不失去魅力。有了“花”的心,掌握了种“花”的秘诀,就能成为“花”的“种”,而且保持“花”的光彩。世阿弥说:
所谓“花”,没有特别的意思,只要竭尽全力去掌握诸多的剧目,磨炼精湛的技艺,懂得如何给观众带来珍奇感,这就是“花”。提出“花是心,种是艺”就是指此而言。
在人们心中感到珍奇时,也就感到了新奇有趣。花、新奇、珍奇,三者是同样的感受。
这里的“新奇”,有新鲜、有趣、愉快的含义。感受珍奇、新奇的是观众,观众的身份、年龄、性别不同,对珍奇、新奇的感受自然也不同。《风姿花传》中的“花”,表面看来似乎并非指特定的演技,而是指观众“特定的反映”,其实,“特定的反映”是指使观众感受到的新奇和珍奇,世阿弥表示两者是一致的。因此笔者认为,实质上它明示演员如何掌握综合的本领,如何具有艺术造诣,使观众能感受到“花”的艺术魅力。如此看来,“花”的含义就明确了,它指的是艺术风姿、艺术光彩、艺术魅力,包含从演技到文化教养、人生阅历、舞台经验等各方面的艺术素养。
第七编还说:“不常驻的便是花,也就是‘能’”;“一味选择时间的就是花”。它意味着演员在舞台上的艺术魅力中,最光彩的点是瞬间的、稍纵即逝的,是择时的。也就是说,“花”不是持久的,不是演员主观上能控制的,只有经过长期刻苦的修行磨炼,功夫到家,万事俱备,各方面修养达到最高境界,才能自然地冒出火花、放出光彩。
这一观点寓意深刻,通过自然界“花”的比喻,对看似抽象、抓不住摸不着的“艺术魅力”一语道破。从演员层面讲,因年龄、角色、功夫、理解的不同,甚至健康状况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舞台效果,给观众以不同的感受。从观众层面讲,年龄、性别、职业、层次的差异,也会产生不同的感受。只有观演双方都处在最佳状态,“心气”契合,才能产生共鸣,才能出现或感受到“花”。因此,演员想要永远保持“花”的魅力,就要永无止境地执著追求,甚至奉献毕生精力。
世阿弥又说:“秘而不传即是花”。具体含义是:对于竞争对手的剧团及观众,倘若隐藏缔造艺术魅力(“花”)的手段和功夫,则效果更佳。这一名句至今在日本被用于商业性的广告语或杂志标题。其含义不在于“花”的美学价值,而在于“花”要有把握观众心理的本领。
世阿弥说:“能具备给人们意想不到的感动的策略才是花。”这从另一侧面强调了观众感受的珍奇、罕见,因为特有的秘密一旦泄露,感受就会被削弱,观众的期待也就无所谓“罕见、珍奇”了。一般认为,演技是“花”的关键。由此看来,“花”是演员在舞台上能引起观众感动的艺术魅力,除了后天的不懈努力外,也包含演员个人的天赋、素质。在日本有学者认为,世阿弥所谓的“花”,与其说是指演员所具备的艺术魅力,不如说是指观众的感受。笔者并不如此认为。
“幽玄”
另一个区别于“花”的概念是“幽玄”,这是从汉语中借用的词汇,同样是衡量“能”的美学标准和美学境界。
世阿弥对于“幽玄”也有多种说法,没有明确的定义。《风姿花传》第三编称:
看他演什么都不觉得弱,这是强势(功夫到家)的演员。还有的演员演什么都让人感觉优雅华丽,这便是幽玄。
从这句话分析,“幽玄”的意思为与“强势”相对照的“优雅、华丽”。如果说“功夫到家”只是匠气的“技”,那么“幽玄”便已上升到格调高雅的“艺”。正如中国京剧界常说的,一味耍弄匠气的“技”不过是“洒狗血”,更高的表演境界应该是“精、气、神、韵”。
在第六编“花修”中,世阿弥用一系列“华丽、柔和、优雅、娴静(恬静)、典雅”的具体例子来诠释“幽玄”:
角色中皇帝的妃子、后宫的女官,以及艺妓、美女、美男,草木中的花类,这些人和物的外形姿态是幽玄的。
如果扮演老尼姑、老太太、老僧,绝不可激烈地狂怒,也不可用幽玄的风格来表演粗暴粗野的人物。这样就完全不是真正的“能”。
本来很强硬、很强暴的人物,倘若演成幽玄的风格的人物,便不成为真实模仿,也不是真正的幽玄。
那么,所谓“幽玄”是一种含蓄的美,意味着与强、硬相对的柔和、优雅、华丽,是与粗暴、激烈相对的娴静、典雅。总之,“幽玄”是一种美的理念。
“幽玄”支配着日本中世纪的“美”的意识,也用于和歌中。但是,能的“幽玄”理念又与一般“幽玄美”的概念不完全相同。世阿弥用十多年的时间完成《风姿花传》(1400~1412),而他关于“幽玄”概念的界定也是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他认识到,由于时代的不同,观众对于“幽玄”的要求也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