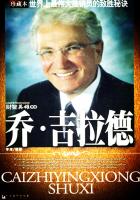蒋光慈回到上海,应瞿秋白之荐,来到上海大学任教。
上海大学坐落在上海西摩路南洋路口,前身是上海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1922年秋,因校方管理不善,引发学潮,师生一致请求于右任出任校长。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民国时期曾任临时国民政府交通次长,后任检察院院长。起初于右任不愿出山,在孙中山和其他国民党人的劝说下,才走马上任,并将校名改为上海大学。
孙中山对上海大学抱有极大的期望,想通过这所大学培养一批革命人才。他亲自批准,每月由大帅府财政部拨给万元,又捐赠宋教仁墓园中闲置土地六百亩建立校舍。上海大学特聘孙中山为名誉校董。于右任当校长时,共产党人邓中夏主持校务,瞿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
蒋光慈在上海大学任教授,教社会学系的课程。他以特有的豪迈的气度、精神焕发的仪表打动了师生们。上海大学的学生王秋心、王怀心、黄仁、杨之华、孟超和附中学生刘华、持志大学中学部学生戴侠等人,都和他往来频繁,关系密切。他向这些学生传赠自己的诗作、介绍俄国的十月革命、赠送进步报刊。有时兴致好时,还会请一些学生在小酒馆里小酌两杯,促膝谈心。在学生们的眼中,这位老师慈和温馨,能感染影响自己。
开始蒋光慈住在浙江路皖商公司,后来又迁居到法大马路明德里的一间房子里。房子中间拉一道帷布,里面摆写字台、椅子和床,床上一条像大别山区出产的那种竹席,一条俄国毯子;外面摆一个小台子和一只煤油炉,生活非常俭朴。他平时下一碗面条,就算一顿饭。
光慈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教书、编讲义、写诗、作文中。同时他还兼着苏联塔斯社报刊翻译科的科长,密切注意中国报刊的动态,及时将报刊上的一些重要文章翻译成俄文,提供给塔斯社。另外,他也关注着中国文坛的动态,并时常以创作者的身份参与文坛的一些活动。
可是,无论多么繁忙,每当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他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书英,想起那段婚姻。他无法以父母的高压、王书英的渴求来原谅自己,他为自己的软弱和意志薄弱而汗颜和自责。对书英的歉疚常常让他感到自卑和无地自容。
父亲所说的“纳一房‘小的’”也时常让他感到刺耳。小英子是牛吗?去留由人,处置由人。他能这样去做吗?不能!他最讨厌的就是当时的一些名流在婚姻上的惯常做法:在老家娶妻生子,在外面纳妾享受。让老家的妻子抚养儿女,孝敬老人,独守空房,苦度春秋,像深宫怨妇那样在祈盼中渐渐老去,慢慢凋零。这无异于是在精神上杀人!这样残酷的事,他做不到!可是他又不可能带她出来,在复杂的大上海,小英子既不可能会支持他的工作,也随时可能被他所连累。懵懂的小英子啊!然而就这样一直天各一方,对小英子来说其实与前者也没有什么两样。从他和小英子进洞房那天起,错误就已经铸成了,他蒋光慈就已经毁了王书英一辈子,他蒋光慈就是个罪人。想到这里,蒋光慈感到窒息。
为什么书英遇到的是我,会是我的童养媳,如果换成别人的,她或许能和其他童养媳一样,结婚生子,一家人团团圆圆,尽享天伦。是啊,从一开始,她就不该是我的童养媳,难道这就是她所说的“命”吗……如果是,我也要打破这个“命”。既然她不该是我的妻子,那么为什么就不能让她成为她所愿意的其他某个人的妻子呢?即使是现在,或许也都还不晚。蒋光慈心里闪过一道灵光,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好人家,我宁愿父亲将她当做蒋家的女儿嫁过去,也不要她守着老人孩子,守一辈子空房。
想到这里,光慈的心松了一松,毕竟这对于书英来说也是一条出路。那现在所要做的就是托个家乡的人,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父母和书英。
有了这个想法,光慈开始暗暗地为书英攒钱,他想为书英准备一份丰盛的嫁妆,赎罪也好,祝福也好,这是他现在唯一能为书英做的了。当然这一切还要书英首肯才行。按照书英的性情,或许她宁愿在家守一辈子空房,也不愿走出那个牢笼。光慈吃不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就要亏欠她一辈子了。
开学不久的一天上午,蒋光慈在几个学生的簇拥下,从教室缓步走出来。这时,一位身着黑布长褂、头戴礼帽的年轻人走上前,将蒋光慈仔细打量一番后,笑着问道:“你是蒋侠生先生吗?”
蒋光慈听到对方喊出自己少年时代曾用的名字,知道来人不是同窗,便是旧友,于是,遣去学生,笑道:“我正是从前的蒋侠生,现在的蒋光慈。你是?”
“汪昆源!”对方响亮地答道,“当年河南青年学会会员汪昆源!”
“啊呀!”蒋光慈紧紧地握住来客的手,“原来是昆源兄呀!早就听闻大名,今天才得幸会!”
汪昆源也很高兴:“俺是听曹靖华说你在上海大学任教。今天顺道来贵校,并没有费多少口舌,就打听到你了。这也是咱们有缘呀!”
“有缘有缘。”蒋光慈频频地点着头,把汪昆源领到了学校大门旁边的一家咖啡馆,要了两份咖啡和一些时尚吃食,两人面对面坐在几案旁,一口气谈了一个多小时。汪昆源谈起各地的运动,不经意提起了一个人:“……宋若瑜你知道吧?就是在‘五四’运动中就表现非常突出,被大家誉为‘中州女杰’的那个。”
蒋光慈立刻想了起来,细细想来,他和这位“女杰”还有一段渊源呢!于是赶紧追问:“噢,知道!那她现在呢?”
“你想,就这还能有好结果吗?她被开封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开除了。不过她倒没有退缩,也没有气馁,将同时被开除的其他七位同学组织起来,复习功课;第二年夏天,又考到了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系。但是由于家庭困难,今年春天休学回到开封了。后来经一位朋友介绍,到信阳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教书,教英语和美术等课。最近听说由于积劳成疾,又加辍学郁闷,患上了肺病。因此,精神上有些苦闷。”
蒋光慈听着,轻轻地倒抽一口凉气,不由为宋若瑜捏上一把汗。汪昆源曾经听闻蒋光慈和宋若瑜以前通过信,宋对蒋似乎很有好感,于是便尽其所知,将宋若瑜的情况,一一告诉蒋光慈。光慈听了拧紧了眉头。
宋若瑜,又名宋如玉,字文彩,1903年生于豫南汝南县的一个穷苦农家。父亲宋殿卿,母亲秦氏。宋若瑜十岁左右,举家迁居到姥姥家所在的七朝故都开封,在商业繁华的大坑沿定居下来。父亲宋殿卿性格刚强,开始给人家做仆役,后来因忍受不了世态炎凉的“闲气”,回家卖“锅葵”。因他技艺精湛,经营得法,很快成为大坑沿一带的“名吃”,生意红火,供不应求,加之秦氏给人家做佣也有收入,因此日子逐渐好转。秦氏先后生养九个儿女,唯独只存活宋若瑜一个。这么一颗掌上明珠,当然是“捧在掌上怕飞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开封素以文化名城闻名,清代的贡院、民国初年的留学欧美预备学校,都曾给这古老的汴京带来过一片文化生机。尽管宋家来自乡村,但他们还是将独生女儿送到前营门县立女子小学校读书。若瑜天资聪颖,学习成绩优异。初小毕业,没有经过高小阶段,就直接考入开封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这一年,宋若瑜虚岁十五岁,已长成一位身材颀长、相貌俊美的大姑娘了。长长的腿,一米六几的身个儿,腰肢纤细,脸蛋圆圆,两弯烟眉下,生着一双妩媚的大眼睛;举手投足间,既带有农家姑娘的质朴、豁达,又蕴含中原女性的大度、宽厚。由于学习成绩突出,待人热情大方,能歌善舞,长于辞令,她被誉为省立一女师的一朵出类拔萃的校花。
新的学校,新的生活,给她带来了新的活力。在《清明上河图》一般热闹的马道街上,在威严高大的相国寺,宋若瑜和同学们漫步探古,纵论国事,指斥时弊,展示自己的宏伟抱负和远大理想。有时不顾日落天黑,饥肠辘辘,兴致未尽而流连忘返。
学校有位教刺绣课的丁明德老师,是“鉴湖女侠”秋瑾的同乡兼同学。秋瑾牺牲后,她离乡北上来到开封任教。宋若瑜经常到丁老师那里求教谈心。丁老师向她讲述秋瑾组织光复军,配合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义举。从此,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行者、民主革命女英雄秋瑾的形象,时时在宋若瑜的头脑中闪现,并曾对自己的好友说:“俺长大了,一定要做鉴湖女侠那样的人物!”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迅速波及河南省省会开封。《新青年》《新潮》《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每周评论》《湘江评论》《少年中国》等报刊,在开封青年学生中间流播、传阅,使他们很快觉醒起来,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行列,传播新文化,宣传新思想。宋若瑜与曹靖华都率先参加。
五月九日,一女师召开女界国耻大会,参加会议的有一千多人。在会上讲演的女学生,个个义愤填膺声讨国贼,悲愤至极。三届三班的潘娴,在台上讲演时,当时咬破手指,血书“坚持到底”四个字以激励同学。宋若瑜讲演时,即兴朗诵秋瑾写的诗句:“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呼吁同胞们携手奋起,捍卫国土。大会之后,举行示威游行。宋若瑜带领一女师的同学,手持方旗,高呼“还我青岛”“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口号进行示威。她还带一女师的同学们,打破男女界限,与开封省立二中的学生领袖曹靖华、叶毓情、汪昆源等人共同出席请愿大会,去贡院,去省府,强烈要求省长和议员致电中央撤销卖国的《二十一条》。同时,宋若瑜还和外校的男同学一起抵制日货。当时,他们曾在宋门站岗,负责检查入城货物。先贴封条,再派人仔细检查,是日货就予以没收,是国货就发还原主。
她虽年纪不大,但沉着冷静却是有名的。一天,在马道街路东商场开大会。宋若瑜正在讲演时,省府派军警来捣乱,还向空中鸣枪,顿时会场大乱。一位女学生在楼上跌倒,腿骨被摔断。宋若瑜不慌不忙,一面呼喊大家不要乱,一面指挥大家高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齐奋斗,齐奋斗”的战歌,众人一心,稳定会场,以对抗暴力的捣乱和镇压。会后,同学们对宋若瑜的沉着冷静,对她的胆识和魄力,无不交口称赞。
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封的学生运动不断深入。进步学生成立组织,创办刊物。二中的曹靖华、汪昆源、关尉华、王沛然、叶毓情、张励等人,形成共同行动的核心。他们在1919年底,以“发展个性的本能,研究真实的学问,培养青年的真精神”为宗旨,成立了青年学会。宋若瑜跨校加入,成为该会的第一位女会员。
叶毓情同蒋光慈在固始县志成小学和固始中学都同过学,对蒋光慈的为人、学识和斗争精神都十分了解。经他的介绍和推荐,在安徽芜湖省立五中读书的蒋光慈,成了开封青年学会的外省籍会员。
“五四”时期,男女界限分明,想一时完全打破是不可能的。二中学生要与一女师同学联系困难重重。当时“男女有别”的社会舆论压力特别大,再加上反动当局派人监视,校方规定男学生一律不准进女师的大门。怎么办?宋若瑜主动提出,把联络地点设在自己的家里。这样,外地、外埠寄来的书信、报刊都先到她家了。一时间,大坑沿宋家成了开封进步学生组织的联络站和集散地,进步青年熙来攘往,笑语飞扬。
1920年,蒋光慈写了诗作《读〈李超传〉》。
李超为当时的北京大学女学生,广西梧州人,家中富有而父母早亡。一个过继的哥哥,全无良心,待她特别坏。李超对封建旧家庭不满,追求妇女自由平等,发奋出外读书。其兄采取恫吓手段,强迫婚姻,以至实行断绝经济供给的绝招,企图使她就范。李超曾忧愤地说:“……此乃先人遗产,兄弟既可随意支用,妹读书所求学乃理正言顺之事,反谓多余,揆之情理,岂得谓平耶?”此话不仅不为其兄理解,反而变本加厉对其施行迫害。李超贫病交加,积郁成疾,终于患肺病而死,时年二十三岁。时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先生,愤而写了《李超传》,为这个可怜的短命女学生鸣不平:“李超有钱而不得用”,“以至受种种困苦艰难,以至于病,以至于死……这是谁的罪过……这是什么制度的罪过?”胡适向“封建宗法社会制度”,向“家长族长的专制”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时在安徽芜湖省立五中读书的蒋光慈,读了《李超传》后,悲愤难禁,热血贲张,一口气写成了抒情新诗《读〈李超传〉》:
读了你的历史,知道了你的身世。
我起了一种感想——呜咽还是涕泪?
呜咽!
涕泪!
是你的际遇;
是我的心事。
你不是你父母所生吗,
为什么家财不能承继?
你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吗,
为什么做事不能自主——被人家儿牵制?
哎!
你一生的命运——乖舛!
你满腔的热血——空具!
怨天呵!
天不语。
恨地呵!
地无灵。
这倒是谁的罪恶?
你看这昏昏的呵!何处不是地狱?
你看这丛丛的呵!何处不是荆棘?
哪里有清洁的空气——可以呼吸?
哪里有明亮的境界——可以做个立足地?
身上徘徊;
天涯无着;
也不怪你郁郁的而死!
女士已矣!
空间无止境;
时间不停息;
继斯人之后者——也不知道还有凡几?
现在的青年女同胞呀!
但愿你们振作精神,加倍气力,
来与这黑暗奋斗——
为生者增光;
为死者吐气。
蒋光慈将诗由芜湖寄到了河南开封青年学会指定的联系地址。没有几天,此诗便到了宋若瑜的手中。
宋若瑜坐在闺房的书桌前,仔细地读着蒋光慈从芜湖寄来的诗稿。她被作者对弱女子李超的那颗无限同情的心打动了,也被作者对女性的召唤所震惊。诗中强烈的排比,铿锵有力的反诘,深深感染了她!她在心里默想,我们青年学会的宗旨是“发展个性的本能,研究真实的学问,养成青年的真精神”,这把个人的解放放在社会解放之前,是不是有点虚无飘渺了?对照李超大姐的惨死,对照蒋侠生的诗,我不得不对咱们青年学会的宗旨提出这样的疑问。
宋若瑜赶快把邮差送来的报刊、书信收拾一下,飞快地奔向大纸坊街的省立第二中学,找到了青年学会会长曹靖华,把蒋光慈的这首诗向他推荐:“靖华!安徽的蒋侠生寄诗来了,写得好!”
曹靖华接过诗稿,慢声慢语地说:“等我回到宿舍再看吧!”
“看你这人,真是慢性子,”宋若瑜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俺特地送来的,你现在就在教室里看!”
曹靖华将这位新朋友的诗作,足足看了三遍,这才猛地一拍大腿,仰头大声地说:“李超的死,是社会黑暗造成的,是封建礼教迫害的。只有像蒋侠生讲的——来与这黑暗抗争,来与这黑暗搏斗,咱们才有出路。若瑜,他讲得对极了!”
“嗯,俺看这首诗可以在咱们的《青年》上发表。”宋若瑜举荐道。
“你就编发好了,俺赞成,”曹靖华点点头,“这首诗放在咱们刊物的首位。它有号召力,能鼓舞人!”
宋若瑜告辞了曹靖华,高兴地又取道去找青年学会会员叶毓情。她又把《读〈李超传〉》那首诗送给叶毓情看,再次征求她的看法。叶读罢连连夸好。宋若瑜也夸赞叶毓情做了一件好事,为青年学会介绍了这么一位诗人会员,增强了学会的战斗力。叶毓情看到开封一女师的校花如此欣赏、夸赞自己的老同学蒋侠生,灵机一动,高兴地说:
“蒋侠生的故事多着呢,若瑜,下午课余时俺到你家给你讲一些,好吗?”
“好呀!欢迎欢迎!”宋若瑜点着头,脸霎时红了。
下午,叶毓情来到大坑沿宋家。宋若瑜热情地将她引进自己的卧房。房间不大,陈设简朴,收拾利索,并没有多少脂粉气。最显眼的是,书桌上方悬挂着一幅龙飞凤舞的书法,写的是鉴湖女侠秋瑾的诗《梅》。她们就是在鉴湖女侠的《梅》下,开始了有关蒋光慈的闲叙。叶毓情说:“蒋侠生身个儿高高的,脸面儿白白的,两只眼睛又明又亮,真是一个风度翩翩、潇洒英俊的学生。他待人热情诚恳,时时给人一种向上的力量。”
宋若瑜静静地坐在那里听着,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眨着。
“咱俩在固始县志成小学是同学,又在固始中学同学一个学期,”叶毓情继续说,“记得咱们的国文老师曾这样讲他:‘蒋北峰这个学生,谈笑起坐舒缓有致。听其思辨,吐言深刻,玩耍嬉闹时,却又宛如天真的顽童,大有哲师风范。稻看秧,树看苗,人是从小看大。我看他人才难得,说不定真能成为一座山峰呢。’”叶毓情学着那位老师浑厚的腔调,摇头晃脑地说着,逗得宋若瑜不由得格格笑起来。
“他后来怎么又到芜湖读书了呢?”
“他为人正直,爱憎分明,在固始中学第一学期结束时,就气愤学校校长平时对穷家子弟横眉竖眼,对富人的子弟点头哈腰。后来气不顺地憋在心头,实在按捺不住,就聚集几个同学跑到办公室,质问那个校长:‘请问校长,穷人的子弟是不是人?为什么你对富人的孩子笑嘻嘻,对穷家的子弟恨不得一口吞?’校长被问得噎在那里,气得脸发青,怒喝蒋侠生‘滚出去’,还推了蒋侠生一把。蒋侠生见校长动手,吼了一句‘打你个狗眼看人的校长’,带着一帮学生把校长痛打一顿。结果放寒假时,他被学校开除了。蒋侠生在白塔畈老家闲住了半年多,就又到芜湖读书了。”
宋若瑜听到这里,轻轻地嘘了一口气。
“蒋侠生这首新诗写得是好,”叶毓情说,“他父亲是位塾师,自小就教他诗词格律,吟诗作对……”
叶毓情一个多小时的介绍,不仅使宋若瑜对蒋光慈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还使她不明不白地产生一种冲动,想进一步了解他,还想见见他。十七岁姑娘的这种渴望,当然只能埋在心底,对谁也不能说出口。
1920年春,到上海出席全国第一届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的曹靖华回到了开封。他带来了蒋光慈的一篇新写的议论文《我对于自杀的意见》。曹靖华对青年学会的会员们说:“蒋侠生作为安徽芜湖学联的代表,也出席了上海的大会。咱们这位安徽籍的会员,为我们争了光夺了彩。他在大会上的发言,字字有声,催人奋进,赢得了代表们不断的掌声。会后,请大家看看他这篇新写的文章,语言犀利,观点如炽,你们一定会翘起大拇指……”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宋若瑜心中早已潜藏的火种,就像遇着了清风,立刻燃起煌煌的火苗,荡起了情思的波涛。回家再次翻读蒋光慈的《读〈李超传〉》,发现在诗的“小引”中,竟然还有这么一段文字:“明智的女性是不会放过一个才华横溢的男人的。异性之间的这种吸引力,这种天然的默契,往往可以超越任何空间地域的障碍,甚至于弄得绝大多数同类和异类都摇头表示:想象不到,不可理解。”
姑娘读着这段话,似乎是蒋侠生专为她而写,似乎他们冥冥之中有着某种“天然的默契”,好像他们在人生旅途上应该会发生携手扶持、相濡以沫的事。这些想法在她那渴慕社交、渴慕友谊的性格中一经发酵,心头一下子被不安和躁动占领了。这是1920年4月,正是春光明媚、万物复苏的季节。那天晚上,宋若瑜失眠了。在床上辗转反侧到雄鸡高唱,半睡半醒地迷糊了一会,猛地翻身下床,迎着窗前早晨的霞光,毫不犹豫地铺笺挥毫,给蒋光慈写了这么一封信:
侠生社友:
请原谅一个陌生女子的冒昧,给你写信。读你的诗文,深感有一种奔突的力量;素来禹勤(即毓情)、靖华友言及你的为人,均夸奖你的爱国热情,表扬你的学识,令我敬仰。如蒙不弃,愿与你结为良友,来与这黑暗社会奋斗。
青年学会会员宋若瑜
信文虽短,但字字珠玑。宋若瑜有生以来第一次给异性写信,信很快落到了十九岁的蒋光慈的手中。傍晚,他来到长江边上漫步。四月的江流,浪花飞溅。他在这里与大自然对话,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他踽踽独行着,俯首低眉之间总感觉有一双无所不在的眼睛,发亮地凝视着他。那是一双饱含期盼、羡慕与喜悦的少女的眼睛,一双足以使自己魂牵梦绕的眼睛。啊,美的存在就是这样难以寻觅又易于发现的吗?他想起来了:叶毓情上次来信描述的学生集会演讲、开封军警鸣枪捣乱会场时,那位临危不惧、沉着冷静、指挥若定的青年学会女会员,准是她;曹靖华在上海向我称赞的一女师校花的新女性,肯定就是她。信中最后一句“来与这黑暗社会奋斗”,不就出自我的《读〈李超传〉》中的诗句吗?江涛澎湃,夜幕降临。蒋光慈不觉有一种偶遇知音的兴奋。
“宋若瑜!”蒋光慈在心中默念着这个美丽的名字。晚上他给宋若瑜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表示愿意彼此结为良友,终生毋相忘。
接着,蒋光慈的心已无暇旁顾了。因为他的人生道路,有了重大的转折。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另一番全新的生活——先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继而赴苏俄留学。
在苏俄留学两年多的时候,蒋光慈曾给宋若瑜写过信。在信中,他向她打听家乡的形势,向她传播苏维埃的盛况。还向她宣传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思想,希望她找拜伦早期的代表作——长篇叙事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阅读。蒋光慈说,自己与拜伦一样,“同为被压迫者的朋友”;还以拜伦自诩,设想与拜伦对话:“19世纪的你,20世纪的我。”
接到蒋光慈的信后,宋若瑜在开封四处寻找拜伦的诗集,还告诉她的好友:“在俄国的那位朋友,要做中国的拜伦了,真是有才气、有志气!”拜伦的诗,震撼了宋若瑜的心扉;中国的拜伦,惹得中州女杰魂牵北国,春心浮动。
事实上,宋若瑜这几年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被开封省立一女师开除;考取东南大学读书;休学到信阳省立二女师任教。
开除的事,源于1919年11月16日,福建福州学生为提倡国货和抵制日货,与日本驻福州居留民团发生冲突。结果,爱国学生被击伤七人,被打死一人,同时打伤很多市民,造成震惊全国的“福州惨案”。福州学联因此于当日向全国各界联合会发出急电。开封学生闻讯后,极为愤慨。宋若瑜立即组织一女师学生上街游行示威,高呼“头可断,血可流,福州不可丢”、“力救福建”、“抵制日货”等口号。直到1920年初,斗争时起时伏,学潮仍在继续。各学校都要求学生复课,但学生不听,仍坚持罢课。开封一女师校长,请求省教育厅厅长李步青批准,张贴布告,开除所谓“出风头,闹学潮”的宋若瑜等八位学生。顿时,一女师上下一片哗然:许多学生哭喊着“宋若瑜”这个名字,找到宋若瑜的宿舍声援她;有的同学干脆扯下布告牌上的布告,将布告牌砸成了几块;还有的在教室外面高呼:“李步青——理不清!”“宋若瑜无罪!”
而坐在宿舍里的宋若瑜却纹丝不动,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有的只是满腔的怒火。事隔五年之后,她在给蒋光慈的信中谈及此事时说:“你是一个革命者,我也是一个反抗者。我反抗宇宙间一切不平等、不自由的待遇!我诅咒所有的资本家及帝国主义者。这种反抗或者就是我的生活,我自幼就爱反抗,因为反抗,所以在开封一女师被开除了——但是我很愿为这种有价值的反抗被开除。”
作为全国性的“五四”爱国运动,到了1920年已接近尾声。开封的运动也因一些进步学生被开除,加之寒假已到,学生各自回家,学运力量分散而受到了影响。宋若瑜的学籍虽然被开除,但她追求进步、渴望求知、探索救国救民方略的热情并没有被遏制。她一面冷眼面向街坊邻里的讥讽,掩泪向父母陈述爱国无罪的道理,一面积极托人帮忙,转入了开办不久、倾向进步的北仓女中复习补课。
1922年夏,宋若瑜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梦寐以求的南京名牌大学——东南大学教育系就读。当她置身于南京这六朝古都,见到了云集在东南大学的陶行知、竺可桢、茅以升等一代中华英才时,真是欣喜至极。她暗下决心:“杜门谢客,埋首读书”;“努力研究教育,以造成一个平民教育者”。谁知正当她废寝忘食、奋发向上的时候,宋家因经济困难而断其供给。宋若瑜无奈,只得忍痛含泪于1924年春休学回开封了。
当年被一女师开除,动摇不了宋若瑜积极向上、追求进步的人生信念;今日的经济困难从大学休学,更不会使宋若瑜气馁消沉,一蹶不振。经友人介绍,她受聘于河南信阳省立二女师任教。
宋若瑜,这位立志献身平民教育的东南大学教育系的优等生,以她的渊博和俊秀潇洒,博得了省立二女师师生们的喜爱。不管是授英语、代美术、教体育,还是当斋务管理生活,总是与学生们像同学一样亲密无间。只要一有机会,她就向老师和同学们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她喜欢诗词,爱读名著,更希望在自己周围出现文学新秀。信阳籍的当代著名剧作家赵清阁,就是在她的指点之下,踏上文学之路的。赵老曾多次回忆自己的成长之路,每次回忆都深情地怀念她的恩师宋若瑜,说自己在省立二女师附小读书的时候,“音乐、体育老师姓宋,是著名作家蒋光慈的夫人,她发现我爱好文学,常常叫我到她屋里去,为我讲些新文学知识,介绍我阅读‘五四’以来的新书和杂志,如冰心的《寄小读者》《小朋友》月刊等”,她“是我新文学方面的启蒙老师”,她为我“这棵幼苗”“奠定了矢志文艺的兴趣和志愿”。
宋若瑜,这位酷爱大自然的姑娘,笃信卢梭返于自然的学说,如今置身于林壑优美、民风淳朴的古城信阳,感到十分快慰。
不过,夜深人静,沉下心来,失意的一面又占据了宋若瑜的心头。二十一岁的宋若瑜,这时候是多么需要温暖言辞来慰藉,多么需要爱情之露来滋润啊!
深秋,金色的阳光给喧嚣的上海洒下一片柔情。仿佛这污垢的闹市,也配接受那美神的微笑。
蒋光慈从汪昆源口中得知宋若瑜的情况和下落。这位还未曾谋面的姑娘,经过汪昆源的详细介绍,让蒋光慈一下子感到她不就是《夜未央》中那位勇于追求、大胆施爱的苏维娅吗!“此生不遇苏维娅,死到黄泉也独身!”一番回忆与回味,她一下子和他百般向往、千般追寻的苏维娅融为一体了,在他心中占据了几乎是压倒一切的位置。
蒋光慈兴奋极了。他要把已被截断的爱的红线赶快连接起来。可是一阵忐忑不安的心理在作祟,简直犹如罪恶缠身,他又想到自己虽然向往于自由恋爱,虽然追求进步思想,可是在老家仍旧有一个封建礼教的樊笼,书英还在那里无辜地企盼,望眼欲穿。光慈呵,你仍然是系在封建婚姻牢房里的一个囚徒。你想自由么?那书英怎么办,在书英还没有另觅到归宿的时候,你怎么敢妄谈自己的向往!
蒋光慈陷入了烦闷之中,掉入了痛苦的深渊。几经思想反复之后,他还是给宋若瑜写起了信。
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诗说得好:“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鱼雁传书,日益频繁。心理上的吸引对地理上距离的克服,心灵上的相通对面容上陌生的超越,表现为情书的屡屡往返。蒋光慈理解了情书是爱的使者,情书是两性愉悦和谐的福音。他醉了,爱情笔谈成了他与宋若瑜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走在高楼林立的大街上,蒋光慈会看见每一扇窗口那里都有宋若瑜的眼睛;走在市郊的绿野里,蒋光慈会觉得每一朵野花都闪烁宋若瑜的面容。蓝天上的每一朵白云,森林里的每一片绿叶,夜空里的每一颗星星,阳光里的每一缕清风,都能为蒋光慈带来爱的信息,爱的幻影。
蒋光慈和宋若瑜的相爱,是有深厚的根基的。其一,他俩都憎恨人间的不平,敢于反抗黑暗的势力,向往光明的未来。这诚如宋若瑜在信中所说:“侠生!你以为我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贵族式的女子吗?哈哈!你猜错了!你是一个革命者,我也是一个反抗者。”其二,他俩有共同的志向和爱好。这就是炼铸能力,投身革命,服务社会,而文学又是他们共同的爱好。宋若瑜不仅能歌善舞,而且有较高的文学天赋,她会写诗,会翻译,有敏锐的感知、悟性和表达能力。这一点,很受蒋光慈的赏识和称赞,多次说宋若瑜“你是我司文艺的女神,你是我的灵魂”、“只因我是诗人,你是司文艺的神女”,甚至说“我想我俩将来走一条路,我希望你也勉成一个女诗人。”
蒋光慈把宋若瑜当做了可亲可敬的女英雄苏维娅,当做了同心同德的司文艺的女神。她在他的心中几乎占据了压倒一切的位置。蒋光慈在信中以满含诗情的笔调,以冷静的、愉悦的、焦灼的,有时又是不可抑止的激情,谈人生,谈爱情,谈意趣,谈志向,谈对未来前程的设计。
……
屋内的伴友:一盆金黄色的菊花,一架子的西文书。闷起来的时候,就看看花,对它发一阵痴想;痴想发过了之后,觉得更是无聊,于是掀开几页蟹形文字的书来看。钟点到了,就夹起书包上学校里去讲课。课讲完了之后,或者回到屋内闷闷地稍微坐一下,拿起笔来写,或编讲义,或翻译文章。有时候下了课,独自一人跑向花园里逛一逛。
啊!这就是我近来的生活!有趣味呢?还是没有趣味?我想起,或者是幻想罢,你时常同阎女士及其他一些可爱的女郎游玩,散步,欣赏自然界的美丽,是何等的幸福!是何等的生动!但是我呢?……
这是一封较长的信。据信文推断,这不是蒋光慈回国后给宋若瑜的第一封信。因为信中有这样的段落:
……这或是我无聊的默想,但是人越无聊,越盼望朋友的来信,而况是亲爱的朋友的信?因盼望而默想,因默想而乱猜——这恐怕是人之常情罢!
阿弥陀佛!今天接着你的回信了。接着信的时候,不觉得什么喜欢,不觉得什么兴奋,但觉得得到了许多安慰。
为什么盼望来信呢?大约是为着要得到一点安慰罢。
是信呢?还是安慰呢?……
宋若瑜在蒋光慈的“进攻”下,彻底熔化了。年轻的姑娘“缴械投降”,可怜地回应道:
我现在才相信爱情的势力是可以支配人的一切的,才知道恋爱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自从和你结下了不可解除的恋爱结,我的一颗赤裸裸的心无时不是紧紧的系在你的身上。
这场恋爱,不仅使蒋光慈身心愉悦,也激发了他的创造潜能的爆发。他在致宋若瑜的信中曾说道:
近来中国文学界无甚大发展。所谓新诗人、新文学家,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可是他们的作品,真太不成形了。在内容方面,他们固无足取,即在技术方面,他们也幼稚已极,拿起笔来就是诗,一至于诗与白话混淆,分不清什么是白话,什么是诗。不错,新诗是要用白话体的,但是并不是一切白话都是诗罢。我很有点志愿办一个文学刊物,振作中国的文学界。可是一个人精力有限,在最近期间,这种志愿是达不到的。
话虽这么说,他还是抓紧时间,说干就干。不几天,他和沈泽民等人创办的文学刊物,就筹备就绪了。给宋若瑜写信后不到半个月,他们就在《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登出了《春雷文学社小启事》,说组织这个文学社的“宗旨是想尽一切力量,挽一挽现代文学界‘靡靡之音’的潮流,预备每星期在《觉悟》上出文学专号,请读者注意”。第二天,周刊性的“文学专号”便创刊了。
第二年,蒋光慈编定、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新梦》。这是他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大厦奠定的第一块基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献给俄国十月革命的歌集。在当时,《新梦》的产生,“不啻是一颗爆裂弹”!
这颗爆裂弹带来了不少的关于“世界革命”的消息!这颗爆裂弹,惊醒了许多左倾的青年,把他们从沉梦拖了出来!这颗爆裂弹告诉我们,只有“世界革命是我们的唯一的出路”!
继诗作《新梦》之后,1926年1月,中篇小说《少年飘泊者》也终于付梓。这些都是在他们热恋中完稿推出的。用蒋光慈的话说,是若瑜给了他“安慰”,是爱情给了他无穷的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