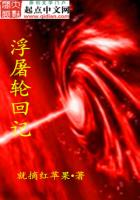中华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在《诗》、《书》、《周礼》、《仪礼》、《礼记》、《易》、《公羊传》、《谷梁传》、《左传》、《论语》、《孟子》、《尔雅》、《孝经》“十三经”的基础上,历代学者又不断为这些经作注。对“经”所作的注叫传,对传所作的注叫疏,另外还有像章句、集解、笺、释等都是众经的衍生物,形成“经学”的泱泱大国风范。在思想领域,儒家虽堪称一尊,但佛、道亦不失存在的地盘。在中国文学史上,自《诗经》开始,到先秦散文、汉赋、魏晋骈文、传奇,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成为中华文化又一支巨流,历代的文学批评家们对这些作品的考释又不断充实着这一支文化巨流的内涵。有人统计,仅《红楼梦》研究成果的字数已超过《红楼梦》原著的250倍。在中国史学史上,像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等撰成的二十五史大体汇集了历代王朝的文治武功与广大人民的辉煌建树。其他像中华文化中的书法、绘画,以实物形态呈现出来的建筑,以生活习俗呈现出来的人生礼仪、四季节庆都内涵丰富。
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确实一点都不过分。有人或把她分为精英文化、庶民文化;有的把她分为高雅文化、通俗文化。我想,人们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存在着层次的不同是确定无疑的。
在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士仁人那里,传统典籍文化是他们研习的对象。他们致力于推进“天下大同”的神圣事业,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不断肩承着继往开来的历史大任,像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像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像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壮怀激烈,前赴后继,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构成为中华文化中范型人物的长廊,他们以无穷的榜样力量,激励着后来人不断高擎起光大中华文化的旗帜。
中国传统社会曾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把对传统儒家经典的研习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尺度,因而在学校里,在社会上,都有无数的生民陶育在儒家浓郁的氛围中,他们注重人生立品的重要性,多强调“士先器识而后文章”,先德而后艺;他们亦多注重建立起和谐的社会人伦秩序,事亲、敬长、尊老、爱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们还抱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积极向上精神,“敬贤而思齐”,“尊贤人而远佞臣”,为了给子女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不惜三迁、断梭;他们也多以“克己奉公”的精神自觉抵御着各种不良风气的侵袭。从整个中华文明史上看,他们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量。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确实存在着优胜劣汰的发展规律,有的人不信《礼》、《易》、《诗》、《书》,却把《水浒》、《三国》、《金瓶梅》、《西游记》看作是中华文化的集中体现,人们常常称颂关公的忠,诋毁曹操的奸,诅咒西门庆的淫佚,赞扬孙悟空的勇武……其实,考察一下明清小说的创作者们的身世,我们便不难明白,他们多为科举落第者,是一群想有所为却又被堵了进取之路的文人,他们谙熟社会上的黑暗面,多怀满腹牢骚,因而在小说中多用反讽笔调,与中称颂关羽,却也凸显了关羽的专横(看不起黄忠,有时身在沙场,却想着与同僚比武以决高低;看不起陆逊,以致失了荆州),虚夸(刮骨疗毒时故意以下棋来显示其豪气,从身体本身看,显然得不偿失)。书中称颂李逵,却也凸显了李逵的凶残(杀死无辜小孩,一块一块地割下黄文炳的肉在火上炙熟吞食)。书中称颂刘备,却也凸显其无能担其大任(每每出兵,总是大败而归,不仅如此,每次败后还埋怨“天不佑我”,号啕大哭,束手无策,与曹操败后从敌阵中突出后还豪放地大笑,并检讨对方的失误形成鲜明对照)。总而言之,效法英雄时常并不能使自己臻于完美的境界,反而贻害自己,故有人说,中华文化中蕴含着浓重的“水浒气”、“三国气”,倘把这些理解为就是中华文化的全部,并加以发扬光大,势必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时下许多青年人经常正是由此而认识中华传统文化,因而或误入歧途,或矢志抵拒,在他们的心目中,如此糟糕的中华文化徒然滋长帮派意识,徒然滋长破坏精神,于社会的发展进步无补。
我们以为,对中华文化的认识不能仅停留在片段的理解上。明清小说实质上多为研习了传统文化经典的人们在人生理想破灭后对现实世俗恶风陋习的鞭挞与揭露,有时也憧憬着理想社会状态的到来。倘若我们把它们所披露的传统文化中的不健康因素就看作是传统文化本身,便不免舍本逐末,无法求得对中华文化真谛的认识。我们应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研习中华传统典籍文化的风气,通过析薪传火,使中华文化的优良部分不断得以发扬光大。
(原刊《世界日报》1998年2月1日、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