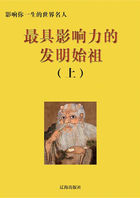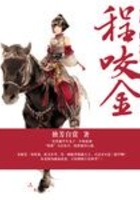这部书的缘起,始于2012年,当时《南方都市报》的记者联络我,希望我协助他们为先父宋淇做一个每周专题系列。我当下便问:“你们为什么对我父亲感兴趣呢?或者说,怎见得你们的读者会感兴趣呢?”他们答,因为我父亲在多个领域都颇有名气,但大众却对他认识不深。这也是实情。
对影迷来说,他是香港国语电影业的先锋;对张迷而言,他是张爱玲的好友兼顾问,多年来协助她写作和出书;在红学领域,他是最早提倡以文本为先的红学家之一;在翻译界,别的不说,他早在米沃什(Czeslaw Milosz)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已别具慧眼译出《攻心记》(The Captive Mind,2013年简体中文版名为《被禁锢的头脑》),单此一事已足够令他声名鹊起。当然他的成就远不止此,不同的人会窥见他的不同面貌,但能一睹全豹的却绝无仅有。要令人们更了解他,显然需要一部传记。
然后我再问记者:“这每周专题将持续多久?”他们答,已准备连载廿周,每期有一整页的篇幅。我叫他们还是三思,因为我实在难以想象,一份商业性质的报纸居然会给这类专题这么多宝贵的版面,但他们十分坚定。就这样,宋淇系列便正式开始了。
第一期刊于2012年9月4日的《南方都市报》,最后一期则是2013年8月27日,结果一年来总共刊出了四十二期,远超过他们预想的廿周。这系列文章就成为了本书的基础。
当初联络我时,《南方都市报》显然认为要认识宋淇,最好就是问他的儿子。一般来说这是对的,但现实并没有那么理想。我现在掌握的资料,主要有三个来源。
首先是我自己的回忆,包括父亲和亲戚告诉我的家庭往事。然而在1968年,我十九岁时,已只身到澳洲留学,跟香港的双亲分隔两地,一直到2003年才回港定居。我年少时,父亲并没有告诉我很多他自己或家中的事。1985年,我正式成为美国公民,之后回港短住。其间跟父亲闲聊,最佳的话题似乎就是家族史了。但我不认为他讲的都真有其事,因为有些情节实在太耐人寻味,我觉得他自己在加油添醋。他在1996年去世,母亲则在2007年去世。其后,我拿这些故事向姐姐求证,她说大部分闻所未闻。现在,已没有谁可以再问了。早知如此,我当年便应该向父母查明个中曲折,但一切都来不及了。和很多口述史一样,我这里要复述的故事也难免真假夹杂。
其次是已经刊行的文献,例如父亲写我祖父宋春舫的《毛姆与我的父亲》、提及他和张爱玲友谊的《私语张爱玲》等。这类资料的问题是,尽管在个别事件或人物上提供了很多细节,但涵盖的范围太狭窄、太片面,不足以连成一篇完整的传记。
最后一种则来自未刊的手稿和书信。我父亲跟好几位名作家都是好友,如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等,通信数以百计。这批手稿不但反映了他们彼此的友谊,也展露了各人的思想性情。以张爱玲为例,她的信中便有大量珍贵资料,可以令我们对她的文学作品有崭新的理解。
以上几类资料无疑各有局限,但我也不得不用作本书的依据。有些事,如果我手头刚好有详细资料,我可以多说一点;如果我所知有限,我就没有什么可说。读者看完这本书之后,可能会觉得张爱玲是我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因为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跟她有关。实情不一定如此,只是张爱玲恰巧留下了大批书信,资料最多,所以篇幅便最多了。举个反例,父亲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了十多年,这段日子不能说不重要,可惜我所知有限,也只能轻描淡写地带过。
另外,《南方都市报》刊出文章时,因版面所限而删减了部分内容,现在已逐一补入;我也稍为增加了一些新内容,如讨论《相见欢》的那篇和结语中的那个故事。原来有些较口语化的句子,我在书中也做了修订,力求风格一致。
但愿以上所述能解释明白这部书的来龙去脉。
本书得以出版,实有赖《南方都市报》协助,特别是记者陈晓勤,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