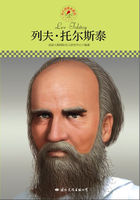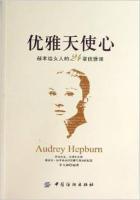柴可夫斯基和阿纳托里在1877年11月到达意大利后,突然感到恹恹无生气,不过停留威尼斯期间仍努力将《叶甫根尼·奥涅金》的第一幕写好了。这时,阿纳托里接到达维多夫(亚历山德拉的夫婿)的一封信,要他立刻回去把米柳柯娃带离卡明卡。柴可夫斯基陪伴阿纳托里去维也纳,一方面是为他送别,另一方面是迎接替代阿纳托里的索伏朗诺夫。
他和梅克夫人仍书信往来不断。12月8日他从维也纳写信给她,说他发现瓦格纳的歌剧演出令人生厌,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也同样让他无动于衷。又说,他认为法国作曲家的作品反而引起他热烈的共鸣。在听过德利伯的《雪尔维亚》芭蕾舞曲以后,他告诉梅克夫人,说自己的《天鹅湖》和《雪尔维亚》比较起来真是非常贫乏,在过去几年间,除了《卡门》之外,要以德利伯的乐曲最令他欣赏了。
送走阿纳托里及接过索伏朗诺夫后,柴可夫斯基离开维也纳,在威尼斯小住,继续编写《第四交响曲》。他发现梅克夫人已经耽溺于酗酒及音乐之间时,12月15日找到个机会道出了心中的不悦:“一个男人借酒浇愁时,为的是麻醉自己及产生幻觉。但是这种幻觉的成本很高……酒只能暂时使我们忘却烦恼……音乐却并非幻觉,而是发泄……”
他这番话似嫌过分,因为,不久之后他也向阿纳托里承认自己喝得很多,而且这种习惯终其一生都未曾改变:“我没有酒就活不下去。不多喝点的话,我永远享受不到宁静。我自己早已习惯于偷饮,看到身旁的酒瓶时,心中不禁暗暗窃喜。”
柴可夫斯基在1878年1月准备和莫杰斯特及康德拉契耶夫一起度假。他意外地发现,音乐学院的会计主任写信告诉他,代表俄国参加巴黎博览会的差旅费是1000卢布。他已经完全忘记那回事,而政府当局因他没有动静而误认作是接受派遣。事已至此,他只好借口身体不适,不能前去。
尼古拉费尽心力,结果却换来了柴可夫斯基的装病逃避。柴可夫斯基的答复是,即使他肯去巴黎,俄国音乐的影响也不会扩大。至于假装生病的问题,他的解释是:“你太不了解我……可能你没有错,我真是在装病……但那正是我的真正本质。”
尼古拉对他这种诡辩做何反应,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柴可夫斯基却始终坚持不去巴黎。尽管有这些事件的困扰,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仍在1月7日完成,3天后送往莫斯科。尼古拉在2月22日首演以前一直没发表意见,甚至演奏后也不表示自己的观感或是听众的反应如何。
当柴可夫斯基正在为此纳闷时,高兴地接到梅克夫人来信,说交响乐团的演奏虽然并不理想,但这新交响曲首度演出相当成功。她问他这作品是否有个主题时,柴可夫斯基的答复是洋洋洒洒的一大篇:
今天收到你的来信,我非常高兴,得知你很欣赏新交响曲,我更是喜出望外……你问我在编写时曾否考虑过要给它定个主题,通常我对这种问题的答复是“没有”,这个问题实在也很难答复。《第四交响曲》有一个主题,也就是说可用文字表达它的内容。我要把全部乐曲及每一乐章的含意讲给你一个人听。
序曲是全部乐曲的思想中心,它所代表的是命运。那种无可逃避的力量,能使我们寻求快乐的抱负在没达成以前就半途而废,它妒忌地不让我们的安宁与幸福完整无瑕……这种力量是无可征服的,我们除了顺从它或自怨自艾之外,别无选择的余地。
毫无前途的绝望感受越来越强烈,而且越来越尖锐。是不是脱离现实后迷失在梦乡中反倒好些?一种甜美而亲切的梦包围着我,一种光明而神圣的大道引导我前进。灵魂在梦乡中无比的深沉,一切黑暗与痛苦都可忘却,那里只有快乐。
然而,那不过是个梦而已!命运粗暴地惊醒了我们。一切的生活只是痛苦的实际经验和稍纵即逝的快乐美梦继续不停地交相更替。这里不是天堂,大海在吞没我们以前,我们都被波涛驱策得东翻西滚。第一乐章的主题大致就是这样。
第二乐章表示另一个阶段的遭遇。当我们独自在家中不愿工作时,忧郁感会乘虚而入偷袭我们,同时,我们挑来排遣时光的书,会不经意地滑落到地上。经过一长串的回忆后,往往倍增感伤!不过,那些幼时的事回想起来倒是很甜美。我们既无勇气且缺乏意念来开创新生活,自然对过去不胜怀念与怜惜。说起来我们都非常惧怕面对现实,我们十分希望能多休息些时候,以便能回顾往事。
有时,若我们的血管中流动着鲜血,生活就为我们带来所向往的东西。有时,我们的心中只有悲伤与无法挽回的失望,但那都已随着时间的飞逝而逐渐消失。我们消逝在过去里的是我们的无限伤感,但同时也可以说它夹杂着若干甜美的回忆。
第三乐章中并没有表现某种固定的情感,那里面只有反复无常的姿态及无从捉摸的格调,是一个人在酒酣耳热,飘飘然之时,脑子里所想的东西。那时的情绪是既不愉悦也不悲伤,似乎并没有特定的思考主题,幻想更是自由自在纵横无阻,结果乃产生出一种最奇特的感受,可能突然间想起酒醉农夫或一首街坊上的歌谣,也可能感觉到远处传来一阵军乐声。这也是在入睡时常会遭遇到的复杂景象,它和实际生活并无关联。
第四乐章表明了一点:如果你自己寻找不到快乐的理由,去看看别人。看他们是怎样享受生活情趣,看看他们是如何把自己投入欢乐之中。它描述的是一个乡村假期,当我们看到别人高兴时,几乎还没来得及忘却自己,无情的命运就又再度前来干涉我个人。别人却不管我们如何,不但看也不看,更不注意我们是如何孤独及如何悲伤……你是否还要说整个世界都是陷在悲愁之中呢?快乐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在别人的欢乐中寻求你自己的欢乐吧!这样可使你的生活变得可以忍受。
我对这交响曲再也没有可说的了。自然,我的描述不很清楚,它不能使你完全满意,而且器乐方面的特点无法加以分析……
附言:我在这封信付邮前,又把它读过一次。我对这复杂且不完整的主题深感不安,因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将自己的音乐思想及形式以文词表达,这份工作并不很成功。我去年冬天编写这首交响曲时,精神始终提不起来。实际上它是我当时的感情反应,但那也只不过是一种反应而已。
至于怎样才能以清楚及肯定的语言把它加以重新编写,我并不知道。我早已忘却很多事情了,只有热情及痛苦经验的一般印象仍然存在。我急于知道在莫斯科的朋友对我的作品作何感想。
这封信是1878年3月1日从佛罗伦萨发出的,《叶甫根尼·奥涅金》恰好在一个月以前完成。他后来告诉塔涅耶夫说:“我编写它时就知道它不会成功,然而我仍把它完成。如果尤尔根松有意出版,我愿把它公之于世。”
交响曲及歌剧均已写妥,柴可夫斯基心满意足地在佛罗伦萨休闲度日。他的身体康复,精神焕发,这要归功于3个人:莫杰斯特、阿纳托里和梅克夫人。他和莫杰斯特、康德拉契耶夫及索伏朗诺夫在3月中旬回到瑞士。他们在一起演奏了许多新乐曲,其中包括他特别欣赏的《西班牙交响曲》。极可能是受了拉罗的这首乐曲鼓励,他才一面编写《G小调钢琴奏鸣曲》,一面从事《提琴协奏曲》工作。他对梅克夫人说:“在一首乐曲未完成前就动手写另一首,这还是我生平第一次。”
《提琴协奏曲》在4月初完成后,他自己及准备初次演奏它的柯代克都不满意,于是改用现今被称为《短歌》的那首乐曲替换。柴可夫斯基加紧谱写《短歌》,当《短歌》在4月11日大功告成时,柯代克已对它毫无兴趣,接受柴可夫斯基献赠的朋友也表示没办法演奏。它直至1881年底才由另一位名人在维也纳作首度演出。
尼古拉3月22日在莫斯科演奏《第一钢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对尼古拉改变态度甚感高兴,他说:“一开始我就相信他会演奏得很好。这乐曲本是为他编写的,我曾针对他的高超技巧考虑再三。”最后其他朋友也同样成为拥护《提琴协奏曲》的人。
在返回俄国的行期接近时,柴可夫斯基心中极为不安。他已经安逸地享受着新发现的自由生活,他写信给梅克夫人说,他想辞去音乐学院工作:“过了几个月自由自在的生活后,再回去教学生,对一个完全不适于那种工作的人来说,可真是乏味!我无法使你正确地了解我自贬身价的感受。”
他对俄国政局不稳的消息颇为担忧。“社会主义暴动分子在年初时取得优势。他们一面煽动农民革命,一面以谋杀高级政府官员为手段来瘫痪政府。”他在起程回国时,深为西方国家报纸上连篇累牍的谣言而感到痛心。4月20日他从维也纳写信给梅克夫人,说他自己的精神还好,极有活力,请她放心。他在4天后抵达卡明卡。
柴可夫斯基看到达维多夫等人仍如往常一样热情接待他时,心中十分愉快。他随即开始工作,新的钢琴奏鸣曲于4月底完成,同时并着手为儿童编写24首小型的钢琴曲。
他和米柳柯娃离婚的一些手续交给阿纳托里办理,而且从梅克夫人那里得到出资1万卢布的承诺。梅克夫人为了慰劳柴可夫斯基,邀他前去布莱洛夫乡下的别墅小住。他满心感激地住下以后,在那优美的环境中再次寻求适当的歌剧题材。一开始,他曾考虑过《水妖记》,但最后选择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他写信告诉莫杰斯特说:“它使我泪如雨下……希望听众们的心境也能和我编写时一样。”
6月13日柴可夫斯基再度在莫斯科露面。第二天,参加尼古拉的生日酒会时,他发现尼古拉的脸上显露出不悦的神情。柴可夫斯基写了封信给梅克夫人提到这件事:“他因为我不肯担任俄国代表去参加巴黎博览会,所以一直不原谅我。他认为我应该接受那番好意,凡是不领他情的人他都不喜欢。他希望所有在他身边的人都能感激他的栽培,而我在他的心目中似乎已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这可从他的表情中看得出来。”
柴可夫斯基是为处理离婚手续而前去莫斯科的,但是米柳柯娃却不见踪影。于是他趁机逃往卡明卡,将一切留给尤尔根松办理。最后,米柳柯娃露面了,她坚决否认曾经同意过离婚。尤尔根松无可奈何,允诺给她一笔钱,请她离开莫斯科。
柴可夫斯基安全地回到莫斯科时,已决定要通知尼古拉,说他决心辞去音乐学院的教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