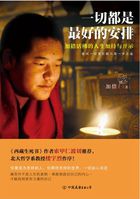刘云
一、现代化改革的政治结构背景与动机
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并不是经济上已经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财产并要求参与政治而肇始的,改革的启动以及整个过程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模式的典型,其目的是为了保护王室、行政与军事官僚的政治利益。它既不受上升中的资产阶级利益的引导,也没有开明专制主义精神的指导,它的目的是要在西方列强和欧洲文明日益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中维护奥斯曼帝国的统一。
采纳现代西方的科学技术与西方国家的组织机构对奥斯曼帝国来说都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有力手段。
奥斯曼帝国现代化改革的直接原因当然是帝国的衰弱,而导致衰弱的背景既有外部的威胁,也有内部的政治结构问题。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发展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明确的事件来界定帝国的衰落。但也有许多的事件表明了这一变化的过程。例如刘易斯就将《卡尔洛维茨条约》看成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这是奥斯曼帝国在一场胜负分明的战争中第一次作为战败国一方签订的一项条约,并且被迫把长期属于奥斯曼人统治下的、被视为是伊斯兰园地的一部分大片领土,割让给了异教敌人。”
按照卡尔·布朗的观点,1774年《库屈克条约》的签订则是一个转折点。随着1768-1774年俄土战争的结束,帝国失去了克里米亚汗国(宣布独立)和在黑海的霸权。
其实,从奥斯曼帝国1683年在维也纳的失败到希腊独立战争(1821-1829)期间的一系列历史事件,都可以看成是帝国走向解体的标志。但是比较明显的是从18世纪以后,帝国就被拖入了与欧洲列强的无休止的战争之中,而且不断地失利。在不断变化的同盟与敌国的关系中,奥斯曼帝国变成了俄国、哈布斯堡帝国、英国、法国和普鲁士等欧洲五强之后的第六个玩家。自从《库屈克条约》以来,奥斯曼帝国变成了内外战争的战场,这导致了大量的领土的丧失。
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也沉重地打击了帝国的统一。世纪之交沙特王国的扩张(1806年其宗教部落军队夺取了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穆罕默德·阿里统治下的埃及实际上的独立以及他对叙利亚和西里西亚奥斯曼省份的占领、黎巴嫩的艾米尔巴夏尔·希哈布二世的独立运动(1788-1840)、阿赫马德贝伊领导下的突尼斯的现代化和独立的突尼斯的形成,都说明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与现代中东政治地图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比阿拉伯地区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奥斯曼帝国的欧洲省份。1804-1806年和1815-1817年的塞尔维亚人的起义、1821-1829年的希腊独立战争、1857和1875年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起义和1876年保加利亚人的起义,都说明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统治是极不稳定的。
随着希腊独立战争的开始,国际势力、地区势力和地方势力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了。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以牺牲奥斯曼帝国为代价要解决巴尔干地区的少数民族问题时,它们又要打算支持奥斯曼帝国成为抵御俄国的堡垒。之所以有这种矛盾,是因为巴尔干的事务不仅与欧洲列强的权力平衡有关,而且与欧洲各国的民众有关,他们支持民族主义运动,并推动他们的政府对民族主义运动进行干预。从奥斯曼帝国的角度看,衰弱的帝国正在被拖入种种政治实体的权力斗争之中——国家、准国家、地方公国、民族与宗教集团,它们都以民族主义话语为他们志在独立的行动辩护。而且,在它们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斗争中,国外和国内的力量结合起来了。奥斯曼帝国统治上层陷入了国际阴谋与国内叛乱双重困境之中。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它的维持与强大依赖于在对外扩张中不断取得胜利,从而有更多的土地和战利品来推动帝国庞大的军事官僚机器。“所有奥斯曼人的军事组织、民政、税收和土地制度等,都是配合征服和殖民而不断向异教者的地方实行扩张这个需要来制订的。”
奥斯曼帝国的快速扩张为朝廷和统治上层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土地、贡品、战利品以及其它资源。军事上的失败必然会动摇帝国的整个军事与社会制度。
如果只以欧洲列强的冲击来分析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改革是片面的。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还有强大的内部动因,那就是内部的社会变化引起的加强中央集权和进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改革最主要的内部动力来自帝国各地的地方分离力量。当帝国在新的国际体系中寻求新的作用时,它在内部陷入了地方分权化的危险之中。
蒂玛制度(Timar System)和禁卫军(Janissary)制度是奥斯曼军事封建制度的支柱。蒂玛即素丹给军人们分封的采邑,军人们从蒂玛中获得经济收入,同时要在战时为素丹提供军事义务。这种分封土地的制度就是蒂玛制度,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使素丹不必支付军费而拥有一支强大的封建骑兵,而且在于对农业人口的控制。同时,通过蒂玛制度素丹还有效地防止了省督、军官和地方贵族的权力膨胀,使素丹获得了相对高度集中的中央权力。但是16世纪晚期以来,由于帝国经济的萧条,蒂玛持有者的农业收入急剧下降,再加上在对外战争中不能取得胜利而得不到战利品,许多蒂玛持有者对军事义务失去了兴趣,有些人索性放弃了蒂玛,或逃往城市,或参加日益壮大的土匪队伍,有些平民甚至通过贿赂非法取得蒂玛。
中央政府为了保证得到财政收入,素丹开始将采邑作为包税地分封给与军事义务无关的社会上层。国家控制的蒂玛制度逐渐地向半自治的包税制转变。蒂玛制度和封建骑兵严重地衰落了,奥斯曼帝国得以维持和强大的一个重要支柱坍塌了。
由于蒂玛制度和封建骑兵的衰退,素丹只好靠加强和扩大禁卫军来满足帝国的军事需要。禁卫军是奥斯曼帝国的常备军,也一度是奥斯曼帝国的精英部队,绝对地忠诚素丹和奥斯曼国家。
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中央集权削弱的过程中,禁卫军的权力越来越大,成为左右朝政的重要力量。1618-1730年,至少有六位素丹被禁卫军赶下台。
1682年禁卫军的将领第一次在乌勒玛的支持下被任命为大维齐。
禁卫军、地方乡绅、低级乌勒玛等传统势力还经常联合起来挑起社会叛乱、阻挠改革。
18世纪初,禁卫军已经无力在对外战争中抵抗外国侵略者,但它的力量却仍足以阻挠国内的任何改革。
地方势力权力的不断膨胀也严重地侵蚀着素丹和中央政府的权力。地方势力分为三类:由乌勒玛、卡迪和穆夫提组成的宗教集团;地方驻军和近卫军组成的军官集团;权威根植于优越社会地位的贵族家族的阿扬和德雷贝伊。显然,地方势力既来自于中央政府的管理部门,也来自于当地的贵族家庭。在科普吕吕任大维齐时期(1689-1691年),中央政府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来防止省督们滥用权力并约束禁卫军。但是对省督权力的限制却方便了新的地方势力阿扬(Ayan,乡绅)的成长。阿扬是地方乡绅,管理地方的公共事务,可以影响中央政府的决定。为了对付地方政府的离心倾向,中央政府不情愿地加强了阿扬的地位。在18世纪行政与财政紧张之时,中央政府日益将行政职能赋予阿扬,他们“开始类似于那些可以在自己永久拥有的土地上拥有私人军队、征收赋税并管理司法的贵族”。另一种掌握地方权力的人是德雷贝伊(Derebey,山区地主),他们主要是17世纪奥斯曼帝国各省的行政管理衰弱时出现于安那托利亚。18世纪末,鲁米利亚(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的许多地方和几乎整个安那托利亚都处于德雷贝伊的控制之下,支配着大量的武装力量。德雷贝伊在他们的世袭王国中进行自治性的统治,其权力在谢里姆三世时达到了高峰。由于对外战争的需要,帝国把主要的军事力量从内地调往前线,这进一步加强了地方势力的权力。由于战争的失败、领土的丧失、前线开支的增大,帝国的安全形势与经济条件都恶化了。地方乡绅对物质资源的控制、德雷贝伊现象、非正规军队和雇佣军的出现都清楚地表明了中央政府控制能力的丧失。由于对外战争的需要,帝国把主要的军事力量从内地调往前线,这进一步加强了地方势力的权力。
奥斯曼帝国的内外安全的衰弱与其政治经济的急剧变化是相互依赖的:国家控制的蒂玛制度逐渐地向半自治的包税制转变。在经济条件变化的情况下,国家必须保证得到财政收入。素丹将采邑开始分封给社会上层,其中包括政府官员和阿扬。起初,这些包税地的授予只是短期的,但后来这些给予包税人的利益被滥用,变得可以继承了可以转让了。
当欧洲在加强国家对物质资源和税收的垄断时,奥斯曼帝国却在逐渐地失去控制力,变得越来越依赖地方势力和各职能部门。这种政治经济的变化也影响了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合法性。奥斯曼帝国社会阶层的形成是建立在传统秩序基础上的,这种传统秩序中“公正”是稳定的关键概念。“它意味着社会中的每一个集团和个人都各得其所,不侵犯他人的权利。”
上层统治阶层的特权只有在他们能够维持这种秩序并能保护穆斯林社会免受外部侵略时才是合法的。
现代化进程与帝国的统治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对理解帝国统治者在面对19世纪的“东方问题”时面临的困境是非常重要的。近卫军、省督、阿扬和德雷贝伊的桀骜不服已经清楚地表明帝国中央权力丧失问题的严重性。有些情况下,这一过程导致了一些省份的完全丧失。地方领袖们垄断了当地的政治和经济资源,这最终导致了一些的国家的形成。在正在形成的国家体系的国际关系框架内,奥斯曼帝国的地方分权是中东和巴尔干地区现代国家形成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对外战争的失利、禁卫军的飞扬跋扈、地方势力的权重、内部安全的削弱、包税人营私舞弊,都对中央权力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严重地削弱了奥斯曼政府的中央集权。
为了帝国的生存,为了恢复和加强素丹及中央政府对帝国的有效统治,就必须拥有一支技术上更有效率、政治上更可靠的军队。正是这种需要引发了帝国的军事现代化改革。
二、现代化改革的进程与特征
谢里姆三世1792-1796年的改革一般被看作是奥斯曼现代化改革的序幕。军事改革是谢里姆三世改革的主要内容。他对欧式的训练方式和法国教官的接受标志着他与奥斯曼素丹过去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分离,过去素丹总是倾向于维护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制度。谢里姆三世启动了帝国的改革。在新开设的军事学校中聘用外国教官、派官员去欧洲考察、在欧洲各国建立常设大使馆,都为欧洲思想在奥斯曼帝国的传播奠定了制度基础。
但是,谢里姆三世遇到了禁卫军的叛乱且被推翻。
1826年5月,马哈穆德二世和他的新军粉碎了禁卫军的叛乱,并宣布取消禁卫军。
传统势力因此失去了武装力量的支持,这标志着以加强中央集权为目标的军事、法律和行政改革的新时代的开始。马哈穆德还镇压了与禁卫军有密切联系的贝克塔希教团的叛乱,取消了他们的道堂,同时将宗教瓦克夫收归国家统一管理。这些措施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宗教部门的控制。
1826年马哈穆德平息了省督们和封建主的叛乱,并很快废除了蒂玛制度和封建骑兵制度,建立文官为省长的地方行政机构管理地方事务。由于军队和政府机构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员的需要,马哈穆德二世又开设了军事学校。
奥斯曼帝国现代化最初是在封建君主和封建官僚的主导下启动的。没有传统社会势力的最初参与,现代化要成为一种主动的改革进程是不可能的。素丹的改革也得到了其他传统势力的支持。1808年素丹马哈穆德二世就是在贝伊拉克塔尔·穆斯塔法帕夏领导的阿扬联合力量的帮助之下掌权的,穆斯塔法帕夏在谢里姆三世退位之后变成了改革的支持者。素丹承认了阿扬在各省已经获得的实际权力,具有世袭性地位的阿扬则完全支持素丹对军队的重组以及对军事和税收的最高权力。
高级乌勒玛是马哈穆德二世时期支持改革的又一传统社会力量。作为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乌勒玛为了宗教与国家的利益而支持改革。
他们是宗教权威,他们对改革的支持安抚了低级乌勒玛和民众的不安情绪。但是乌勒玛又是改革的对象,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他们的权利与地位在逐渐地被削弱,这是改革进程的明显特征。
谢里姆三世和马哈穆德二世改革的重要性并不在其实际成就,而在于这些改革导致的对以后帝国现代化发生重要作用的一些间接后果。首先,随着改革的发展,出现了现代官僚阶层,尤其是1833年最高波尔特翻译局的设立及其规模和重要性的增长,使帝国的现代官僚阶层在制度框架内开始形成了强大的势力,成为日后推动改革的主要力量。日后许多改革派的重要人物都出自最高波尔特翻译局。他们是奥斯曼帝国的精英,他们的权力来源于素丹,来源于国家机器的现代化过程。这些新型的社会力量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希望保护国家机器免受来自内部和外部威胁。以这些新的官僚阶层为核心,现代政府职能部门和相应的管理机构发展起来了。当然,马哈穆德时期的行政机构远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所要求的行政管理结构。另外,帝国时期的改革奠定了以军官和文职官僚精英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模式,我们将奥斯曼-土耳其现代化的这种模式定义为权威主义模式,就是在这种模式下,帝国走上了主动的现代化道路,这种模式至今仍然影响着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
奥斯曼帝国传统政治机构的加速改变是坦志马特(Tanzimat,意为改革)改革开始之后的事,它开始于1839年颁的第一个坦志马特敕令,结束于1878年素丹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解散奥斯曼帝国第一届国会之时。
在坦志马特改革的第一阶段,现代化改革深入到了司法、行政、教育等领域,引起了奥斯曼帝国社会结构的重大改变。由于帝国的行政、军事、教育机构改革而形成的新的社会力量,在后来土耳其共和国的形成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坦志马特的主要成就是:取消世袭性的包税制,创立了现代货币制度和税收制度;
教育和司法的世俗化制度逐渐形成;政府职能部门的科层化;帝国议会和宪法的产生;
武装力量按内外不同的两个领域进行了划分;现代地方管理制度的引进。
所有这些都说明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制度发生了向法治制度的转变,这些变化都是以帝国诏令的方式推动的。第一个诏令“哈蒂-沙里夫”(Hatt-i Sherif)将矛头对准了地方分权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了遏制腐败的包税人的独立性和保证国家的防务资源,提出实行常规性的固定税收制度。诏令还宣布不管信仰何种宗教与教派,保证所有臣民的财产与公民权;实行普遍兵役制,服役期限减少为四到五年;按照法国的模式重组省一级的行政机构,地方官员的收入为固定薪金,个人财产与政府管理资源要明确地分开。
坦志马特改革的第二个时期开始于1856年1月颁布的“哈蒂-胡马云”(Hatt-i Hu-mayun)。在这一诏令中,素丹麦积德重申了宗教自由和非穆斯林臣民的平等地位,还规定了防止腐败和司法中的刑讯逼供的措施;颁布了保护贸易和商业不受阻碍的条例。19世纪60年代,建立了许多世俗法庭,颁布了世俗刑法、商法、海运法和贸易法,所有这些新的法律都是按欧洲的样式制定的。
除政治行政改革之外,进一步向国际贸易和外国资本开放帝国领土是坦志马特第二阶段的重要内容。欧洲的商品可以自由地进入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因此失去了专卖、税收、关税等许多商业方面的特权,本来这些权利可以用来防止帝国财政的进一步恶化。
1954年,也就是麦积德的改革诏令颁布的前两年,帝国政府为了解决由于克里米亚战争造成的财政问题开始向国外借款。16年之后,帝国政府已经完全依赖外国的贷款了,同时还款支出每年要花掉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最终导致帝国财政在1875年破产。
坦志马特改革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时地方分权的发展和列强的压力而提出的。1839年哈蒂-沙里夫诏令颁布时,国内的分离主义已经威胁到了帝国的领土统一。
塞尔维亚人的起义、希腊独立战争、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以及他对伊斯坦布尔政权的合法性提出的挑战,都说明改革诏令的颁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这种背景下,1830年代和1840年代的改革矛头就直接对准了地方分权势力。
坦志马特第二时期的改革实际上是西方列强意志的体现,是在英法等国的胁迫下进行的。
俄国于1853年7月占领了奥斯曼帝国的多瑙河各省。自1853年10月以来,英国、法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就一直在与俄国军队作战。哈蒂-胡马云的颁布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促使欧洲列强在巴黎会议上接受奥斯曼帝国。巴黎和约的第七条宣布签字国尊重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领土统一。而且,条约规定所有俄国军队占领的奥斯曼帝国领土要归还给帝国。改革的内容是大国压力的产物,含有迎合西方的一面,是为了在所谓的“东方问题”获得欧洲列强的支持,从而维护奥斯曼帝国的统一与主权。
阿布杜勒哈米德在位的三十多年通常被认为是专制主义统治时期,但他继续进行着现代化和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他极大地扩展了帝国的教育改革,加强了通讯设施的建设。尽管他执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但报纸、杂志和书籍却进一步增多,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将更多的西方思想带到了土耳其,其影响也日益增加。
国家行政管理方面的现代化在继续进行。他使用现代国家机构进行监视,他创造了国家监督民众以保证素丹统治的必要方式。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具有这样一些特征:改革是由封建君主和封建官僚启动的,而后来现代官僚又成为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帝国的统一和保护国家机器免受内外的威胁,同时保护官僚上层的利益;改革的模式是自上而下的权威主义模式;许多改革措施与西方列强有密切关系、与所谓“东方问题”密不可分;改革首先在军事领域,后来主要在军事与政治领域进行,经济现代化长期被忽视,与经济有关的一些措施其着眼点是税收问题。
三、奥斯曼帝国改革的后果
加强中央集权的现代化改革中出现的现代力量对奥斯曼帝国最高权威提出了挑战,这是改革的实施者没有想到也不愿看到的事情。军官、行政人员、教师、知识分子等现代职业阶层,与国家的现代机构存在着直接联系,他们的人数不断增长,要求进一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教育改革提高了城市识字率。19世纪后半期,这些识字的公众成了谈论政治的重要人群。立宪与代议制思想的兴起、少数民族中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穆斯林人口中泛土耳其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思想的上升,都与识字人口的增加有关。1865年,“青年奥斯曼人”开始宣传他们的思想。他们主张在伊斯兰原则基础上实行宪政和代议制制度;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反对阿扬和德雷贝伊的分权倾向;
主张以祖国(Vatan)的认同取代传统的对米勒特(Millet,民族)的认同。
人与过分西化又几乎完全垄断着现代国家机器的官僚上层展开激烈争论。他们是奥斯曼帝国立宪主义的理论、代议制政府理论和国家语言改革理论的先驱。这种理论即来源于坦志马特时代的社会变迁,也来源于改革诏令的法律精神,后来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的重要思想源泉。
在前大维齐米德哈特帕夏的领导之下,青年奥斯曼人与文人官僚、军官联合起来,展开了立宪运动。1876年12月,在部分军队的支持之下,青年奥斯曼人争取到了帝国宪法的颁布和议会的建立。代议制度的实行也是现代化改革导致的社会变迁的结果。帝国设立议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不是由文化决定的,而是由帝国多样化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所需的政府职能的必要性决定的。
现代化冲击下的奥斯曼社会与传统的社会相比越来越多样化了。有势力的传统社会力量,诸如素丹本人、地方贵族、部落领袖和具有传统倾向的乌勒玛,仍然是奥斯曼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坦志马特时代发展起来的现代力量在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进步作用。而且诸如乌勒玛、官僚、军队等社会集团由于利益的不同发生了内部分化,有些倾向于现代化,有些则倾向于传统。
奥斯曼帝国19世纪的改革导致在衰弱的帝国中产生了强有力的素丹权力。国家机器的中央集权化和现代化为素丹的专制统治提供了必要手段。但专制主义未能阻止帝国的分裂。1878年7月的柏林会议允许奥斯曼帝国恢复对保加利亚的主权。但塞尔维亚、罗马尼亚、蒙底内哥罗却独立了。奥匈帝国占领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东北部的巴顿、卡尔斯、阿尔达汗被让给俄罗斯。为了遏制阿拉伯各省的分离倾向,哈米德将泛伊斯兰主义当成是国家统一的意识形态工具。坦志马特时期,国家上层中宗教人员的作用在日益淡化,而哈米德二世却把传统宗教权贵吸收进统治上层,身边围绕着乌勒玛与苏非教团的领袖。
作为传统的米勒特制度的结果,帝国经济存在着明显的宗教方面的分野。19世纪,从事传统农业的主要是穆斯林,而现代资本主义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则主要是非穆斯林。
因为封建骑兵并不包括非穆斯林,他们得不到由于军事义务才能获得的土地。非穆斯林的经济注意力只好转向贸易和金融方面。19世纪末,雇用工人超过十人以上的工业企业90%属于非穆斯林。
另一方面,米勒特制度提供的自治权,打开了基督教米勒特与欧洲国家进行贸易和联系的早期通道。在东方问题的冲击下,基督教社区加强了和西方的政治经济联系。这阻碍了改革家们政治上对少数民族的统一。
柏林会议处理完帝国的欧洲领土之后,欧洲列强又开始干涉奥斯曼帝国的心脏地区安那托利亚。在柏林会议上,英国政府对东安那托利亚的亚美尼亚的利益表示了直接的关注,1879年和1896年列强将两项改革计划强加给帝国。素丹哈米德二世要对付英国人的亚美尼亚自治计划,又得应付列强对帝国税收、司法和宪警的监督。奥斯曼帝国政府努力加强中央集权,而欧洲列强却在促进省一级政府的分离倾向。而且,英国的计划是在完全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区鼓励亚美尼亚人的自治。
欧洲的这种干涉与哈米德重新建立对东安那托利亚的控制的努力同时发生。在19世纪30和40年代成功地制服了大多数德雷贝伊和库尔德部落领袖之后,奥斯曼帝国政府已经能够相对控制安那托利亚东部省份。但是,俄土战争期间,安全形势完全恶化了。为了重新控制库尔德人,奥斯曼帝国政府利用了已经存在的库尔德人在农村的阿加与在城市的贵族之间的矛盾。政府努力利用各种各样的集团,以使它们不能对中央政权提出挑战。为了建立一种控制和监督机制,也是为了准备另一场与俄国的战争,1891年建立了哈米德骑兵团,由免服兵役和赋税的库尔德部落民组成。同时在欧洲的改革计划鼓励下建立起来的亚美尼亚武装开始了军事行动,挑起了穆斯林对亚美尼亚人的报复和怀疑心态。中央政府最终失去了对局势和哈米德骑兵的控制,这支自主行动的军队在不断升级的暴动中成为主要的力量,最终导致了1895年-1896年的亚美尼亚大屠杀。
另外,奥斯曼帝国试图加强国家控制时陷入了东方问题的困扰。哈米德对所有事务都进行严格控制的专制主义了失败了。长期以来由于不能够阻止外部力量的进攻,专制政体失去了其合法性,内部反对派的力量得到了加强。哈米德二世专制时期,推翻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各种社会力量和政治思想形成了。
当东方问题体系包含了帝国的安那托利亚心脏地带时,安那托利亚同时也成了新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心脏地带。坦志马特时代,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行政管理改革的影响之下,民众领土的认同发生了变化,以前人们典型地认同于“伊斯兰的家园”,而现在则越来越多地认同现代民族国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青年奥斯曼人是首次提出了政治上忠于祖国的思想。然而当70年代的立宪运动要在奥斯曼国家的旗帜下团结不同的米勒特时,祖国一词则更多的具有穆斯林和土耳其人的内涵,而安那托利亚则是他们的领土核心。在哈米德二世的统治之下,“奥斯曼人”的认同越来越多地具有“土耳其人”的特征,即使是这一认同以普遍性的伊斯兰词语进行了包装。与亚美尼亚和希腊的情况一样,土耳其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是在国内反对派与流亡欧洲的土耳其人的共同影响下发展的。
推翻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各种社会力量和政治思想在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进一步形成了。1895年进步与统一委员会建立之后,青年土耳其运动开始活跃起来,并能不断地得到军队的支持。1908年7月青年土耳其人在萨洛尼加发动起义,素丹被迫恢复宪法和议会。青年土耳其党人分为自由主义者和统一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官僚上层,支持君主立宪制;统一主义者主要是居于社会中下层的政府公务员、军官和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以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为中心,主张进行更为激进和集中的改革。
通过对宪法的修改,素丹从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变成了名义首脑。1913年,统一主义者恩威尔、塔拉特、杰马尔等三巨头建立了独裁统治,提出了激进的社会改革纲领,其中包括法律的世俗化、妇女地位的提高、组织选举、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
尽管奥斯曼帝国存在到了1923年,但青年土耳其革命却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秩序的结束。改革进程的社会和政治动力最终摧毁了素丹制的基础,结束了奥斯曼帝国五百多年的统治。新军和现代官僚机构的建立本来是为维护帝国的统治的,但来自新式军队和现代官僚机构中的社会力量最终转而反对帝国的素丹制。如果考虑到帝国改革的最初动机,《色弗尔条约》的签订则是百年改革完全失败的标志。
四、小结
奥斯曼帝国现代化进程包含两个层面:首先是总的现代化进程引起的奥斯曼传统社会结构的转变;其次是国家的改革精英们的有目的的改革行为。18世纪和19世纪,这些主动和被动层面上的社会转型引起了奥斯曼社会的巨大变化。对欧洲国家竞争体系的卷入、与正在兴起的世界市场的一体化、世界文化意义上的政治与科学思想的传播,都破坏了奥斯曼得以存在几个世纪的社会基础。朝廷和上层官僚进行了旨在按现代欧洲模式重新组织对武装力量控制的改革。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几乎是在一种强制性的轨道上运行。哈米德二世的专制主义统治表明,强制性的现代化道路加剧了传统统治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奥斯曼帝国的权威主义现代化最终破坏了它保卫传统秩序的初始目的。
由于军事安全的需要而引发的对军队和官僚机构等现代国家机器的现代化不仅是奥斯曼和土耳其现代化的聚焦点,也是其动力。奥斯曼现代国家制度并不是通过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而形成的,而是通过统治上层的强制实现的。国家制度的严格等级划分、国家机器与统治精英被看作是同一种东西,都反映了奥斯曼改革及这种改革的强制性轨道的权威特征。由安全的需要而推动的土耳其的现代化有两个明显不同的面孔。一方面,它是一种面对外部压迫的战略调整,另一方面,对内则是一种统治上层强加的社会政治工程。
尽管作为一种传统的世袭制国家的奥斯曼帝国消失了,但它却为土耳其共和国的产生创造了思想、文化、民族意识、政治力量等方面的条件。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结构、政治文化以及与巴尔干国家的冲突结构在土耳其共和国时期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