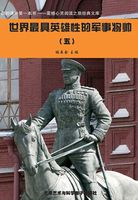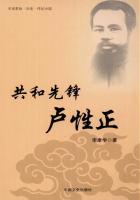现代舞蹈的先驱者(美国1877~1927)
天生的舞蹈家
1877年,邓肯出生在旧金山一个贫困而破碎的家庭里,出生前,父母正闹着离婚。父亲远走他乡,母亲为生活疲于奔命,备尝艰辛。
母亲是个音乐家,靠当家庭音乐教师谋生。因而经常整天不在家,晚上很晚才回来。邓肯的兄弟姊妹过着贫穷但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散学后就可以漫步海滨,纵情幻想。
邓肯的母亲出身于爱尔兰天主教家庭,一直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后来她发现丈夫并不是她理想的那样完美无缺,就离了婚。从此带着4个孩子独自闯荡。她彻底背叛了天主教信仰,转而相信无神论,她把无神论思想传给了她的女儿邓肯。
邓肯5岁开始上学。
开学的第一天,老师布置她的学生们写一篇作文,介绍各自的家庭,写完就念给她听。当她听到一个又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情况以后,下面站起来的是她这个班上最小、最穷的学生,依莎多拉·邓肯。只见她念道:
我5岁的时候,我们家住在23号街上一所小房子里。由于付不起房租,就不能再住下去,只好搬到17号街。不久,由于缺钱,房东不让我们住下去,又搬到22号街。在那里也不允许我们安然住下去,于是又搬到10号街……
没完没了的搬家把老师惹恼了,她拍案而起,骂邓肯是捣蛋鬼,故意用恶作剧耍弄老师。
这可是担待不起的罪名。邓肯被送到了校长面前。校长冷冰冰地说道:“叫她母亲来领人。”
邓肯的母亲来了。可怜的母亲读了女儿写的作文,泪水夺眶而出。她发誓说,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真话,我们的流浪生活就是这样。
贫困和屈辱,已使得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成了一名彻底的无神论者。她的宗教情感,慢慢地转化成另一种能量,与命运抗争,教子女成人。
从公立学校出来,邓肯反而受到了真正的教育。每天晚上,母亲给她的四个子女弹贝多芬、舒曼、莫扎特、肖邦的曲子,或者朗诵莎士比亚、雪莱、拜伦、济慈的作品。白天,邓肯一个人悄悄地去库尔勃利丝的图书馆,贪婪地攻读荷马、狄更斯、萨克雷的全部著作。
最让她不忍释卷的是惠特曼的诗,那充满激情的句子深深地打动了她,她一不小心就忘乎所以地在座位上念出声来:
我轻松愉快地走上大路,
我健康,我自由,整个世界展开在我面前,
漫长的黄土道路可引我到想去的地方。
从此我不再希求幸福,我自己便是幸福,
从此我不再啜泣,不再踟蹰,也不要求什么,
消除了家中的嗔怨,放下书本,停止苛酷的非难。
我强壮而满足地走在大路上。
地球,有它就够了
我不要求星星们更和我接近,
我知道它们所在的地位很适宜
我知道它们能够满足属于它们的一切
……
邓肯试着写了一部小说,还自己编了一份报纸,新闻、社论及文学作品,均出自于她一人之手。这些东西,她只给库尔勃利丝看过。她从那里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夸奖:
“孩子,你会比我和你爸爸都了不起。”
海滩是依莎多拉·邓肯常去的地方。她凝望着起伏的海浪,或迂回,或直捷,或急厉,或舒缓,偶尔有长尾巴鱼腾挪窜跃,使神秘的潮汐洋溢了生命的气息。从这里,邓肯悟到了关于运动、舞蹈的最初的观念。
依莎多拉·邓肯的舞蹈天分最先被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太太发现。
她对邓肯的母亲说,邓肯的舞姿让她想起了意大利著名的芭蕾舞演员范妮·艾斯勒。这句话增添了邓肯的信心,也鼓舞了邓肯的母亲。第二天,她便把女儿送到旧金山最负盛名的芭蕾舞教师那里。那位教师端详了邓肯半天,认为她姿质不错,可以一试。
于是开始试了。
他让邓肯用脚尖着地,走一段路给他看看。
邓肯奇怪地问道:
“这是为什么?”
“这样才美。”
“不,这很丑,我做不来。这不是自然的。”
邓肯扭头就走了。母亲紧跟在后,攀住她的肩膀说:
“孩子,我同意你的观点。”
邓肯没有去做学生,而是继续当她的“老师”。她有些名声了,孩子们都愿意上她的课。她从不斥责学生,她尊重每一个学生的想法,并鼓励他们异想天开。她教孩子们背诵朗费罗、拜伦的诗,先让他们领会其中的含义,然后根据诗意轮流做出动作,以此评估每一个学生对诗歌和舞蹈的理解能力。
很显然,邓肯追求的不是芭蕾舞蹈。她虽然说不清她的追求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但她在探索着,努力探索着。她深知,她的艺术潜伏在她心中,一旦找到钥匙,她就能进入这个世界。
由于邓肯有舞蹈天赋,加上母亲对她的教育和影响,6岁时她的舞蹈天才就显露出来了。有一天,她召集了六七个街坊上的孩子(有的小孩甚至还不会走路),让他们坐在她身边。邓肯则教他们挥动手臂。原来她在给他们当“老师”教小朋友们跳舞。
由于邓肯全家经济拮据,加之所读书籍的影响,全家人决定离开旧金山到国外去寻求发展。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闯荡英法
邓肯千方百计想离开旧金山到外面去发展——随同某个大剧团外出演出。
于是,有一天,她毛遂自荐,去拜访一家巡回剧团的经理,请求允许她表演舞蹈。一个上午,在一个又大又黑、空荡荡的舞台上试演。母亲为邓肯伴奏,邓肯穿一件小“图尼克”跳了一段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的《无词歌》。跳完以后,经理沉默了一下,然后转身对邓肯的母亲说:“这种玩意儿不适合在剧场演出,它更适合于教堂。您还是把小姑娘领回家去吧。”
第一次初试,邓肯大失所望,但她并不甘心。又开始想别的主意出国。她发动全家人来商量,她一人侃侃而谈一个多小时,向家里人讲清楚为什么在旧金山再也不能待下去的种种理由。母亲有点困惑不解,但很乐意跟邓肯到任何地方去。
最后决定:邓肯和母亲先去芝加哥,姐姐和两个哥哥仍留在旧金山,等挣些钱后再来接他们。
到达芝加哥,正是酷暑六月天,邓肯随身只带了一只小提箱,里面有祖母的一些老式首饰,外加25美元。她盼望能立刻得到聘用,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她穿着希腊式的白色小“图尼克”拜访了一位又一位经理,给他们表演舞蹈。但他们都像最初的那位一样,“好倒是很好,只恐怕不适合舞台演出”。
过了几星期,25美元花光了,祖母的首饰也典押了。由于付不出房租,行李全被旅馆扣留。两个人身无分文,只得流浪街头。
邓肯想起自己外衣衣领上有一个小小的但非常漂亮的爱尔兰上等真丝花边,在炎炎烈日下,她东奔西走,转了一整天想卖掉它,总算在傍晚时候有人出10美元买下了它。邓肯用10美元租了一间房子,剩下的钱买一箱西红柿。以后接连一个星期,母女俩就靠这些西红柿度日。由于吃不上面包和盐,可怜的母亲身体衰弱,连坐都坐不起来了。而邓肯呢,每天一大早就出门,想尽办法去见经理。最后,邓肯只好决定,只要有工作,干什么都行。于是,她便去找一家职业介绍所。
“你会干什么?”柜上的那个女人冷冰冰地问道。
“什么都会。”邓肯回答。
“哼,依我看,你什么也不会!”
绝望之中,有一天,邓肯去找共济会教堂屋顶花园的经理。他嘴里叼着一根很粗的雪茄,帽子压住一只眼睛,傲慢地看完了邓肯表演的舞蹈后,说:“嗯,你长得不错,风度也挺优美。如果你肯改变一下,不跳这些,跳点有刺激性的玩意,那么我可以雇佣你。”
想到家里最后剩下的一点点西红柿,想起饿得发晕的妈妈,邓肯豁出去了,便问经理:“你说的‘刺激性’是什么?”
“嗯,”他说,“不是你跳的这些,得穿短裙,加点花边,还得甩大腿。你可以先跳点希腊舞蹈,然后再转动花边裙子,甩开大腿,那就引人注目了。”
可是上哪儿去找这些花边裙子呢?邓肯知道,开口借支或预支是没有好处的。邓肯徘徊在大街上,又饿又累,差点晕倒,忽然看见马歇尔·菲尔德百货公司的一家分店就在跟前,就走进店去求见经理。当邓肯被引进办公室,见一位年轻人坐在写字台后面,看上去很和气,于是邓肯向他解释,明天上午需要有一件带花边的裙子,如果能赊给她,她一定领到工资后就付款。年轻人答应了她的请求。邓肯买了做裙子的白色和红色的料子,还有荷叶花边,夹着一大包衣料回家一看,母亲已经气息奄奄了。但她勇敢地从床上坐起来,为邓肯赶制服装。干了整整一夜,直到黎明才缝完最后一个褶子。
邓肯带着这套服装再去拜访经理,乐队已经做好了试演的准备。
“你用什么音乐?”他问。
由于事先没考虑到,邓肯随口说出了当时的一首流行歌曲《华盛顿邮车》。音乐奏了起来,邓肯尽最大努力给经理跳了一段“刺激性”的舞蹈,边跳边编。经理高兴极了,从嘴里取出雪茄,鼓掌说道:
“跳得不赖。你明天晚上就可以上台,我要替你宣布一个特别节目。”
经理给邓肯周薪50元,并且慷慨地预付了一个星期。
邓肯用一个艺名在这家屋顶花园登台表演,获得很大成功,观众掌声不断。但她心里腻味透了。她认为这是违背自己的理想,取悦于观众的事,一生中只能干一次,对,干最后一次。经理后来要求与邓肯签订巡回演出的合同,邓肯坚决拒绝了。
她偶然结识了芝加哥某报社的女助理编辑安勃,这位年过半百的妇人,以充沛的精力组织着一个“波希米亚人俱乐部”。波希米亚原系捷克斯洛伐克波希米亚地区的一个民族,因其热情奔放、浪荡不羁而成为诗人艺术家部落的代名词。
邓肯很快就成了这个俱乐部最受欢迎的客人。那些艺术狂徒们歇斯底里的叫嚣和莫名其妙的举止虽然令人不敢恭维,但他们对舞蹈的理解却使邓肯感到宾至如归。邓肯美妙的形体、流畅的线条以及符合内心律动的节奏,牵扯出“波希米亚人”被劣质啤酒淹没的宗教情绪,他们亲切地称邓肯为“希腊小姑娘”。如果说安勃以其经济上强大的支持而成为这个俱乐部的天神宙斯,那么,依莎多拉·邓肯则以她优美绝伦的舞蹈标榜了自己爱与美的神位——维纳斯。
在困难之中也会出现奇迹,邓肯发出的求助电报有人给她寄钱,她和哥姐前往纽约,邓肯从一开始就认为哑剧是一种贫瘠无聊的东西,根本谈不上艺术。为了生活,她强迫自己去排练那生硬呆板的一招一式,而内心无时无刻不在抵触着它,这当然是不能进入状态的。
排练中,邓肯遭到了大主角梅的一个耳光,这对邓肯来说,太刺激了!贫困与饥饿,羞辱和痛苦,像一块巨大的针毡,裹紧了这个尚未成年的姑娘。血,一滴滴地从心头渗出,模糊了过去的辛劳和未来的期待。依莎多拉·邓肯忍不住大放悲声,簌簌滚落的泪珠织成了一张苦涩的帘子。
在纽约演出二星期后,接着就是巡回演出,邓肯又恢复了那种沉闷的旅行和寻找客栈的生活。
一年就这样过去了。
邓肯非常难过,现在生活令她不堪回首。她的美梦、理想、抱负,全都化成了泡影。她常常捧着古罗马诗人马库斯·奥列留斯的书,在布景后面走来走去,她试着采取斯多噶学派的哲学来减轻自己心中的痛苦。
戴利为了票房收入,挖空心思把艺妓搬上舞台,她要邓肯也加入艺妓的四重唱。邓肯看出剧团接二连三干的蠢事,她再也不能忍受了。她对剧团和戴利感到厌恶,鼓足勇气申请了辞职。
姐姐伊丽莎白的舞蹈学校却越办越兴旺。邓肯全家搬进温莎旅馆底层的两个大房间,每星期的租金是90美元。但不久就发觉学生所交的学费还不够支付房租和其它费用。表面上看来很成功,其实银行帐户上却出现了赤字。
怎么办?邓肯全家非常着急,又毫无办法。
一天下午,温莎旅馆突然失火,邓肯全家和学生们逃出旅馆后,才发现自己丧失了全部家当,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有。全家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回想在纽约的种种不幸和遭遇,邓肯陷入了辛酸的幻灭之中。
邓肯想到了去伦敦的计划,全家人都赞成去伦敦。没有一分钱,怎么去?她不得不去找曾经在她们大厅里跳过舞的有钱太太们,她一家一家地去乞讨,受尽了冷遇和教训,最后总算凑足了300美元,弟弟雷蒙德在各个码头附近兜圈子,终于找到了一艘运牲口到赫尔的小船。船长被雷蒙德的诉说所感动,答应把他们当作旅客带去,虽然这样做是违反船上规章制度的。
他们终于一路辛苦的到达了伦敦。
在伦敦邓肯赢得了上流社会的尊重,爱德华国王和威尔斯亲王都接见了她,并对她赞不绝口。她取得了曾经看来是梦幻般的成功。
除了跳舞,邓肯的业余时间就被他人占据着,要么听诗人朗诵诗歌,要么偕画家出去散步。他们都是真正的朋友。邓肯在他们中间感到非常快乐,可心里却不十分惬意,因为,她的舞蹈虽然获得了诗人、画家们的狂热赞赏,但所有的剧场经理都无动于衷,这就使得她的艺术无法面对大众。
她要去寻找更加适合于她的舞蹈艺术的土壤。
她想到了“欧洲之都”——巴黎。
邓肯在巴黎的首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和赞誉,她的信心更足了。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她很快便能相当流利地阅读法文和讲法语。博尼埃常常一连几个下午和黄昏在工作室里为邓肯高声朗读,声调抑扬顿挫,十分悦耳。他把莫里哀、福楼拜、狄奥菲·高地叶和莫泊桑的作品读给邓肯听,让邓肯了解当时流行的各种法国现代名著。博尼埃还向邓肯介绍塞纳河上的风光,介绍巴黎圣母院建筑物正面上的每个塑像以及每一块石头的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