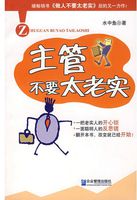随后,我们重新回到了数据收集中,对没有落入这四种我们期望看到的文化中的那些文化进行处理(第一个是安进公司)。在这点上戴夫和约翰进行了持续数年的争论。约翰认为,有可能会有一种商业文化,这种文化中没有值得关注的对手,它已经超越了专注于“击败”另一家公司的那种文化。而戴夫作为一个管理学教授,他不能认同这种观点。戴夫认为,如果一种文化忽略了它的对手,那么它终将走向失败。
最终说服戴夫同意约翰看法的是沃伦·本尼斯和巴蒂西亚·沃德·彼得曼在《组织天才》[ 《组织天才:创造性合作的秘密》,沃伦·本尼斯和巴蒂西亚·沃德·彼得曼著,纽约Perseus出版社,1997年出版。]中的相似发现。这本书中提到的跨时代的伟大群体就是我们认为拥有第四阶段后期或第五阶段早期文化的那些群体。
数据结果也支持约翰的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文化呈现出被我们称为第五阶段的特征——它们拥有“单纯的好奇心”,它们的表现都开创了历史先河。
在我们回顾录音和笔录时,我们发现第五阶段的“术语视界”清晰可见。人们在那个阶段使用的词汇往往是“天哪”“奇迹”“幸运”“愿景”“价值观”以及“我们”。尽管我们没有正式地去评估语气,但是我们的观察发现,第五阶段组织中的人往往说话声音更轻和更虔诚,而第四阶段的人往往更热闹。
回顾那些采访,其中大多是转录,四种文化的细节都与我们的调查吻合。但几乎在同时,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在21世纪初,我们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没有可辨别业务专长的第五阶段文化。很多这类公司并不赚钱,但却获得了大量的投资。更让人不解的是,很多这样的公司上市,并且估值远远超过了那些世界级的公司。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网络泡沫的破灭给出了答案:从长远来看,公司文化与战略表现密切相关,会因为一些重要因素而下降到较低的阶段。因此,每个拥有伟大文化和低性能战略表现的公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发现它们的文化在不断下坠:优秀的人才流失,“我的生活糟透了”的语言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随着五种文化的发现,我们开始寻找一种能总结它们的简单的方法。虽然这个过程是非正式的,但事后总结时我们发现自己还是遵循着专注群体的相同的系统流程:我们走进一种文化,用我们的语言总结它,然后记录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注意到,“生活糟透了”“我的生活糟透了”“我很牛”“我们很牛”以及“生命是伟大的”这些标签可以适用。我们已经使用它们8年了。在搜集到一种文化的数据后,我们就会与身在其中的人分享它们以及它们的名字,只有两个组织中的人们认为这些名字不适用。这两个组织都具有特殊的问题(一家组织中的一位领袖身患绝症,另一家组织的所有者关闭了一个成功的子公司)。
下一个主要的突破是在结构上。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研究非正式关系网络,其中大部分来自二手资料。随后,我们开始让一些人描绘他周围的关系网结构,同时他们也将这些有关联的人的文化阶段进行评级。我们注意到,结构与文化阶段的相关程度非常惊人——超过90%。虽然关系结构已经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被广泛研究,这个领域往往被分为人际沟通领域和群体沟通领域。但第10章中所描述的三边关系似乎处于这两个领域之间,因此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用几个星期来查看那些提及“三人组合”“三位一体”或者“三人”等沟通方面的研究,在阅读完上百篇文章之后,我们发现没有一篇涉及第10章中所提到的观点:一个人需要对另外两人之间的关系(依据价值观)质量负责。然而,一旦这种见解被确定之后,它就变得非常明显,所以我们肯定有人在某些地方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虽然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没有找到他们的研究。
在2001年我们发现,可以依据人们使用的语言来将一种文化迅速地挂靠到第一到第五文化阶段上去(通常是在几分钟内)。我们的初步判断与调查结果相关程度达到90%以上。在此基础上,我们放弃了调查,开始使用专家评审方式。我们对一些南加州大学里戴夫带的研究生进行了早期的可靠性评估研究,了解到机构内部的人与外部观察者在判断他们同事的文化阶段时几乎一样地准确(相关性指数超过0.9)。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人们对于自身的文化阶段判断并不准确。我们观察到的动态是,处于第三阶段的人往往会说自己在第五阶段;第二阶段的人往往说他们在第四阶段。虽然他们的自我评价(基于自身的行为)都高估了两个阶段,但人们都非常善于评价他们周围的文化。换句话说,人们能够准确地说出他们在第三阶段文化氛围中工作,但他们经常将自己形容为第五阶段领袖。
随后,我们训练整个团队,让他们去评价那些与他们一起工作的人(以匿名的方式,他们的回答被保密)。我们有五组独立的数据库,每一个都反映了不同的测量系统,我们调查的人员比例也是从这些来源中获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据并不代表随机抽样,我们的基数人口向受过高等教育的、富裕的和城市里的人口倾斜。此外,随着工作的扩展,我们开始让人们——少于24,200人——评价自己,他们目前的工作团队以及他们机构内部的“重心”。既然已经确认了人们能够准确地“指出”他们工作环境的文化,我们非常自信这种数据收集方式是实用的。(我们使用受访人对他人的评级作为指导,并从我们的研究中去除了他们的自我评价。)[ 为了]确认这种趋势,我们还搜寻了其他阶段发展理论学家的观点。唐·贝克,《螺旋动力学》的作者,他也注意到了同样的效果,他称为“理想的错误”。他是这样向我们解释这种现象的:“我们向往它(一个阶段),因此,我们就认为自己在它那里(那个阶段)。”
在我们的工作接近尾声时,我们的数据库里有超过24,000的人的数据。请注意,本研究变成了一个涉及由部落组成的部落,同时也包括那些接受过培训的人回馈给我们的数据。虽然不能保证他们的观察质量,但我们认为,1997年以来在20多家组织中收集的超过70,000人的数据结果是可信的。
进一步深入
我们的最后一步是“深入”研究某一个客户(这是自1997年第一次研究以来多年后的事情),从这些客户身上我们能够更容易地测量结果。从2001年开始,我们选择了世邦魏理仕——全球最大的商业地产服务公司,因为其团队的有效性可以依据收入进行衡量。我们同时采取了两种方法。第一,我们与“制作团队”合作,使用了本书中的技术,这些团队中大多数都被管理层视为有问题的。根据我们最后一次的测量结果(2005年3月),在全国75个主要团队中,我们参与过的这些团队中有6个登上了前十五的排行榜。(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们的客户,大多数人在与我们一起工作前就已经表现得很优秀了)第二,我们与私人客户集团合作,它是这家公司一个新成立的部门,它在36个月内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收入(从0 开始)。
其他结论
有趣的是,在我们参与咨询过的或者收集过数据的公司里,人们往往开始在他们的关系中运用部落领导力:在他们的婚姻中、家庭关系中、邻里关系中,等等。这个系统也适用于非商业关系,不过重要的是这种使用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研究范围。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更广泛的关系拓展方式应该算是民间智慧。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过将本书中技巧应用到一般关系中产生的任何矛盾。
对于某些学界同人来说,我们的研究方法可能看起来不太精确。然而,应该指出,文化阶段是每个人自己的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有德国到密苏里州那么远。所以很容易区别出一个人所处的阶段。即使只经过很少的培训,人的判断可靠性也能达到85%。
写在最后
我们的最终结论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本书由一个部落写成。虽然这些文字是我们写的,但这些观念来自我们周围的所有人——我们的客户、研究对象、研究生、世界级学生、CEO、工会领袖、政府官员、朋友和家人。我们的角色非常简单:提问,通过与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讨论找出答案,然后问更多的问题。我们同样需要感谢我们的部落。我们希望你在阅读本书之后,能与我们联系,分享你的经历和故事,从而建立我们所有人的部落。
附录C
如何与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