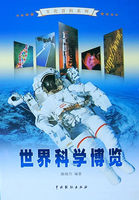他注册了儿子的名字
◎文/张翔
父亲的爱就如同阳光照亮海岸一般照亮孩子的眼睛。
认识蒂文和他的儿子是在沙加缅度,那时,我在加州留学,有空的时候,我常去36街拜访我定居加州的姐姐。蒂文和他的儿子是姐姐的邻居。我是在一次午饭过后看到蒂文和他的儿子的,那时他正在房前的空地上教儿子学自行车。
我一眼便看到了他的儿子,眼神从惊讶滑落到怜悯。因为他的儿子是一个残疾人,孩子的头是扭曲的,向后弯着,几乎贴在了左肩上,脸部的肌肉紧绷着,显得有些吃力。
我问身旁的姐姐关于他们的情况,姐姐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天生的,没什么,他父亲对他很好。”我分不清这话是淡漠还是赞赏,或者是一种麻木。只是觉得姐姐的回答是如此“习以为常”的轻松,是我所感到意外的,因为姐姐向来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人。我想一个再好的父亲大概也抵挡不了这与生俱来的创伤吧。
我用一种怜悯而忧郁的目光注视着这个年幼的背影,只是在孩子一个转身的片刻,我的目光遭遇了他的眼神。他看着我,眼睛中是那种饱含童真的晶莹剔透的蓝,宛如夏威夷阳光下的一弯海水。他还调皮地冲我眨了一下眼睛,如波光闪动。那是一种健康而幸福的眼神,这是我意料之外的,因为我在国内所见过的残疾人,眼睛总不可避免地隐含着伤痛、自卑,甚至嫉恨。
我走过去,认识了这父子俩。蒂文请我去他家做客,我答应了。
在第二个休假日,我捧着一束鲜花去拜访了他们。小蒂文已经学会了骑自行车,轻松而自然,乐此不疲。他刚把我迎进家门,就跑出去骑车了。
我走进大门的时候,吃惊地看到他们客厅的墙上居然挂着一幅大照片,这个人不是什么总统正要,也不是那些歌星影星,居然是写《时间简史》的史蒂芬·威廉姆·霍金——和小蒂文一样有残疾症状的英国科学家。
蒂文看出了我的惊诧,于是解释说:“小蒂文以前总是很自卑和困惑于自己的长相,同学们也常常取笑他,有时,他连学校都不想去了,成绩糟透了。于是我找来了霍金的照片。我告诉他,他长得像霍金,只要努力学习,以后也能像霍金一样成为科学家……后来,他学习很努力,成绩棒极了,同学们都很崇拜他,喜欢他,也就不再嘲笑他了……”
讲到这里,蒂文拉着我到了小蒂文的房间,一进房门,我看到了正对门的那面墙上,居然挂满了装裱好的商业标识证书。
“这是什么?”我搞不明白了。
“你仔细看!”
我走近一看,上面居然是用“福勒·蒂文”的名字注册的商业标识,各种行业的,居然有十八种之多。
“我注册了小蒂文的名字,我相信他会成名的,当然最重要的是让他自己也相信。每当他感觉到困难或痛苦的时候,我们就鼓励他,说困难是必须的经历,我们都坚信他以后能成功,能成为名人,会有很多人要抢着注册他的名字,在各种商品上……然后他就会慢慢地振作起来,继续努力,他每天都能看到这些标识,每天都充满着对生活的信心……”
我几乎惊讶得合不上嘴,居然有这样的一个父亲,将自己的未成人的儿子的名字早早地注册了。而他只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来鼓励自己的孩子去勇敢面对挫折,充满信心地面对生活。
我终于明白,姐姐为什么如此轻松地回答我的问题了,也终于明白小蒂文的眼神为什么会如此的晶莹剔透而没有丝毫阴影了。因为他拥有着一个深爱他的父亲,而父亲的爱就如同阳光照亮海岸一般照亮孩子的眼睛。
小蒂文回来了,一头扑到了蒂文的怀里,两父子拥吻着,幸福地对视着。从小蒂文湛蓝的眼睛中,我能够看出,父亲已经将爱注册在了他的心里,一生一世。
父亲的音乐
◎文/韦恩·卡林
抚慰你所爱的人的心灵,是最珍贵的礼物。
我还记得那天父亲费劲地拖着那架沉重的手风琴来到屋前的样子。他把我和母亲叫到起居室,把那个宝箱似的盒子打开。“喏,它在这儿了,”他说,“一旦你学会了,它将陪你一辈子。”
我勉强地笑了一下,丝毫没有父亲那么好的兴致。我一直想要的是一把吉他,或是一架钢琴。当时是1960年,我整天粘在收音机旁听摇滚乐。在我狂热的头脑中,手风琴根本没有位置。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手风琴被锁在走廊的柜橱里,一天晚上,父亲宣布:一个星期后我将开始上课了。我难以置信地看着母亲,希望得到帮助,但她那坚定的下巴使我明白这次是没指望了。
买手风琴花了300块,手风琴课一节5块,这不像是父亲的性格。他总是很实际,他认为,衣服、燃料、甚至食物都是宝贵的。
我在柜橱里翻出一个吉他大小的盒子,打开来,我看到了一把红得耀眼的小提琴。“是你父亲的。”妈妈说,“他的父母给他买的。我想是农场的活儿太忙了,他从未学着拉过。”紧接着,我在蔡利先生的手风琴学校开始上课。第一天,手风琴的带子勒着我的肩膀,我觉得自己处处笨手笨脚。“他学得怎么样?”下课后父亲问道。“这是第一次课,他挺不错。”蔡利先生说。父亲显得热切而充满希望。
我被吩咐每天练琴半小时,而每天我都试图溜开。我的未来应该是在外面广阔的天地里踢球,而不是在屋里学这些很快就忘的曲子。但我的父母毫不放松地把我捉回来练琴。
逐渐地,连我自己也惊讶,我能够将音符连在一起拉出一些简单的曲子了。父亲常在晚饭后要求我拉上一两段,他坐在安乐椅里,我则试着拉《西班牙女郎》和《啤酒桶波尔卡》。
秋季的音乐会迫近了。我将在本地戏院的舞台上独奏。
“我不想独奏。”我说。
“你一定要。”父亲答道。
“为什么?”我嚷起来,“就因为你小时候没拉过小提琴?为什么我就得拉这蠢玩意儿,而你从未拉过你的?”父亲刹住了车,指着我:“因为你能带给人们欢乐,你能触碰他们的心灵。这样的礼物我不会任由你放弃。”他又温和地补充道,“有一天你将会有我从未有过的机会:你将能为你的家庭奏出动听的曲子,你会明白你现在刻苦努力的意义。”
我哑口无言。我很少听到父亲这样动感情地谈论事情。从那时起,我练琴再不需要父母催促。
音乐会那晚,母亲戴上闪闪发光的耳环,前所未有地精心化了妆。父亲提早下班,穿上了西服并打上了领带,还用发油将头发梳得光滑平整。
在剧院里,当我意识到我是如此希望父母为我自豪时,我紧张极了。轮到我了。我走向那只孤零零的椅子,奏起《今夜你是否寂寞》。我演奏得完美无缺。掌声响彻全场,直到平息后还有几双手在拍着。我头昏脑涨地走下台,庆幸这场酷刑终于结束了。时间流逝,手风琴在我的生活中渐渐隐去了。在家庭聚会时父亲会要我拉上一曲,但琴课是停止了。我上大学时,手风琴被放到柜橱后面,挨着父亲的小提琴。
它就静静地待在那里,宛如一个积满灰尘的记忆。直到几年后的一个下午,被我的两个孩子偶然发现了。
当我打开琴盒,他们大笑着,喊着:“拉一个吧,拉一个吧!”很勉强地,我背起手风琴,拉了几首简单的曲子。我惊奇于我的技巧并未生疏。很快地,孩子们围成圈,格格地笑着跳起了舞。甚至我的妻子泰瑞也大笑着拍手应和着节拍。他们无拘无束的快乐令我惊讶。
父亲的话重又在我耳边响起:“有一天你会有我从未有过的机会,那时你会明白。”
父亲一直是对的,抚慰你所爱的人的心灵,是最珍贵的礼物。
超越极限
◎文/易容
能让我们超越极限的力量,不是名利,不是财富,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不是,而是在血管里涌动,一次次漫过心底的爱。
电视台正在播放一档新节目,名为《超越极限》。参赛者被选中后,须在规定时间内吃掉一盘让人毛骨悚然的食物——活的蚯蚓、蜘蛛……场面刺激,直接挑战人的嘴、胃和心理承受能力。
那期节目从头到尾,尝试者不乏其人,但几番努力,终于还是败下阵来,到最后竟无一人过关。
妻说:“换了我,我也无论如何吃不下去,真恶心呢。”在女人中,妻算勇敢的了,一次在车上遭遇小偷,人人明哲保身,视而不见,唯妻挺身而出,把包甩过去,将小偷的刀打落在地。
“那要是给你很多钱呢?”我故意问,“比如说两万,你敢不敢吃下去?”
妻毫不犹豫地摇头。
“两万太少,要是两千万呢?一辈子锦衣玉食,你吃不吃?”我接着寻找可能的条件。
妻想了一会儿,仍摇头:“确实诱人。但要真吃下那盘东西,我想我下半辈子再也吃不下任何东西了。生无乐趣,要那么些钱有什么用?”
我笑:“如果发生灾难,不幸被压在石堆下等待救援,无食无水,只有这些东西可以维生,我想那时候任何人都吃得下去了。”
妻说:“也许那时我会吃吧,饿得晕头转向,求生的本能会战胜一切恐惧和恶心。”
“所以说想要超越极限,必须将人置于死地,否则人的潜能就不会发挥到极致。”我得意地作总结。
妻沉思着。
良久。她开口,一字一顿:“有一种条件,我一定会将它整盘吃下去,毫不勉强,心甘情愿。”
我问:“什么?”
妻说:“如果能让父亲回来。”
妻的父亲去年因肝癌去世,妻在病榻前陪伴数月,用尽所有办法,却始终于无力回天,眼睁睁看着老人怀着对人世无比的留恋而离去。那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遂成妻心口永远的痛,时至今日,每每午夜梦回,泪湿枕巾,常说又见到父亲笑容依旧,宛如生时。
“如果能让父亲回来,那算得了什么呢?”妻的眼圈红了,面容却透着坚定。
我听着妻的话,一颗心不由得被深深震撼了。
原来,许多时候,能让我们超越极限的力量,不是名利,不是财富,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不是,而是在血管里涌动,一次次漫过心底的爱啊。
大爱而弃
◎文/张翔
许多的时候,小爱为惜,而真正博大的爱却是一种忍痛的抛弃。
很多时候,常常想起朋友跟我讲的一个故事,关于母爱,关于抛弃。
故事是说曾经有一个聋哑的孤母,生了一个孩子。生下这个孩子之后,这个残疾的母亲毅然决定抛弃这个孩子,将其送给了一个没有子女的人家。
因为唯有这样,才可能给孩子一个完整健康的家庭,才不会让孩子失去语言的能力。
每每想起,总让我泪涟于这种爱意的痛弃。
但是后来我却遇到了另一件真实的故事。那是我老家的旧邻,同样是一对母子。孩子的父亲在一次车祸中去世了,母亲一个人带着男孩。还好,母亲在一个效益好的单位里当经理,生活还算宽裕。母亲对孩子自小失去父亲很愧疚,所以自小就加倍宠惯孩子。就是这个蜜罐里泡大的男孩,直到二十多岁,居然还不知道如何照顾自己,还常常惹出许多是非,让母亲疲于打理,就在这一年,母亲出事了。医院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上面赫然写着“癌症晚期”,她已没有太多的时间流连于世了。母亲走出医院的大门,就将化验单撕了个粉碎,抛撒路边。
那天,男孩又很晚才回家,母亲突然意外地大发脾气,说你太让我失望了。男孩感到很诧异,自己平常不就是这样吗?但是,紧跟着的却是母亲琐碎的唠叨。后来,男孩很生气地和母亲顶起嘴来,最后,母亲拿出五千块钱递给儿子,决绝地将他逐出了家门,说:“你去吧,有本事就自己养活自己去。”男孩从来没有受到过这种打击,因此愤然而去,自己闯荡去了。
半年之后,男孩经历了很多的磨难,终于自立起来,成了个坚强的男儿。而此时的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以前是多么不懂事呀,让母亲如此辛劳操心。于是决定回家去给母亲道歉,希望母亲能回心转意,接纳自己。当回到家的时候,出来迎接他的不再是曾经慈爱的母亲了,而是我们这些邻居和亲戚。他的母亲早已经在三个月之前辞世而去,留给他的只是一份家产和一封情切的遗嘱。
遗嘱中,母亲告诉他之所以抛弃他的原因,只是为了让他能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在自己死去之后,能好好生活下去。
他幡然悔悟,在母亲的墓前,泪洒了一地。
而站在他身后的人们也泪流不息,他们大概也都如我,明白了一种爱的深意:许多的时候,小爱为惜,而真正博大的爱却是一种忍痛的抛弃。
吊在井桶里的苹果
◎文/丁立梅
爱和被爱是从两面感受太阳的温暖。
有一句话讲,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说的是做女儿的,特别亲父亲。而做父亲的,特别疼女儿。那讲的应该是女儿家小时候的事。
我小时,也亲父亲。不但亲,还崇拜,把父亲当成举世无双的英雄一样崇拜。那个时候的口头禅是,我爸怎样怎样。仿佛拥有了那个爸,一下子就很了不得似的。
母亲还曾“嫉妒”过我对父亲的那种亲。一日,下雨,一家人坐着,父亲在修整二胡,母亲在纳鞋底,就闲聊到我长大后的事。母亲问,长大了有钱了买好东西给谁吃?我几乎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给爸吃。母亲又问,那妈妈呢?我指着在一旁玩的小弟弟对母亲说,让他给你买去。哪知小弟弟是跟着我走的,也嚷着说要买给爸吃。母亲的脸就挂不住了,继而竟抹起泪来,说白养了我这个女儿。父亲在一边讪笑,说孩子懂啥。语气里却透着说不出的得意。
待到我真的长大了,却与父亲疏远了。每次回家,跟母亲有唠不完的家长里短,一些私密的话,也只愿跟母亲说。而跟父亲,却是三言两语就冷了场。他不善于表达,我亦不耐烦去问他什么。无论什么事情,问问母亲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