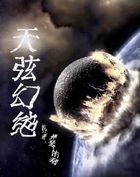约翰·费瑞厄和摩门教先知谈话后的第二天早晨,他就去了盐湖城,找到了要去内华达山区的那位熟人,托他交给杰弗逊?候坡一封信。信中把他们迫在眉睫的危险情况告诉了那位年轻人,要他即刻回来。办完这件事,他松了一口气,便带着比较愉快的心情回家了。
快到农庄时,他惊讶地发现大门旁的两根柱子上各栓着一匹马。他赶快走进屋,发现客厅里有两个年轻人。一个脸色苍白,脸长长的,正躺在摇椅上,两只脚翘得高高的,架在火炉上。另一个脖子短粗,长相粗俗,得意洋洋地站在窗前,两手插在口袋里,嘴里吹着流行的赞美曲。费瑞厄进来时,两个人都向他点了点头。躺在摇椅上的那一个首先开腔。
他说:“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这位是德雷伯长老的儿子,我是约瑟夫?思特杰逊。当上帝伸出圣手,把你们引出苦海时,我就和你们一起在沙漠上旅行过。”
另一个带着重重的鼻音说:“上帝在合适的时候终将把全人类都引进他的天国。这虽然进展很慢,却非常精细,毫无疏漏。”
约翰·费瑞厄冷淡地点头致意。他已经猜到了来人的身份。
思特杰逊接着说道:“我们是奉了父亲的旨意,来向你女儿求婚的,请你看看我们两人中谁更合适。我只有四个妻子,而德雷伯兄弟已经有了七个,因此我比他更需要。”
“不能这么说,思特杰逊兄弟,”另一个急忙嚷道,“问题不在于我们已经有了几个妻子,而是我们能养活几个。我父亲已经把磨坊给我了,所以我比你有钱。”
思特杰逊激烈地反驳道:“但是我将来要比你有钱。等上帝把我父亲招去,他的硝皮坊和制革厂就由我掌管,再说,我年纪比你大,在教会中的地位也比你高。”
小德雷伯一面对着镜子讪笑,一面说:“还是让姑娘自己来决定,我们完全听她的选择。”
在这场对话进行的过程中,约翰·费瑞厄一直站在门口,愤怒得忍不住要拿马鞭去抽打这两个不速之客。
最后,他实在忍无可忍大步走到他们面前喝道:“听着,我女儿叫你们来,你们才能来这里。但如果她没有叫你们,我不愿意再看到你们丑恶的嘴脸。”
两个年轻的摩门教徒大吃一惊,瞪大了眼睛望着他。他们原以为,他们这样争着向这姑娘求婚,不论是对他还是对他女儿,都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费瑞厄吼道:“有两条路可以从这屋子出去。一条是门,一条是窗户。你们选择哪一条?”
他那棕色的脸膛显得非常凶狠,青筋暴起的双手透着恐吓。两位客人吓得一下子跳了起来,拔腿就跑。费瑞厄一直跟到门口。
他挖苦地说:“你们俩决定好走哪条路后,请通知我一声。”
思特杰逊脸都气白了。他叫道:“你是自讨苦吃!你竟敢违抗先知和四圣会。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小德雷伯也喊道:“上帝会降罪你的,他既然能让你生,也能让你死!”
“那我就让你先死!”费瑞厄气极而狂吼,震得门户嗡嗡直响。他正要跑上楼拿他的猎枪,露茜就拽住了他的胳膊,把他拦住。他还没有从露茜的手中挣脱开时,就听见一阵得得的马蹄声。思特杰逊他们已经跑远了,他追不上了。
他气呼呼地边擦汗,边喊道:“这两个游手好闲的混蛋!要是把你嫁给这样的人,还不如让你去死。”
露茜表示赞同:“爸爸,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杰弗逊马上就要来了。”
“是的,幸亏他要来了。真盼他早点儿回来,不知道那些混蛋以后还会捣些什么鬼。”
确实,这个坚强的农民和他的女儿正处在一个最困难、最危险的关头,他们急需有一个人来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为他们出谋划策。摩门教控制的整个地区,从来就没有人敢公开违抗四圣会的命令。连犯一点儿小小的错误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那么,像这种公开违抗四圣会命令的事,又该是什么样的结局呢。费瑞厄心里明白,现在他的财富和地位对他来说都不过是过眼烟云。在他之前,也曾有过像他一样有钱有地位的人被暗杀,而被害者的财产则全归了教会。虽然他勇敢,但是对于将要降临的捉摸不定的大祸,他内心还是存在一些恐惧的。他可以直面横在眼前的任何危险,大无畏地去闯,去承担,但是,这种整日心神不定、提心吊胆的日子,实在是让人难于忍受。但他尽量不让他这种感觉表露出来,被他的女儿发现,整天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是,他再掩饰也瞒不过他的女儿,露茜早就看出父亲整日惶惶不安的心思。
他预料到,他的行为肯定会带来难测的祸患,受到先知扬的警告之后,他意料之中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但是那种方式却是在他的意料之外。第二天早晨,费瑞厄起床时惊奇地发现,就在他的被子上,他胸口的那个地方,钉着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
“限你在二十九天之内改邪归正,否则——”
字后的这一横,比任何恐吓的语言都起作用。约翰·费瑞厄无论如何猜不透,这个纸条是怎么送到他的房子里,钉到他的被子上的。因为,他的仆人睡在另一个房子里,而他们家的门都上好了门闩。他胡乱地把纸条揉作一团扔掉,不对他的女儿透露半点儿消息。可是,这件事的发生,却更使他心惊胆颤。纸条上的“二十九天”不就是在提醒他剩下的期限吗。如果单凭一腔热血、勇猛,是对付不了这样神秘莫测的敌人的。钉纸条的那个人,本可以一刀杀死他,会干得神不知鬼不觉,无法知道杀人者是什么人。
第二天早晨,更奇怪的事情使费瑞厄大为震惊。他们坐下来正要吃早饭,露茜突然大叫指着天花板。原来,在天花板的中央,写着很大的“28”,看起来像是用烧焦的木棒写的。女儿不明白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费瑞厄也没有向她解释。当天晚上,他没有睡觉,拿着枪整夜地守着。这一夜,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情况。可是,第二天早晨,他家的门上又写着一个大大的“27”。
就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他每天都能发现他的敌人写下的数字,就像每天黎明必然到来一样,而且那些数字总是写在显眼的地方,来提醒他剩下的期限。有时写在墙上,有时写在地板上,还有的时候写在纸上,把纸贴在花园的门或栏杆上。尽管约翰·费瑞厄万分警惕,他还是不能查出这些是谁在什么时候干的。他每天一看到这些警告,就像中了邪一样感到恐惧。他为此吃不下、睡不着,一天天削瘦下去,他的眼中整天透露着惊慌失措的神色,就像被人追逐的野兽一样惶恐不安。现在他惟一的希望就是盼着侯坡尽快的从内华达赶回来。
日期从二十天变成十五天,又从十五天变成十天,要命的数字逐日记着,可是杰弗逊·侯坡却没有半点儿消息。时光渐渐流逝,离限期越来越近了,还是不见侯坡的踪影。费瑞厄盼他心切,只要听到路上有马蹄声,或者听到吆喝畜群的声音,总要急忙跑到大门外,四处张望,以为是侯坡回来了,可是每次他都失望而归。期限在一天天地缩短,他不得不放弃了逃跑的念头。他孤独无助,对环绕四周的大山又不熟悉,他深深地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了。通行的大道都有人严密把守,没有四圣会的命令,谁也别想通过。他显然已无路可走,看样子他是怎么也避免不了这场大祸了。然而,这位老人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他宁愿以死相拼,也不愿看到他女儿受到这场污辱。
一天晚上,他独自坐在那里,反复思考着他所面临的危境,但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一个摆脱的办法。那天早晨,墙上已经出现了一个“2”字,那就是说,第二天就是限期的最后一天了。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的脑海里装满了各种模糊而又可怕的预测。他死后,他的女儿会怎么样呢?难道他们真的就逃脱不了布在他们周围的这道无形的网吗?想到自己竟然这样束手无策,他不由得伏在桌上哭了起来。
是什么声音?他在一片寂静中听到了一阵轻轻的爬抓声。声音虽然极轻,但在寂静的夜晚却听得非常清楚。那声音是从大门那里传来的。费瑞厄悄悄走进客厅,屏息凝听。那声音停歇片刻,接着又响了起来,轻得令人毛骨悚然。忽然,费瑞厄感到有人在轻轻叩门。难道是午夜刺客来执行秘密法庭的暗杀指令吗?或者是什么跑腿的来写那期限的最后一天的数字吗?约翰·费瑞厄觉得,与其天天这样提心吊胆、胆战心惊地活着,还不如痛痛快快地死了好。于是,他跳了起来,拉开门闩,把门打开。
门外一片宁静。夜色阑珊,点点繁星在头顶上明亮地闪烁。眼前是庭前的小花园,周围是篱笆和大门。但无论是花园里还是大路上,都没有一个人影。费瑞厄环顾四周,暗暗松了口气。当他无意中朝自己的脚下望去时,惊诧地发现那里趴着一个人,手脚直挺挺地伸展着。
看到这副情景,他惊恐万状地靠着墙,用手捂着喉咙才没有叫出声来。最初,他以为那个人可能受了伤,或者差不多快死了。待他仔细一看,只见那人像蛇一样在地上迅速而无声地爬行,一直爬进了客厅。那人一进屋就跳了起来,迅速关上门。这时,他才看清,来人正是他盼望已久的杰弗逊·侯坡。
“天啊!”约翰·费瑞厄又惊又喜,“你快吓死我了,你怎么这个样子进来了?”
“先给我点儿吃的。”侯坡毫无气力地说,“我已经两天两夜没吃东西了。”主人的晚餐还在桌子上原封未动,他跑过去,抓起冷肉和面包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等他吃饱了,问道:“露茜还好吗?”
“很好,她现在还不知道这些危险。”老人回答。
“那就好。这个房子周围已经被监控起来,所以我只好一路上爬进来。他们也算够厉害,可是要想抓住这个瓦休湖的猎人,那还差远了。”
约翰·费瑞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明白现在有救了。他激动地握住年轻人粗糙的大手说:“你真是一个值得骄傲地年轻人。除了你,我们再也没有别的指望了,只有你才能救我们脱离魔爪。”
这个年轻人回答道:“您说的对,老人家。我确实很尊敬您,但是,如果这件事只关系您一个人,我把头伸进这个马蜂窝以前,要考虑再三。但这也关系到露茜,我是为她而来的。在那些混蛋动手以前,我们早就远走高飞了,犹他州不会再有侯坡家的人了。”
“那么,咱们现在该怎么行动呢?”
“明天是最后的期限,除非今天晚上就开始行动,否则就永无机会。我弄到了一头骡子和两匹马,都在鹰谷那边等着。您有多少钱?”
“两千块金币和五千元纸币。”
“这就足够了。我这儿还有这么多钱,可以凑在一起。咱们要穿过大山到卡森城。您现在最好去叫醒露茜,仆人没有睡在这儿,真是天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