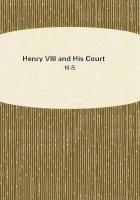福尔摩斯早已掏出了手表。专注地看看狗,又看看表。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仍然没有任何结果。他的脸上露出了极为懊恼和失望的神情。他紧紧咬着嘴唇,手指敲击着桌子,显得非常不耐烦。他的情绪十分激动,连我都不由得真心地替他感到难过。两位官方侦探的脸上挂着讥讽的微笑,心里暗暗为福尔摩斯受到的挫折感到高兴。
“这不会是偶然发生的”福尔摩斯一边踱步一边若有所思地说,“我早就怀疑德雷伯是死于某种毒药,而它终于在思特杰逊死后被发现了,但是它为什么不起任何作用呢?这意味着什么?我敢保证,我对这个案子的推断没有错误,也不可能有错误。可是,这只狗竟没有任何反应。”“啊,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沉默片刻之后,福尔摩斯突然兴奋地大喊一声,迅速跑到药盒前,拿出另一粒药,也把它切成两半,用水化开其中的半粒,加上牛奶,放在狗面前。这只可怜的小狗舌头刚一沾上这种液体,马上四肢抽搐痉挛,接下来就像被雷击了一样,直挺挺地死去。
福尔摩斯放心的出了一口气,擦去了额头上的汗珠。“看来,我的自信心还不够强。刚才我应该了解,假如一种事实和推论矛盾,那么,肯定有某种其他的原因。而不应对正确的推理产生动摇,其实我在看到这药之前就应该想到,盒子里的两粒药,一粒有剧毒,另一粒没毒。”
福尔摩斯的带有哲理色彩的话发人深省。他最后一句话说得如此惊人,我不由得疑心他是否有些不清醒了。狗的死又证明他的推断是正确的。我也开始对这个案子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福尔摩斯继续说道:“你们好像觉得这很奇怪,其实这没什么,只不过开始的时候,你们没有抓住这个惟一正确的线索,而我却幸运地抓住了。以后发生的每件事都证明我的设想是正确的,而这些事情的发生也正是那条线索合乎实际的结果。所以,那些让你们迷惑不解、使案情更复杂的事物,却对我有很大的用处,它们证明我的推断。把神秘和奇怪混在一起不可取,往往最神秘的犯罪是最普通、最平淡的,因为找不到一点特别的线索去侦破它。就如此案,如果尸体在大路上,也没有任何特别的情节引人注意,那么,这个案子很难侦破。所以说,奇怪的事情发生没有使案子更加复杂,而是变得越来越简单。”
格雷格森先生越听越不高兴,最后,他终于忍不住了,说:“福尔摩斯先生,我们承认你是一个机智干练的人,而且有自己独特的工作方法。但是现在请你不要再空谈一些大道理,我们想要捉到那个凶手。事实证明,我和雷弥瑞德都错了,夏明洁不可能是第二个死者的凶手,不可能杀掉思特杰逊,而思特杰逊又被杀了。你说说这个,又提提那个,知道的好像比我们多。现在,你也应该说说对这个案子到底知道多少,我想我们也有权利要求你说。你能说出凶手的姓名来吗?”
雷弥瑞德也附和道:“先生,我也感到格雷格森说得有理。我们俩都努力过,而现在又都失败了。我走进这个屋子以来,你已经不止一次地说你掌握了所需要的一切证据。你现在不该再隐瞒了吧!”
我也跟着说:“如果再不抓住凶手,他可能还会有时间再去危害别人。”
大家这样催促他,福尔摩斯反而显得迟疑起来。他低着头在屋里走来走去,而且像他平常陷入沉思时一样紧皱眉头。
最后,他突然停住脚,对着我们说:“凶手不会再杀人了,你们对此可以尽管放心。你们刚才问我是否知道凶手的名字。我当然知道。可知道他的名字根本算不了什么。只有抓住他才是最后结局。我估计我很快就能抓住他,我要亲自作出安排,而且要安排得非常巧妙细致,因为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非常狡猾、孤注一掷的家伙。事实还能证明,这个凶手有一个和他同样精明的人在帮他。只要凶手自信有人能找到线索,我们就有机会抓住他。但是,只要他稍微起一点儿疑心,他就会改名换姓,立刻消失在这座大都市的四百万居民中。我丝毫没有轻视你们二位的意思,但我得说,我认为你们官方侦探绝不是这两个人的对手,所以我没有请求你们帮助。如果我失败了,我当然会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责任。我愿意承担这种责任。我现在向你们保证,什么时候我的全盘计划不受影响了,什么时候我就会告诉你们。”
尽管福尔摩斯做了上述保证,而且不客气地贬低了官方侦探,格雷格森和雷弥瑞德似乎不甘心就这样下场。格雷格森的脸一直红到发根,雷弥瑞德瞪圆了的眼睛里流露出好奇而又不满的神情。不过,他俩还没有来得及说话,门上就响起了轻轻的敲打声,原来是那不为人注意的流浪儿韦金斯来了。
韦金斯举手行礼说:“先生,我已经把马车叫好了,就在楼下。”
福尔摩斯和蔼地说:“干得好。”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副钢手铐来说:“你们苏格兰场的警方为什么不用这种手铐?你们可以看这弹簧多么好用。一碰就卡上了。”
雷弥瑞德仍然带着不满的声调说:“只要我们能找到该戴手铐的人,那种老式的也照样管用。”
“很好,很好,”福尔摩斯笑着说,“车夫也许能帮我搬一下箱子。韦金斯,请他上来。”
看到福尔摩斯这副要出远门的样子,我不由得非常诧异,因为他从来没有向我提起过。况且此时案子正在关键时刻,他怎么会突然远去呢?屋里有只小小的旅行皮箱,他把它拉了出来,开始给它系上带子。正当此时,车夫进来了。
“车夫,请帮我扣一下这个皮带扣。”福尔摩斯跪在那里忙着,头也不回地说。
车夫一脸不高兴,不大情愿地走过来,伸出手正要帮忙,只听得金属撞击的清脆的咔嚓声,福尔摩斯突然跳了起来。
“先生们,”他大声说道,“我现在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杰弗逊·侯坡先生,也就是杀害伊诺克·德雷伯和约瑟夫?思特杰逊的凶手。”
这一切都是一瞬间发生的,速度快得我们还来不及反应过来。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记得福尔摩斯脸上胜利的表情,记得他那响亮的声音,记得马车夫看到闪亮的手铐神奇地铐在他手腕上时那种茫然、凶狠的神情。有一两秒钟,我们像一尊尊塑像一样站在那里。然后,马车夫大吼一声,从福尔摩斯的手中挣脱出来,猛地向窗户冲去,把窗子的木框和玻璃撞得粉碎。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跳出去,格雷格森、雷弥瑞德和福尔摩斯就像一群猎犬一样扑到了他的身上,把他拉进屋之后,接着又是一番厮打。这个人异常凶猛,一次次地把我们四个人打退。他似乎有着癫痫病人发作时的那种蛮力气。由于他刚才想从窗户冲出去,所以他的脸和手被玻璃划得鲜血直流,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反抗的劲头。最后,雷弥瑞德死死地卡住了他的脖子,几乎要把他卡死。他到这时才意识到反抗是没有用的,可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把他的手脚全都捆了起来。这个名为马车夫实为杀人凶手的人,安静下来之后,我们才气喘吁吁地站起身来,站在那里喘着粗气。
福尔摩斯说:“他的马车就停在楼下,就用他的马车把他送到苏格兰场去吧,这件神秘莫测的小案子结束了。你们有什么问题现在只管问,我会给你们满意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