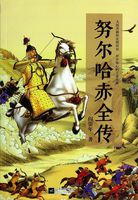活到新的世纪,常常追怀在风云变幻的上个世纪中,我眼目中的群星。其中恩师沈祖棻、程千帆[1]先生在一个甲子中所住留过的七个居室(联想到他们的高洁品质和文学、学术成就),尤其清晰如昨,有如当夜的北斗七星。
我曾经笑问老友,我是一个可信任的人么?沈师逝后,程师亲手将沈师的日记手稿交给我。我也曾写过一本传记型的书经程师手批。
后来我去国离家十年,这书没有出版问世,只在《浙江画报》发表过一篇小文(《沈祖棻和她的词》,载《浙江画报》1985年12月总第78期)。我愧对恩师。
我一生没有对谁宣誓效忠过,甚至对我心仪的群星,也奉守柏拉图所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当我的师弟们出于浓厚感情的追怀,写出感人的悼念文字时,我暗觉过誉而不以为然。尤其是诗歌创作,我特别看重灵犀相通,又何必传世?然而,沈师的诗作,却总有抹不去的光辉在我心头闪耀。
沈师的形象和遗着,对社会对历史是有价值的。用白话文写作的名作家姚雪垠[2]也说:她的作品有什么理由被摒弃在现代文学史之外?不是白话诗,能成为理由么?(其他名家大师的评赞,我将在本书中摘录)对于我来说,尤其难忘沈师在讲台上的魅力。我最爱听精彩的讲座,但再也没有人能使我震撼了。六十年前,在艰难困苦的抗日战争中,在破蔽简易的大学教室里,我忽然看见了我梦想中的千年前的李清照!听见了中华千古精英的声音……这真像一个宗教情结(虽然我始终是一个无神论者)——只有她,才能传述,有如圣徒!
我写下这些话时,还有些自责:莫非也是感情色彩太浓?但近来查翻在美国时影印的华文报刊,才知道一位叫容斋的笔者,早已引人称她:“一千年无此作矣!”(这是名家汪东的评语)他还引了朱光潜的题词:“易安而后见斯人,骨秀神清自不群,身遭离乱多忧患,古今一例以诗鸣。”
沈师的主要创作是古老文体的词。在她还在大学学习期间为名家激赏时,这种文学形式已不是当时的文学主流。但就她当年所写白话诗文看,也是文采焕发的。后来颠沛流离,生活艰难,以旧体诗词抒写寄托,只得到师友知音,难有问世的机遇。但我的观点是:文艺是多元的。比如有京剧,也有昆曲、评弹。时代需要雄壮的进行曲,人民也惦念琴瑟的音韵。灵性的清泉,在古瓶、玉器中,或在山涧闲潭里同样有沁人心脾的效应。既不必矫分雅俗,以雅傲俗;也无须故作姿态,以“俗”贬雅。唤起群众者有功,沟通心灵者也难得;影响大的有它的价值,蕴积深的也自有千秋定论。若只以当时的“票房”衡量,量化一切,也会失去梵高这样的奇才。
那一代人,很多有以旧体诗词言志抒情的习惯。如鲁迅、陈寅恪、吴宓、******、朱德、陈毅……他们吸收古今中外的文化,诗作体现的,有的是人格的魅力,有的是济世的豪情,也有的是兰蕙的幽芳。风格的区别不能妄论高低,百花齐放,才能推动文艺复兴。
诗歌的吸引力,多在于感情的共鸣,形象的鲜活,韵律的和谐。
以婉约见长的词作,那细致曲折的演绎,尤其使人感应深思,久久在心头萦绕。如果只是行家才熟悉的密码语言、专攻者才乐见的深僻典故,一般读者要越过艰难的障碍,往往疲于奔命,减弱了感染力。简易而清新,则使这一代人更容易接受。
在近年的一次文学者聚会上,一个青年在会余问我:什么是诗?
我茫然。她显然不是查不到定义出处的人。面对美文眩目,和“爱你一万年”的超李白式夸张,难于作答。
沈师的诗词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某些差异,提高鉴赏能力。因此我愿有更多的人同享。至少,此书也可作为对一代大师调研的资料吧。
至今,沈师已因车祸,在冷漠无救助中去世(1977年6月27日)三十余年了。程师也于2000年,在极度的关怀与救护中病逝。不同的终结,相同的永远,斗转星移,光辉不灭。再读当年师作及有关评述,那些烙印着时代标记的观点和语言——历史的荒谬,也促使我反思。
但总的感觉是:文艺的天空,越来越广阔。
2004年5月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