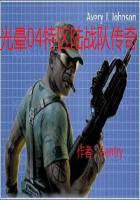过了片刻,朱宝平却气冲冲地来了,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壶汽油,拧开盖就往他的烟上泼,旁边其他人看见了,一些人着急地把自己的烟往一旁拉,一些人喊着“老朱,你疯了”,一边直拉他。那朱宝平也是个倔人,一时咽不下这口气,不顾众人拉扯,把汽油浇完了,把汽油壶往上一扔,掏出打火机,啪地打着火,往泼了汽油的烟叶上一扔,顿时烟叶轰的一下起了火,火焰足有一丈高。众人见得这阵势,都躲到一边去了。胡春华一看这情景,也自吃了一惊,过来就打了朱宝平两拳。这时,烟站其他的人也都忙乱了起来,一个个急急忙忙找水救火。
看着火焰燃起,听着发出的噼啪响声,朱宝平一头跪倒在地上,大哭起来,老泪纵横,他一边哭一边喊:“老天爷呀,你睁眼看一看呀,这世道咋这么不公道哇,这还叫人怎么活呀?老天爷呀,我的烟哪,这是我的命啊。”
祁乡长这时正好经过这里,看见烟站起火了,情知事大,马上停了车,一边又让司机喊乡上干部来救火。交烟的群众见祁乡长来了,一个个就将他围了起来,纷纷状告烟站的人压级坑人,欺负老百姓,告胡春华高价收贩的烟,告胡春华打朱宝平。祁乡长一听肺都要气炸了。这时火在众人的扑救下,也熄灭了,一机子烟仅剩了三分之一,黑乎乎地卷在机子上,周围烟灰乱飞,凌乱不堪。祁乡长让人先把朱宝平拉到乡政府去,然后就扑到胡春华跟前大骂道:“胡春华,你简直是胡来,你今天给我说清楚这究竟是咋回事。”胡春华脖子一梗说:“他要烧烟哩嘛,关我事。”祁乡长说:“与你不相干,不相干老朱就烧烟了?那是钱那是柴草?”胡春华依旧摇着头晃着脑:“他愿烧不烧哩,我管他哩。”祁乡长看到他这态度,火直往上冒,一把扯住他的领口说:“你今天不给老子说清楚,老子要了你的命。”那胡春华是个二杆子,一看乡长要动手了,顺手抄起磅秤上的铁秤砣,扬手就砸在祁乡长的脑袋上。只一下,祁乡长顿时就倒在了地上,额头上血流如注。
这时在场的人都急了,小张、周同还有乡上一帮干部一伙噼里啪啦围着将胡春华拳打脚踢了一顿,一伙就将祁乡长抬到了乡卫生院。在卫生院简单包扎了一下,接着祁乡长被送到了县医院抢救。
乡派出所的人这时也知道了这事,所长郑平安就将胡春华铐了起来,连忙审问填案卷,连夜将他押送到了县公安局拘留所。
祁乡长住到了县医院,当天最先到来的是烟草公司的王经理及林平乡烟站站长一行人。他们带了慰问品,来到祁乡长的病房,这时祁乡长已经包扎结束,头上缝了十来针,正在吊液体,见王经理他们进来,他把头扭到一边去,闭着眼面对着墙,不吭声。王经理走到病床前,坐在床头说:“祁乡长,让你吃苦头了。”祁乡长仍不吭声,王经理说:“祁乡长,都怪我们平时管教不严,这是我的责任,我现在来给你赔情道歉来了。”祁乡长睁开眼睛说:“我吃点苦头不要紧,关键是伤了群众的心哪。当初落实烤烟面积,我是拍着胸脯表了态的,说保证让群众卖个公平合理的价钱。可如今呢?你看看……”说着语气就有些哽咽,说不下去了。
王经理拍着祁乡长的肩膀说:“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你好好养伤,我们会解决的,一定会使你满意的。”
正说着,梁县长带着一干人来了,祁乡长听说县长来了,一把拔下针头,跳下床就要出去迎接。这时县长已进来了,一见此情此景,连忙喊护士给他重新把针扎上。
梁县长说:“祁乡长,我代表县委、县政府来看望你来了,希望你能想开点,干工作嘛,总会遇到一些挫折,这是正常的,不要灰心丧气,要振作起来,以后的路还长着哩,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来干哪。”
祁乡长说:“没事,就擦破点皮,不要紧的,过两天就可以上班了。”
梁县长说:“那倒不急,等彻底好了再说。你的工作县委政府心里最清楚,我梁某人心里也清楚,你是咱们乡镇领导里边最出色的干部之一,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经了这桩事,思想上不要有什么包袱,有什么压力。”
祁乡长听了梁县长这些话,又联想到前几天纪委的调查,就觉得心头特别委屈,忍不住就想掉眼泪,嘴上只是说:“我倒没什么,多少年干工作,这一点解下哩,只是现在最关键的是老百姓,特别是黄羊坡的群众,要是有人不服这事,再闹到市上去,到处乱上访,那特殊问题就成了普遍问题了。”这话分明是说给烟草公司经理听的。
果真,梁县长开始说烟草公司经理了,说:“是啊,现在的问题是赶紧稳定群众的情绪,事态不要再扩大了。王经理,一是对胡春华要严肃处理,不但要处理打人事件,而且还要调查收人情烟和倒贩烟叶的事,你们要借这次事件,好好整顿收烟中的不正之风。二是林平乡烟站原有的人一个不留,全部调换,调一个公平正直的人到林平乡烟站来当站长。第三,要尽快去慰问黄羊坡的群众,特别是朱宝平,朱宝平损失的烟叶钱由你公司负责赔偿,不能让群众损失一分钱。另外,小刘,你通知县委宣传部,要严格控制一切新闻媒体,这事不得再扩大影响。”
王经理说:“行,行,好好。”
几个人又说了几句客套话,一行人就鱼贯而出。
住了三天院,祁乡长就住不安稳了,他要医生开了些针,拿上就回了家。
回家的第二天,朱宝平与黄羊坡的支书却赶到城里来了,他们提了一大包东西来看他。祁乡长吊着针,将大家让到了房子里,让翠花又是倒茶,又是递烟。给大家说:“大家心意我领了,但这东西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要的,其实工作做好了,领导和群众满意就行了。”
支书说:“这是我们村众人和朱宝平的心意,你一定要收下。”
翠花恰好今天上午给娘家送韭菜去了,这阵听见说“心意”这回事,忍不住插嘴道:“要说这心意啊,大家就不用送东西了。大家如果有心意,倒不如每人买上一捆韭菜哩。我家的韭菜多得太哩。”
祁乡长听得她这么说,立时喝道:“滚得远远的。”
翠花伸了一下舌头不吭声了。
大家就都笑了起来。
四
一切事都是这样,发生着,解决着,天天难过,天天都在过。
又在家吊得几天针,祁乡长头上的伤就好得差不多了,到了七天头上,他就又返到县医院里拆了线。
线是拆了,可祁乡长的头上却和蚯蚓爬过似的留下了印痕。老婆瞅着,噘着嘴说:“这下得留一辈子了。”
祁乡长说:“难道就长到头上了?”
老婆心疼地说:“可不,人一上了年纪,这疤痕就好不了了。”
两人正说着,乡上的文书小张却打来了电话。
小张说:“祁乡长不好了,这回可把大娄子捅下了。”
祁乡长一听这话,忙问是怎么回事。
电话中,小张就讲了事情的原委。原来是乡上来了两个女记者,她们一来就威风十足地要找乡上的正职,书记学习不在,祁乡长在县里的家里没回来。小张就接待了她俩,对她俩说有什么事就对自己说。那两个不说则已,一说就说出一桩事来。
她俩从包中拿出一张照片来,说刚才在林平乡上发现了一个沟里有一圈羊,说现在正是封山禁牧的时候,她们来核实一下,然后要写成消息上报的。小张接过照片,看了看,发现照片上是一处山沟里的山坡上,一群羊正在吃草,但背景上除一大堆青草外,赫然有一棵树却是白皮松。小张是从林校毕业的,知道林平乡根本没有白皮松这个树种。再看两人的装束,和地道的农民没什么两样,谈吐也不像是知识分子,由此他就怀疑这两记者是假的,是想借这张照片来诈钱的,就要她们拿出证件来,但这两个记者却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拿出来。她们越不拿证件,小张就越发相信俩人就是假记者。
这时刚好派出所郑平安所长到乡上来了,小张就悄悄地告诉了他这件事,并告诉了自己的想法。郑平安一听,觉得这是个立功的机会,就进了办公室,问俩人是哪的,要她们拿出记者证来。俩人说等见了乡长或者书记再拿。郑所长见她们不拿出记者证,估摸着是冒充的,也是一时欠考虑,当即就掏出铐子要铐两人。
见明晃晃的铐子掏了出来,这两个女的就害怕了,她们从身上掏呀掏,终于掏出了两张记者证来,却是本省某某报农村版的记者,记者证上倒是有公章和钢印的,非常清晰。小张和郑平安俩人瞅了半天记者证,对于真与假怎么也分不出个端倪来。
小张就说:“你这张照片是假的,这不是我们这儿的山,树也不是我们这儿的树,羊也不是我们这里的品种。你们是来诈钱的。”
这句话一说,两女的自知理亏,就不吭声了。派出所所长就吓唬着要逮捕两人,小张觉得事情有些蹊跷,见书记乡长都不在,怕又闯下乱子了,就想放她们走,于是两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将这俩记者打发走了。
谁知走是走了,走了没多久,这两个女的却又返回来了。
原来是这两人“偷鸡不成差点蚀把米”,憋了一肚子的怨气,出了门她们根本就没走,而是到处找人打听养羊的事。终于打问着了林平乡的早然村还有一个人有一圈羊根本没卖。既然没卖,就肯定要放,羊总不能成天圈在圈里吧?当下她俩憋足了劲,问了路,爬了一架山,翻了一架坡,终于来到了该村,也是合该有事,恰好就见一圈羊在山洼里正津津有味地吃草呢,俩人顿时欣喜若狂,拿起相机啪啪拍个不停,同时她们俩还装作游客,和放羊的大爷一块谈了话、录了音、照了相,照相时其中一个女的和那老头一起坐着,怀中还甜蜜地抱着一个小羊羔亲吻。
有了这事,俩人的胆就壮了,重又杀了回来,非要见领导不可。
这回倒把小张弄了个目瞪口呆,小张于是只得赶紧给祁乡长汇报。
现在这阵正是封山禁牧的时候,到处禁声一片,林平乡依然有羊没卖,还在放着,这事要是在报纸上一捅,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他祁乡长这领导还当不当了?听得小张一说,祁乡长情知事情是大事,就赶忙往回赶,可一时液体又吊不完,就坐在车上,一只手扎着针头,一只手提着瓶子往乡政府赶。没想到,路上不平,一颠簸,祁乡长与司机两人又只顾着说话,那液体就漏了,祁乡长只觉得手腕上一阵儿疼,一看,手腕上已肿起了一个大疙瘩,情知漏针了,索性就一把拔掉了。
司机问:“那这药水还要不?”
祁乡长说:“不要了。”
司机就从窗口“日”的一声扔到河里去了,瓶子砸在石头上,发出了砰的声音。祁乡长忽然想:扔了真可惜了,还不如给了老婆让装洋柿子酱哩。
祁乡长匆忙回到办公室,就见两个记者鸡卧架似的并排坐在办公室的排椅上,一个挨着一个。祁乡长一见这两人身上有些土气,一副村民的扮装,情知她们不外乎诈几个钱而已,连忙寒暄了几句,一面又令小张准备饭菜。
事情就是如此简单,这两个记者说发现了还有放羊的,只要乡政府盖个章子,证明这些资料是真实的就可以了。其实像记者下乡采访的一些事,根本不需要盖单位公章的,祁乡长知道这一点,她们这样找借口,不外乎就是想弄点钱而已。祁乡长就一面说公章让人拿到县城去了,一面装模作样地打电话让人往回捎,一边准备了饭,招待两人吃。
两人扭扭捏捏上了饭桌,三两杯下肚,气氛就好多了。不想,俩女记者却又特能喝酒,打点子划拳都在行。祁乡长身上伤还没好利索,不能喝,就派了何副书记和她俩对着喝,酒过三巡,饭过五味,祁乡长就提出让她们别报道了,但两人一致口径说,这事她们拿不了主意,今个小张的态度是这样,她们已给领导打了招呼了,领导已知道了此事,事情要他们领导表态才算数的。祁乡长就拿了一个红包递给他们,说:“乡上事儿忙,和你们领导也说不上话,烦请你们说一下。”那俩人见了红包不知是多少钱,都沉默着,不愿表态。祁乡长就直接说:“这是三千块钱,别嫌少,小意思。”两人心里这才安定了,稍微推辞了一下,就不再说什么,将红包揣到了手提包里,一桌人又开始喝酒。
酒席还在继续,问题解决了,气氛就变了,成了纯粹的朋友间的友情喝酒,双方你来我往,不亦乐乎。
祁乡长见俩女的喝得有些大了,怕她们没见过世面,弄出丑态来,就说自己晚上还得吊针,得先离场,那两个记者这会儿都觉得祁乡长是个好人,提出非要给祁乡长写个报告文学不可,免费在他们报纸上登,不要一分钱。祁乡长也假意应承,一时宾主尽得其欢,各得其所。
从酒场出来,送走了记者,祁乡长却碰上了韩胖子。这时的韩胖子满脸和气,给祁乡长递了一根烟,说他院子里还有两棵树,那是他爷手里栽的,看乡上能不能再补偿点钱。祁乡长从心底里十分讨厌他,心里就骂着:“再补你大个脑。”但这话又骂不出来,就打着哈哈说:“这事不归我管,你问一下文副乡长,如果在政策里边,我们肯定给办。”韩胖子见祁乡长打哈哈,就满脸堆笑,说:“是呀,乡长没办法,县长肯定有办法,县长没办法,估计市长肯定有办法。”祁乡长喝了一点酒,觉得他这话说得有些突兀,话里似乎有话,但也一时懒得问。就说自己还有事就要走。
偏这韩胖子没眼色,看不出祁乡长的喜怒哀乐,非请祁乡长到食堂里去吃饭不可。祁乡长就说有事,韩胖子不识趣地问有什么事,祁乡长一时想不出什么事来,就说得到自己的小姨子珍珍家去一趟,丈母娘安顿了个事。
告别韩胖子,担心自己的谎话有破绽,祁乡长就只能往前走,这样一直走到了珍珍的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