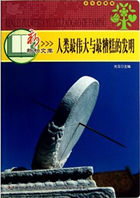一些原因解释了为什么艾滋病感染情况在军队和维和部队中特别严重。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所称,在部队服役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年轻男女,他们认为自己不会受到伤害。服役计划以及驻外部署使他们与家庭分离,而且服役士兵收入稳定,比他们周围人群富裕得多,也更有能力支付性交易或者吸引那些愿意同他们发生性关系的人。平民认为军队和维和部队成员很有权力和权威,这也使得同军队和维和部队成员发生性关系更具吸引力。到目前为止,本章已经讨论了亚洲地区艾滋病感染率的程度和影响。尽管艾滋病已经很好地受到控制,而且在越发达的国家治疗就越容易,在拥有大量发展中国家的亚洲地区,任何关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讨论都必须包含艾滋病问题。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相似,也促使了艾滋病的传播。潜在可能感染艾滋病的人口数目大大超过了已经感染艾滋病的人口数目,这意味着在未来十年中,艾滋病问题会是亚洲政府最重要的安全问题之一。接下来的部分将讨论艾滋病问题安全化的框架。
艾滋病问题安全化的框架
本部分讨论“安全化行为体”,特别是可能促进安全化的“言语行为”和艾滋病问题安全化的指标。这一分析也指出了在正常政策范围内采取或者指定干扰和安全化因素比较困难,该分析以泰国这样已经在安全化艾滋病问题上走了很长一段路,并且正在采取步骤认真对待艾滋病的一些亚洲国家的经验为根据。本章最后部分将讨论亚洲国家艾滋病安全化问题的一般过程。
安全化行为体
中央政府必须承担起针对控制艾滋病作出有效反应的首要责任。中央政府确定国家的首要任务,往往有合法性和权力动员各界人士,并且控制了对抗艾滋病的大部分必需资源。虽然中央政府是安全化过程中的“启动行为体”,但是这一过程中还有另外两组非常关键的“安全化行为体”。
首先是“催化行为体”,即那些必须积极劝导政府将艾滋病问题进行安全化的行为体。艾滋病并不是一个轻易能够自身就安全化的议题。艾滋病病毒较长的潜伏期以及伴随艾滋病的污名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政治因素不愿同艾滋病有关联,而且也不愿提出任何能够更积极地响应这个问题的方案。从此方面看,“催化行为体”在安全化过程中十分关键。“催化行为体”必须已经清楚地确认艾滋病是一个安全问题。如同世界银行、世界货币组织或者其他中央政府,这些对各中央政府有巨大影响力的行为体在劝导一国政府将艾滋病问题安全化方面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事实上,美国政府已经开始这样做,布什总统签定了《美国领导抗击艾滋病、肺结核和痢疾2003议案》(H.R.1298)。美国政府也通过与艾滋病相关的政府和多边机构的双边协商发挥作用。其次是“实施行为体”,即在有效的安全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行为体。他们是一些中央政府以外的行为体,他们将会是建立实施关于控制艾滋病传播政策的必备条件。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都是第二类“实施行为体”的重要构成者。在一些亚洲国家,社会关心是通过其他政府或者半政府组织而不是非政府组织体现的。艾滋病安全化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中央政府要建立政府、地方政府和重要的非政府组织/政府组织抗击艾滋病合作协调的联动机制。
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并非完全意见一致。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已经明确地界定了在卫生领域的权限并且激烈地反抗其他方面对它们权限领域的侵犯。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在公共问题应如何控制方面往往意见相悖。但是,有效地控制艾滋病需要这三方面因素的相互合作和相互协调。非政府/政府组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合作防止了活动的重复,也促使了更加有效地使用资源。地方政府往往在控制艾滋病感染方面联系群众并与群众合作有独特的能力和经验。同样的,与在中央政府相比,当地群众特别是乡镇群众在地方政府里能够更容易地说明他们对政策决策者的需求。地方政府也往往有更具体的机构来展开工作。
例如在中国,地方政府在建立尊重艾滋病感染者权利的法规方面更具亲和力且效率更高。如2002年中国东部的江苏省苏州市颁布了一项特殊的法规,规定了艾滋病感染者的权利和义务,为法律上处理遭受不公平待遇的艾滋病受害者的案例提供了依据。中央政府在三年前就已经草拟了一份相似的法规,但是至今没有颁布。预计在将此草拟的法规交由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得到最后批准通过之前,卫生部还要花费一定时间组织官员和专家进行修订。
非政府/政府组织在遏制艾滋病感染方面也有特别的能力,它们在一些国家中是控制艾滋病的先驱者。非政府组织往往有特殊途径接触性工作者或者注射毒品滥用者,而这些人群传播艾滋病至普通人群以至他们的行为在一些国家的法律下构成了犯罪行为。除此之外,在抗击艾滋病方面,政府同独立的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比扩大政府机构的花费要少很多。在印度,非政府组织比政府机构早很多年就已经开始着手处理艾滋病问题,并且对那些高危人群也有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这一点已经被印度国家艾滋病规划署认可:“灵活性以及创新的途径使得非政府组织能够接触到广大感染人群,但是对政府机构来说这一点很难做到。非政府组织甚至往往能够真实地体现最边缘、最脆弱人群的需求。”印度国家艾滋病规划署已经开始了一些计划,在这些计划中,它通过非政府组织接触高危人群。
尽管非政府/政府组织在处理艾滋病问题上非常重要,但是也要注意到公开地致力于抗击艾滋病并代表携带艾滋病病毒人群或个人的非政府/政府组织在安全化过程中,它们是“实施行为体”中必须的也是弥足珍贵的力量。很少有其他“言语行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说服力如同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群特别是携带艾滋病病毒的社会名流一样大。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群也提供了关于个体行为需求和心理的见解,很少有其他行为体能够如此促成控制艾滋病的有效政策的制定。“实施行为体”中的第三类是宗教组织。在柬埔寨,自1998年起,一个由僧侣建立并经营的宗教组织“瓦特·诺丽和平组织”(Wat Norea Peaceful)开始资助艾滋病孤儿并致力于淡化艾滋病携带者所面临的污名。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也协助参与政策制定进程,并促成了三年艾滋病战略的提出。该组织也在神学院开展倡导性培训讨论会的活动。同样地,在泰国,僧侣通过“僧伽梅塔项目”(San Gha Mehta Project),在出诊期间提供咨询服务并照顾大量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他们也培训其他僧侣和尼姑关于艾滋病的信息,帮助设立资助小组,培训乡镇居民如何预防艾滋病及照顾艾滋病孤儿。
鉴于宗教组织为公众服务的历史悠久、它们的道德权威以及在一些情况下所掌握的财政和机构资源,宗教组织现在已经在控制艾滋病方面较好地树立了其重要性。在向普通群众传播艾滋病是一个安全问题这一信息上,宗教组织的这些特点显得非常有用。将宗教组织纳入到“实施行为体”中也十分关键,因为这种机构可能会传播一些与安全化艾滋病问题相悖的信息,如鼓励人们不使用避孕套。
“实施行为体”中的第四类是媒体。科菲·安南在2004年1月对全世界领导者的发言中指出,“在艾滋病的世界,沉默意味着死亡”。在泰国,大众媒体对哨兵调查结果的广泛传播被认为是泰国艾滋病政策发展的重要催化剂之一。商业大众媒体的独立性也被认为增加了政府关于艾滋病信息的可信度。根据曼谷的一家国际艾滋病预防机构的一名代表所说,“大众媒体为改革社会规范来抗击艾滋病所需的国家政策对话提供了唯一的平台”。一个同样有力的可传达艾滋病严重程度的途径就是通过电影、戏剧以及影星的个人吸引力。像印度这类好莱坞电影已经进入绝大部分居民视野的国家,大众极有可能从媒体的进一步涉入中受益匪浅。
最后,商业部门和工会也是重要的“实施行为体”。艾滋病正如本章之前所提,是一种主要影响处于生殖高峰阶段人们的疾病。商业部门和工会是接触处于危险中的人群的重要节点,私人企业往往也能够提供重要的但是极度匮乏的财政和管理资源来实施有效的艾滋病计划。
安全化过程中所涉及行为体的复杂范围说明这一问题安全化过程也同样复杂。
安全化过程:劝导和协商机制
哥本哈根学派指出,安全化过程同语言学的“言语行为”相似,“通过说一些话,完成了一些事情(例如打赌、许下承诺以及给一艘船命名)。”进一步描述“言语行为”时,布赞等指出:“安全的言语行为并非只是说出安全这个词,关键在于指出存在需要紧急行为或者特殊措施的威胁,并使得重要的听众接受这种指定。”
“言语行为”的进一步描述或者例子是有限的,而“言语行为”的精确特征对于哥本哈根学派而言,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不清。哥本哈根学派也没有详尽地讨论那些“言语行为”的实施者,即“安全行为体”,因而这样的模糊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可预计到。“言语行为”的特征紧密地同做出这些行为的人或者群体相联系,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由它们的来源和对它们“重要听众”的影响所形成。依据之前关于“安全化行为体”的讨论,本章确定了艾滋病特有的安全化过程的四个步骤。这里阐述的一个关键过程是,交流必须发生在中央政府(发起行为体)与广大群众之间。很大程度上以此过程为特色的言语(政治领导者)紧密地与哥本哈根学派所描述的“言语行为”相符。但是,安全化的其他过程,特别是“催化行为体”,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过程以及政府与“实施行为体”之间的过程不能贴切地与“言语行为”相符。虽然哥本哈根学派没有详尽指出“言语行为”的构成部分,但是仍然暗示了信息的单边传递即“言语”。中央政府与“催化行为体”之间的重要过程以及中央政府与“实施行为体”之间的重要过程有可能通过互动过程成功地加以控制,其间涉及说服和协商。就此而言,本章讨论了艾滋病特有的安全化过程,使用了范围更广的术语——“说服以及协商的过程”。言语行为可能被认为是这种更广泛的交流中的一部分。
如上所述,安全化的关键过程即政府通过此过程向更广泛的人群传播关于艾滋病威胁的信息。各个级别的政治领导特别是高级别领导在公共场合的常规活动和话语在安全化过程中至关重要。在一些亚洲国家,相似的过程已经展开,而且已经在抗击艾滋病方面有着特别有效的贡献。柬埔寨的政治领导者由于其在国内控制艾滋病感染方面所起的作用受到广泛赞誉。柬埔寨总理洪森已对艾滋病的严重程度做过定期声明,例如“艾滋病比战争更加严重”。美国负责卫生科学的助理国务卿也指出,在泰国,“国家领导者通过艾滋病对社会可导致的潜在破坏的预测作出有意识的决定,不仅要国家领导者讲出来,更要让部长级官员尽其责……让整个政府谈论这些……这使得社会其他部门——如宗教社团和商业社团——的领导者仿效他们”。安全化过程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步骤必须发生在“催化行为体”和中央政府以及中央政府和“实施行为体”之间。国际机构如联合国已经努力鼓励各中央政府通过在高级别场合讨论艾滋病问题来抗击艾滋病,其中最著名的是2001年联合国大会关于艾滋病的特别会议。世界银行和世界货币组织致力于鼓励中央政府通过坚持有效地将抗击艾滋病计划纳入减贫战略规划来采取针对艾滋病的行动,它们也坚持调节并评估中央政府与其他国家利益共享者之间为抗击艾滋病形成的伙伴关系。其他国家政府,如美国,已将对外援助同受援国对艾滋病作出全国性的有效应对相挂钩。中央政府可能采用各种机制与“实施行为体”进行交流,并影响它们参与到安全化过程中。各种行为体能够聚集阐述自己的观点并致力于相互合作与相互协调的会议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中央政府往往控制着流向地方政府的资源。在一些情况下,中央政府需要依赖地方政府来提供资源。中央政府也在一些情况下为政府机构、非政府机构和宗教机构提供资金,政府机构、非政府机构和宗教机构、媒体、工会和商业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在它们工作中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鉴于这些群体之间的大部分协商情况,其中一个群体与另外一个群体关系的历史背景以及对它的相对影响可能会构成劝导可能的“实施行为体”加入安全化艾滋病问题的动态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