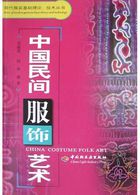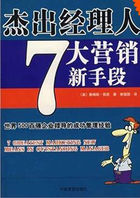孔传为孔道辅之后,“有《杉溪集》及道辅击蛇笏藏于家”。击蛇笏历代相传,八传至孔涛,孔涛请赵孟、白珽、许谦、黄溍等当时名贤为之作诗作文。白珽《击蛇笏》云:“圣学亿万年,圣源浩无涯。八传得巨源,愤学求似之。遗经与遗物,保护如婴儿。万里去复远,见者咸赍咨。况此一尺槐,千载孔林思……畴能起段公,共赋甘棠诗。”许谦《孔涛巨源携八世祖中丞击蛇槐笏求诗》云:“君家爱甘棠,什袭传八世。岂惟子孙珍?观者咸起畏。勿徒宝此传,肖德惟尚志。”击蛇笏之所以令“观者咸起畏”,主要是让人们从中感受到孔道辅所表现的凛然正气。同时,孔氏族人“肖德惟尚志”,努力继承、践行、光大“圣学”。南宋以降,孔氏南宗代有才人,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刚直磊落、成就卓著的士人,如孔传、孔端隐、孔洙、孔涛、孔贞时、孔庆仪等,不胜枚举。
徽州支作为孔氏南宗的重要支派之一,对遗物的珍藏也为人称道。徽州支祖孔端朝南渡时,悉心保护上世告敕、祖父遗书及孔氏家谱。绍兴元年(1131)四月,孔端朝任黟县令,“六月张琪犯徽州,黟之四境焚杀一空,端朝与幼累奔山间,仅得不死,所携上世告敕、祖父遗书,生生所资皆失之矣,独此谱山中人得之,转以见归。此谱乃古本,叔祖贰卿削去旁支,独载世袭者,有识惜之,今亡而更存,岂非天也?”“生生所资”足见其珍视之情,“亡而更存,岂非天也”足见其对家谱失而复得的庆幸之情。孔端朝之后,不但将诰敕世代相传,而且继承发扬了孔端朝之思想,认真研习儒学,因此多有出仕为官者,在当地产生了重要影响。
南宗族人对珍宝的珍视与世代相传,既体现了对先辈的“孝”与无限追思,也体现了对故乡曲阜的思念,更体现出对宗族精神与文化的薪火相传。孔氏族人南渡以后,一方面通过建立家庙、祭祀先祖、续修谱牒、家学教育等途径开展传统的宗族活动,传承并发展孔氏家族深厚的宗族文化;另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从事政治、教育、文化活动,衍圣弘道,化民成俗。南渡后不久,孔氏族人便陆续到各地赴任,如孔端朝任黟县令,孔端问任奉新县丞,孔端植任通城令,孔传任抚州军州事等职,孔端友知郴州,孔瓒知和州等。正如孔柳先所析:“滞留在衢州的孔子世家,其男性人员,绝大多数为官赴任去了。留在衢州的暂住人员,都是他们的女眷和子女,这是一个人数较多的人群,由孔传的夫人和季子端己统领,孔玠年幼,也在其中。”孔氏扈跸南渡本身体现了孔氏家族对宋廷的忠诚;孔氏族人寓居衢州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处理好宗族事务之后,陆续赴各地为官赴任,更体现了其对朝廷的拳拳之心。关于南宗族人重礼之精神、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发扬以及其重要作为,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作详尽阐述。
三、定居衢州与孔氏南宗之界定
孔氏家族南迁对江南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史称“东南阙里”的衢州,使民众得“近圣人之居”,并将之视作“天心之眷顾”,由此,衢州受孔氏南宗的影响也更为直接、更为广泛。正如地方志中所载:“今圣裔之迁衢,岂非天心之眷顾耶?而愚又以为天之意即圣人之意,圣人者必有所取于衢,而故以其裔寄之也,即未必以衢私其裔,而实以其裔重吾衢。”尽管历代典籍对孔氏南渡的记载不少,但“关于当初中国这个第一家族为何赐居衢州,却语焉不详,缺乏相应介绍。也许当时兵马倥偬,失于记载;也许后学浅陋,疏于检索,总之,对此问题,似乎成了历史悬案”。关于孔氏南宗定居衢州的原因,现代研究者大多认为是基于当时衢州相对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建炎年间,衢州处在追袭赵氏王室的东西两路金兵进军路线的中空地区,是两浙十三州府中,唯一没有遭受金兵烧杀抢掠破坏的地区。到了绍兴初年,衢州成了两浙各州府中社会最稳定、经济最繁荣的州府”。陈定謇先生在综合考察当时衢州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其他因素之后认为:“孔氏一族地位显赫,但无关政要,把他们安置在杭州上游未遭异族洗劫,文化极为发达的衢州正是适得其所,看来是最佳的选择。”正是因为时局与衢州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孔子世家在衢州滞留二年之后,于绍兴二年(1132)决定长期定居于衢州”。
金华名儒胡翰指出:“由春秋以来,传序五十有三世,庙于鲁者,礼也;舍鲁而南者,宗子去国,以庙从焉,亦礼也。”可见,诗礼传家作为孔氏宗族文化的重要内涵,修建家庙、祭祀先祖作为孔氏家族的重要宗族活动,在孔氏族人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在南渡之后建家庙成为其头等大事。南渡之初,“诏权以衢州学为家庙”,南宋宝祐二年(1254),菱湖家庙建成,此后,又两迁其地,分别是城南家庙和新桥街家庙。孔氏南宗家庙在历史上多次毁坏,多次修建,其修葺受到历代政府的高度重视。孔庙(也称文庙)虽然遍布天下,然而“为孔氏之家庙者,则惟曲阜与衢”。所以,古人在谈到衢州孔氏家庙时,往往与曲阜孔庙并提,如“地位崇广,规制壮严,遐瞻阙里,实相辉映”;“与阙里之堂南北并峙”。曲阜为圣人故里,历代无数帝王、官僚、士人亲临曲阜,祭祀孔子,家庙在人们心目中无疑是神圣之地,因为有了“与阙里之堂南北并峙”的孔氏家庙,因为有了孔氏南宗族人的衍圣弘道,衢州于是就成为神圣的“东南阙里”和“仲尼家”,“尤为南邦人士中心所向往”。在孔端友和孔传的积极努力下,孔氏家族的宗族事务在南迁后很快得以开展,宗族传统和文化由此得以传承。同时,孔氏族人也遍布南方各地,分支众多,彼此之间也存有诸多关联,形成了族人规模庞大、宗族文化深厚的孔氏南宗,在南方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近几年来,关于孔氏南宗的研究也逐渐引起广泛关注,在史料收集、整理与重大史实的考证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突破。与此同时,人们对孔氏南宗的界定也渐趋一致。徐寿昌、崔铭先两位先生认为,孔氏南宗具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我们认为,只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相统一的角度来认识孔氏南宗的内涵与外延,才能更全面、更深入地揭示孔氏南渡的意义及其历史影响。
从狭义维度上看,孔氏南宗仅指南宋初年随宋室南渡的孔氏族人。徐寿昌先生认为:“‘宗’者,此系‘宗族’、‘宗派’之谓也。‘南宗派’的内涵,是宋金战争和对峙时期,始终效忠于赵宋王朝而南迁的孔子后裔;其外延则是所有与孔端友一起,或像他一样从宋室南迁的孔氏族人。”这里很显然是就狭义的孔氏南宗而言的,也是现在很多人论述孔氏南宗的基本切入点。《衢州孔氏南宗家庙志》在《支系》中将孔氏南宗分为“南宗派”、“衢州派”以及“其他派系”予以介绍。其中,“南宗派”为“孔端友一系流寓后裔”,下分江夏支、漳州支、潮州支、南浔支、杭州支;“衢州派”为“孔传一系流寓后裔”,因“传有七子:问、己、守、位、植、隐、惟,其中守、惟无嗣”,故“衢州派”除“一部分寓居衢州”外,下分长支、二支、三支、四支、五支,分别为孔端问、孔端己、孔端位、孔端植、孔端隐的流寓子孙;“其他派系”则包含徽州支、永康支、钱塘支、吴兴支等。
从广义维度上看,孔氏南宗除了从宋南渡的孔氏族人之外,还包含南宋以前已南迁,并于南宋时归附南宗衍圣公的孔氏族人,如会稽支(孔子二十二世孙孔潜避地徙会稽)、临江派(孔子四十世孙孔绩仕于临江,其后居此)、广州支(孔子四十一世孙孔昌弼唐末时避地南雄,其后移居广州)、温州支(孔子四十二孙孔桧于后唐时迁徙定居温州)等。孔氏南渡以后,衢州成为南宋境内各支孔氏族人(包括南宋以前南迁的孔氏族人)会族之地。孔氏南宗积极进行收族的努力,对各支派起到凝聚作用,“南宋境内之孔氏,却仍以衍圣公马首是瞻,心悦诚服地接受孔氏南宗府管理。即便是早于孔端友南迁的孔氏族人,亦到衢州叙旧典、续昭穆,也把衢州当做是东南之阙里,心甘情愿地接受其制约”。因此,南宋之前南迁的孔氏族人也称南宗宗子为“南宗子家大人”或“南宗子家老爷”。诚如孔德成所说:“后五传而至端友公,以从宋南渡,家于衢,是谓南宗。元至元间,洙公北逊,由元迄今,几六百年,承袭罔替,是谓北宗。夫北宗有六十户,南宗则衢州一支之外,凡宋时南渡与晋唐代南徙者尚有十余支。”这里所讲的“南宗”便是广义上的孔氏南宗。
第二节孔氏南宗与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也称政治认同),是指社会成员(民众)对国家所持的政治文化具有较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政治认同所要解决的是个人的政治归属感,即个人从心里、情感和价值上应归属到那一个政治群体或国家,也就是确定个人的群体身份和国别身份”。政治认同虽然和国家机器密切相关,但它属于非强制的范畴,换言之,政治认同主要是从心理和文化层面实现个人对集体、政治系统的认知、情感和价值判断。国家要实现得到社会成员认同、尊重和自愿服从的政治目的,运用具有象征意义和符号特征的有效载体便是其中的重要途径,即通过代表国家核心价值观念的象征符号使国家“人格化”,使人们能在感官所及的实在对象中感受和想象国家,因为“国家是不可见的,它必被人格化方可见到,必被象征化才能被热爱,必被想象才能被接受”。
代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儒家文化,“一直是华夏民族的精神轴心,它不仅提供了先民彼此认同的最广泛的思想基础,而且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普遍精神依托,它为处于严重利益分化状态的社会,创造出了一条人们彼此沟通与认同的纽带,为社会的融合提供了一种极具感召力与号召力的思想理论,它在心灵深处诱导亿万人民彼此认同与亲和”。可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的国家认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历代帝王崇儒重道,通过各种尊儒活动向社会成员宣扬、灌输主流政治意识和文化价值,以强化国家认同。对孔氏宗族的重视和利用,是历代统治者尊儒崇儒的重要表现,其具体表现则是不断强化孔氏后裔的身份意识,提高孔氏后裔的地位,以达到强化国家认同的目的。
以衢州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历史上深受吴越文化和荆楚文化影响,“其风悍以果,君子耿耿好义而敏于事”,又因“居浙右之上游,控鄱阳之肘腋,制闽越之喉咙,通宣歙之声势”的区位,“矿寇出没,客兵往来……民罹其殃”。北宋初年,吴越王钱俶纳土归宋,两浙地区归属北宋,但因人口成分复杂、文化价值观多元以及官民矛盾突出,两宋至明清时期都存在较强的地方政治离心势力,对地方安定和国家统治构成隐患。宋代以来,封建政府一方面加强对浙西南地区的政治统治,一方面不断强化政治(国家)认同,使“个人从心理、情感和价值”上归属到“一个政治群体或国家”。这实际上是一个“文化”过程,没有文化认同就不可能出现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进一步产生出政治认同。孔氏南迁及其活动对浙西南社会的国家认同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我们认为,这一作用的实现必须具备以下两个因素:一是需要国家扶持,即依靠国家机器保持孔氏家族的身份和地位;二是通过孔氏家族的自身作为在地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以此强化国家认同。
一、历代政府对孔氏南宗的扶持
(一)宗子封爵
自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至圣苗裔”历来受到各种优待,“六经之道,帝王世守之,君臣父子所谓不胥为夷者,皆夫子之赐也。读其书,享其学而可不禄其苗裔乎?”在此背景下,“宗子封爵”也就自然地成为历代统治者推行尊孔崇儒的重要手段和内容。北宋宣和三年(1121),孔子第四十八世嫡长孙孔端友“袭封衍圣公……以示崇奖”,后成为南宗始祖。孔氏南渡之后,情形依旧。高宗绍兴二年(1132),孔端友去世,即“诏以其子玠为右承奉郎,封衍圣公”,形成了衍圣公传承体制。此后,南宋王朝先后赐封孔氏南宗四代嫡长孙为衍圣公,即孔搢、孔文远、孔万春、孔洙。
元至元十九年(1282),孔子第五十三世孙孔洙将衍圣公爵让与曲阜族弟孔治,南宗于是失去了爵位,这就是“孔洙让爵”。南宗衍圣公爵位,从始祖孔端友开始到孔洙让爵,前后历经六代,一百五十三年。孔洙让爵之后的两百多年中,失去爵位的南宗后裔“子孙益多,庙乏主祀,衣冠祭仪混同流俗”。明武宗“甚悯之”,于正德元年(1506)应衢州郡守沈杰之奏请,封孔子第五十九世孙孔彦绳为翰林院五经博士,以主祭祀,并“令世世承袭……以称朕崇儒重道之意”。清代沿袭明制,仍封孔氏南宗嫡长孙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自孔彦绳开始,明清两代,孔承美、孔弘章、孔闻音、孔贞运等总共十五世南宗孔氏后裔先后袭封翰林院五经博士。
民国2年(1913)11月,北洋政府颁布《崇圣典例》,保留北宗衍圣公爵位,改衢州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为世职“南宗奉祀官”。民国24年(1935),奉国民政府行政院令,改授南北两宗宗子为“大成至圣先师南宗奉祀官”和“大成至圣先师北宗奉祀官”,孔子第七十四世孙孔繁豪成为首任“大成至圣先师南宗奉祀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