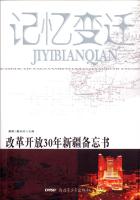如前文所指出的,对新自由主义经济霸权的抵抗,试图挽救处于边缘的人群和国家虽然是全球公民社会兴起的最直接原因之一,但实质上,这一切都可以转化为因为对国家的失望而在万般无奈的境遇中寻求自救。可以说,正是因为国家没有很好地尽到规制资本权力、保护社会的义务,人们逐渐丧失了安全感,这才寻求变革的。鲍曼在《生活在碎片中》一书里曾经谈到过这样一种观点,个体往往不愿意自己做出决定,因为做决定就意味着必须经历选择的痛苦,还是由他人替自己做决定比较好。依据这种观点,对国家主义的反抗就不是反抗国家本身,而是反抗作为家长的国家为自己作了不好的选择,带来了自己所不愿意接受的后果。如果国家合理地规制资本,既实现了发展的职能,又实现了社会公正的职能,那么,这样的国家主义是能够被接受的。因此,如果说全球公民社会是在延续一种“非政治化”的追求,那么,它所追求的“非政治化”并不等同于完全排除传统的政治的“契约的”和经济的“市场的”调节方式,而只是希望在这两种调节方式之外,发展出一种新的调节方式——我们暂时称之为社会的“协商的”调节方式。并且,“协商”作为调节方式所要谋求的是从国家的强制权力中获得解放、与国家相联合共同抵制资本的盲目扩张以及消除资本对生活世界造成的不良影响。也因此,我们不妨将全球公民社会看作是一个试图既超越国家主义又超越市场主义的领域,是国内政治中的“第三条道路”向全球领域的延伸。吉登斯和赫顿合作的一篇文章中有过类似的看法,他们写道,现在需要的能够支持全球化的哲学“既不是新自由主义,但是它要像新自由主义一样,代表着与旧的民族国家框架的决裂,代表着与乌托邦国际主义(这种思想的根基是在全球层次扩展社会主义)的决裂……这种哲学是一种国际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在坚持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热诚信仰民主、殷切地关注人权的同时,融入了更为有效的经济和社会治理。我们需要给正在兴起的全球公民社会添加制度和思想框架,以便使自由主义(我们说的是最好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在这个框架中能够摆脱其不能管理全球市场经济的宿命。”超越国家主义与市场主义并非一种不要国家和市场的观点。很多人看到全球公民社会与国家和市场相互排斥的一面,而忽略了它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虽然在讨论中,我们也曾将全球公民社会不能独立于国家和资本看作是它的无法实现自主和自治的原因,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如果离开国家和市场,全球公民社会根本无法生存,它必须借助于政治权力来推行一系列的主张,而市场是培养其经济能力的场所。全球公民社会的自主和自治不在于它必须与国家和市场决裂,而在于在与他们的关系中保持相对独立性。
至此,我们可以借用克劳斯(Colás)的话来做一个基本的论断,全球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市场关系重建这个更为广泛的进程中的一部分”,它的未来取决它在三方治理结构中的作为。而理想的治理状态是无论在地方层次、全国层次、区域层次还是在全球层次,国家与市场保持平衡、国家与公民社会保持平衡、公民社会与市场保持平衡。因为如果国家过于强大,社会和市场就会受到压制;如果市场过于强大,社会正义必然受到侵害;而如果公民社会过于强大,社会又会陷入“种族分裂和认同冲突”。反言之,如果国家过于弱小,安全和发展都失去了保障;如果市场过于弱小,国家和社会都缺乏物质支撑;如果公民社会过于弱小,恰当的治理和稳定的经济发展都无从谈起。因此,当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三方各自发育成熟并且形成权力抗衡的时候,全球公民社会的历史就完成了。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当前的全球政治变革的前进方向预示着全球公民社会终将获得实现,它并不是一个正义的乌托邦。
但是,就目前的状况来看,要实现相对独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自治,全球公民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现阶段,全球公民社会的主要任务仍在于不断发展壮大,以促成全球治理体系的形成。为此,首先,全球公民社会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国内和国际事务,获得更为广泛的认同,力求成为一种重要的治理和全球治理主体;第二,全球公民社会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国内法律政策的制度,以促成民主的全球治理规则的形成;第三,全球公民社会要更加积极地推动不同层级上的公民参与,通过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全球社会运动、全球网络、全球公众领域等多种形式,密切关注和监督政府和市场行为;第四,全球公民社会要更加积极地批评和抗议不平等、侵犯人权、破坏生态环境、政治腐败和低效等现象,以迫使政府和企业更加负责;第五,全球公民社会要更加积极地在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方面发挥作用,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贡献力量;最后,全球公民社会要更加积极地监督和评估各国和全球的治理绩效,推动治理模式的不断更新。
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公民社会还要有意识地克服自身的局限性。比如,要逐步改善当前存在的官僚化和商业化倾向;提高公民素质、培育公民的参与精神;克服内部精英化、专业化、等级化等弊端,努力趋向民主化,加强内部团结,避免“碎片化”;扶持发展中国家公民社会的建设,平衡南北力量等等。
只有这样,全球公民社会才可能健康有序地成长,逐步确立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
综上所述,以通信技术为支撑的全球联结的便捷性,带来了个体主体性的张扬和公民结社运动的大发展,在各个国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结构性调整中,全球公民社会开始兴起。在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全球公民社会对民族国家和国际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在理论和实践中支撑民族国家的核心概念——主权、公民身份和民主都因其强大的发展势头而被再讨论。全球公民社会对国家的影响不能被忽视,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夸大这种影响。在目前,国家在现实中仍然是强大而不可缺少的,并且它不断地在进行自我更新以提高对新形势的适应性,另一方面,全球公民社会仍然弱小并且局限重重;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中,我们也还无法找到全球公民社会理论的自洽性,取消国家主权的、以全球公民为基本单元的、依靠全球民主来维系的全球公民社会与传统的乌托邦有着极大的亲缘性,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难以捉摸到它的边界。因此,我们更加愿意设想一种并不抛弃政治权力的全球治理结构,在其中,国家、全球公民社会和全球市场平等相处、各司其职、通力合作,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这种愿望既充分肯认了全球公民社会的重要意义,同时极力去除笼罩在它身上的乌托邦色彩,它以已经存在的全球合作为基础,同时又是对一种高于当前合作形式的全球治理结构的追求,它是可欲可求的。然而,即使是这种愿望,我们深知,也是需要全球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对此,我们充满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