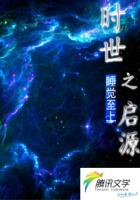既然这些思想必然带来我们科学观的变化,它们当然遭到了抵制。基本上来说,对这里所提出的思想存在两点抵制。首先,抵制来自于那些对传统观点仍旧感到亲切的人。在此我们看到的是对我们在这一章中所展开的种种论证的不屑一顾,他们认为我们的任务是寻找微小的细节或者等待着通过更多的研究驱散笼罩在传统理论边界上的浓云。第二,这种拒斥有着更为普遍深入和微妙的形式。在此我们看到他们也同意演化理论需要修正,然而却又保留了足够多的旧观点,以至于这个修正并不是根本的,而仅仅是装点门面而已。就当前的情况而言,尽管(1a)几乎在生物学和认知科学中被普遍接受,但(2a)和(3a)仍然是少数派的立场。
对我们而言,在仅是部分的变化与我们想要的更加彻底的修正之间的差异依赖于与环境耦合的观念是如何被概念化的。我们的主张是,当(1)到(3)的逻辑被一致地运用时,我们便不可避免地被引向(4)。让我们更仔细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按照传统的看法,生物体在其中演化并逐渐了解的环境被认为是现成的、固定的,且是唯一的。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生物体基本上是凭空降临到一个既定环境中的思想。当我们允许环境有所变化时——达尔文从经验上对这个变化已经很熟悉——这个过于单纯的观念经历了一个改进。这个变动的环境提供了选择压力,这一点形成了新达尔文演化理论的支柱。
然而,在把演化作为自然漂移的推进中,我们走得更远:我们重塑了选择压力,将其作为要被得到满足的更广泛的约束。这里至关紧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并不保留一个独立的、既定的环境的观念,而是让它隐退到支持所谓的内在因素的背景中。相反,我们尤其强调的观念是:环境是什么与生物体是什么以及它们做什么是不可分割的。这一点已经被理查德·莱文汀明确地表述过:“生物体与环境实际上并不是分别被决定的。环境并非是一个从外部对生命体施以影响的结构,它实际上是这些生物体的创造。环境并不是一个自治的过程,而是一个对物种生物学的反映。就如同不存在脱离环境的生物体一样,也不存在着脱离生物体的环境。”
因此关键就是这些物种通过满意生成和规定了有待解决的其自身的问题域。这些领域并不是现成存在于环境之中,就好像对生物体而言环境是它们降落到世界中的着陆垫。相反,生命体与其环境通过互相规定或共同决定而处于相互的关系之中。因此我们将其作为环境的规则性而加以描述的东西,并不如同表征主义和适应主义都共同假定的那样是经过内在化了的外在特征。环境的规则是共同(conjoint)历史的结果,一个从共同决定的长久历史中展开的协调。用莱文汀的话来说,生物体既是演化的主体,又是演化的客体。
我们不能太过强调这一点,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诱惑,即在走向非适应主义演化观的运动中,保留生物体和环境作为分离的两极,而接着又试图去确定各自所占的比重——有点儿内在因素外加一点儿外在限制。然而,这种瓦解演化动力学的模式完全不再适用了,因为它把天赋对习得、自然对教养这些被认为过时的问题强加给我们。但正如苏珊·奥亚玛极其敏锐的分析所指出的,像自然对教养这样毫无希望的问题事实上是拒绝退场的,除非我们学会将生物体和环境视为彼此展开又彼此包进的结构。奥亚玛说道:
形式在连续互动中涌现出来。它远非通过主体来对事物施加影响,而是在诸多分级层次上事物的反应性功能,是对彼此互动作出回应的功能。因为相互选择、反应和限制仅仅发生在实际的过程中,正是这些协调了DNA不同部分的活动,使得基因的影响和环境的影响相互依赖,就像基因和基因的产物是彼此的环境,就像外在生物体的环境通过心理的或生物化学的同化成为内在的,就像通过产物与行为(这些行为选择和组织着外部世界)使内在状态被外在化。
因此,可以更好地将基因设想为这样的要素,它明确了在环境中必然是固定的作为基因起作用的东西,也就是说可以预言它与结果之间的相互关联。在每次成功的繁殖中,一个生物体传递了基因,也传递了基因内嵌于其中的环境。我们把环境的特征,诸如阳光和氧气,看作是独立于生物体的,仅仅由于我们的参照框架是相对的。然而,与此不同的一种看法是,世界是相互联系的。再一次地,这个世界不是一个生物体空降于其中的着陆垫:自然与教养处在一种彼此作为产物和过程的关系之中。
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基因和环境对于所有的特征是必要的,无论这些特征是遗传的还是获得的(通常受启发的立场),但是在遗传的(生物的,以遗传为基础的)与获得的(以环境为媒介的)特征之间并不存在可理解的(intelligible)区分……一旦消除了在遗传的与获得的之间的区分,那么演化不仅作为两个极点而且甚至是作为一个连续统都不能说是依赖于这个区分了。演化的变化所要求的不是在遗传上编码为与获得性性状相对的东西,而是编码为运行各发展系统:生态学上内嵌的基因组。
莱文汀和奥亚玛是理解这个关键性要点的典范。大体上生物学家并没有以生物学要求的严格性和一致性来彻底思考这一点。其理由当然是:如果我们严肃地采纳生命与世界相互展开的观点,那么一开始就会由于我们认为是确定和稳固的那个基础的崩塌而导致一种眩晕感。我们需要更深地沉浸到这种无根基性的感觉当中,并贯彻其所有的蕴涵,无论它是哲学上的还是经验上的,而不是通过再一次在内在与外在之间制造对立(我们已经知道这不起作用)来扫除这种无根基性的感觉。
我们也应当注意最近以选择的达尔文学说的术语(selective Darwinianterms)来研究神经认知机制的理论。用我们的话来说,这些理论不仅包含(1a),而且在不同程度上论证了(2a)和(3a)。有时候,这些所谓的自然选择理论贯彻了这些要点的内涵从而支持生物体与环境的充分的共蕴含的(coimplicative)性质。例如这种自然选择理论的主要提倡者杰拉尔德·埃德尔曼(Gerald Edelman)在最近的访谈中向采访者表示,“你和世界是一起被植入的”。然而,对于在什么程度上自然选择论者愿意舍弃常常停留在他们着述中的客观主义信念,这并不总是清楚的。
9.5来自作为自然漂移之演化的教益
在前一章里,我们论证了知觉存在于知觉引导的行动,并且我们还论证了认知结构是从循环的感觉运动模式中涌现出来的,这种模式使得行动是知觉引导的。我们把这一观点总结为,认知并不是表征而是具身的行动,以及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并不是给定的,而是通过我们结构耦合的历史生成的。
接着我们提出了对如下形式观点的反驳。这种形式的观点认为,知觉与认知过程涉及对世界的各种最优适应。正是这个反驳,促使我们在这一章里辗转讨论演化生物学。那么,我们能从这些讨论中学到什么呢?
让我们再一次回到我们最喜欢的关于颜色的例子。当我们最后离开这个认知领域时,我们已经看到,存在着各不相同的、不可通约的“颜色空间”:对一些颜色的描述仅需两个维度即可(二维色彩),有些需要三维(三维色彩),而别的却需要四个维度(四维色彩),也许甚至还有五维的(五维色彩)。
每一个不同种类的颜色空间是通过特定的结构耦合历史而生成或出现的。
在这一章里,我们的一个目的是要表明,这样一种独特的耦合历史如何能够从演化这个优势观点获得理解。为这一目标,我们对将演化作为一个(或多或少的)累积适应性过程的适应主义观点提出了批评,并且我们已经清晰地表达了一个将演化作为自然漂移的替代性观点。然后,我们主张,这些独特的耦合历史(不可通约的各种颜色空间正是由其生成的)不应该按照对世界中不同规则的最优适应来加以解释。相反,它们应当被解释为不同的自然漂移历史的结果。进一步的,既然生物体与环境无法分割,二者事实上是在作为自然漂移的演化中被共同决定的,那么我们将其与各种颜色空间相联系的环境规则(比如,表面反射系数)最终必须与动物的知觉导向行为联系在一起时才能得到说明。
让我们从对颜色视觉的比较研究中提供另一个例子。众所周知,蜜蜂是三色视觉,它的光谱感受能力朝向紫外线一方移动。同样众所周知的是花朵在紫外线光照下,有着差别明显的反射系数模式。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前一章提出的“鸡与蛋”的问题:世界(紫外线反射系数)和图像(对紫外线敏感的视觉)哪个在先呢?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许会略有犹豫地回答说是世界(紫外线反射系数)。因此注意到花朵的颜色看起来是与蜜蜂对紫外线敏感的三色视觉共同演化而来的这一点是有趣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共同的演化呢?一方面,花朵通过其食物成分来吸引授粉者,因此它必须既要逗引蜜蜂,又要与众不同。另一方面,蜜蜂从花朵中采集食物,因此需要从远处就辨认花朵。这两个广泛的和互惠的约束看似分享了一个耦合历史,在其中,植物特征和蜜蜂的感觉运动能力得到共同演化。那么,正是这种耦合造成了蜜蜂的紫外线视觉和花朵的紫外线反射系数模式。因此,这种共同演化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子,它说明了为什么环境规则不是给定的而是通过耦合历史生成或出现的。再次引用莱文汀的话: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并不适应某些绝对的自然法则,而是与我们自身的感觉活动所创造的框架中运行的自然法则相适应。我们的神经系统不能让我们看到来自花朵的紫外线反射,但蜜蜂的神经系统却可以。而蝙蝠则能“看到”夜鹰无法看到的东西。我们并不是通过一般性地诉诸所有生命都必须服从的“自然法则”来推进我们对演化的理解。
相反我们必须问一问,在自然法则的普遍约束之内,生物体是如何构建环境的,而这个环境又是生物体进一步演化以及自然重构为新的环境的条件。
这种对生物体与环境的共同决定或相互规定的坚持不应与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观点相混淆,这种观点认为不同的拥有感知的生物体只不过是对世界有着不同的视角(perspective)罢了。该观点仍旧将世界看作是给定的,它仅仅承认这个给定的世界可以从各自有利角度来观看。然而我们所强调的与此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主张生物体与环境以多种方式相互展开,这样,那个构成一个给定生物体的世界的东西就是通过生物体的结构耦合历史生成的。进一步的,这种耦合历史并不通过最优适应,而是通过作为自然漂移的演化而进行的。
将世界作为给定的,并把生物体作为对世界的表征或适应,这是二元论。二元论的极端对立面便是一元论。我们并不提倡一元论,生成是一种介于二元论和一元论的中间道路。一个实质上是一元论体系的例子是由J·J·吉布森及其追随者所提出的“生态学进路”。考察一下我们强调动物与环境共同决定的中间道路与吉布森的进路之间的区别将不无益处。由于这一点的重要性,我们将花几段文字来阐明这些区别,以此给这一节作出结论。
吉布森的理论本质上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个特征与我们对知觉导向行为的进路相容。吉布森主张,在对知觉的研究中,对于世界的描述,必须显示为它是如何为有感知的动物构建环境的。在吉布森看来,在环境光线中发现的某些属性,并不能在物理世界本身那里找到。最重要的属性在于环境对动物的给予,吉布森称其为给予性(affordance)。准确地说,给予性在于环境中的事物所拥有的与动物的感觉运动能力相关的互动的机会。例如,与某些动物有关的一些事物,譬如树木,可以攀爬或是为动物提供攀爬的空间。因此,给予性是世界的显着的生态特征。
第二,吉布森提出了一个独特的知觉理论来解释环境是如何被感知的。
他认为,在环境光线中有充分的信息去直接说明环境,也就是说,无需任何种类的表征(符号的或亚符号的)作为中介。更准确地说,它的基本假设就是,在环境光线的拓扑学中存在不变性(invariance),它直接规定了环境的属性,包括给予性。
这第二个因素——它实际上规定了吉布森式的研究纲领——与我们提出的知觉引导的行动这一进路并不相容。这一点很容易被忽略,因为这两个进路都赞同知觉是知觉引导行动的观点,从而抵制知觉表象主义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