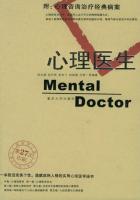海德格尔式的心理分析
一种根本上与弗洛伊德进路或客观关系理论不同的精神病理学观点,是由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路德维希·宾斯瓦格纳(LudwigBinswagner)和梅洛庞蒂在海德格尔哲学的基础上提出的。为了比弗洛伊德所专门分析的歇斯底里和强迫症更一般、更个性地解释心理障碍,与弗洛伊德的表征的、认知主义的和认识论的观点相比,这种解释可以被看作是存在论的。在存在论观点中,性格障碍只要根据一个人整个的在世存在的方式就可以被理解。一个主题,如自卑或优越(dominance),通常不过是个体用以定义其世界的众多维度之一,但却通过早期经验而被固化,以至于成为他在世界中经验自身的唯一的方式。它成了因之物体才被看见的光——光亮本身不能作为物体而被看到——因此就没有与其他在世存在方式进行比较的可能。存在主义心理分析将这类分析延伸到了病理学而非性格障碍,同时它重新描绘了所谓作为存在主义选择的病理学。
然而,病理学的现象学形象(portrait)缺少自己特有的治疗方法,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病人或许试图回忆导致一个主题完整化的最初的事变,并且通过与治疗师的移情而生成和完成这个主题,或经受身体劳作去发现和减缓这个主题的具身姿态——然而,所有这一切也是在弗洛伊德的、对象关系和其他理论方式中所考虑的障碍的治疗特征。
内在于经验的警觉、开放进路的整个人的再具身性(reembodiment)的可能性(我们刚描述过的),或许为存在主义的、具身的心理分析的施行提供了必需的结构和工具。事实上,静心修行、佛教教导与治疗之间的关系,在西方正念/觉知执业者之间是一个充满强烈兴趣又充满巨大争议的主题。
西方意义上的心理分析治疗是历史和文化上独一无二的现象;在传统佛教中,没有明确的相似物。许多西方的静心者(无论他们是否认为自己是佛教徒),要么是临床医学家要么正在考虑成为一个临床医学家,而更多的人都有过治疗的经验。但是,我们又必须提醒读者,我们得放弃在本书中对心理分析所谈到的东西。对于这纷扰的充分讨论会使我们远离主题,但我们要引导读者考虑再具身性的心理分析将采取什么形式。
8.5退回到自然选择
作为对下一章的准备,我们现在打算考虑认知科学中的一个流行观点,它对我们目前已提到的认知观构成了挑战。那么,考虑下面这个对我们讨论的回应:“我愿意承认你们已经证明认知并非仅仅是一种表征,而是依赖于我们行动的具身能力。我也愿意承认,譬如我们对颜色的知觉和分类,与我们知觉引导的活动分不开,并且是由我们历史的结构耦合生成的。然而,这种历史并不仅是任何耦合模式的结果;它很大程度上是生物演化和自然选择机制的结果。因此,我们的知觉和认知具有生存价值(survival value),因此它们必须提供给我们对于世界或多或少的最优适应(optimal fit)。所以,再以颜色为例,正是这种在我们与世界之间的最优适应,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看到的颜色是现在这个样子的。”
我们并不打算将这种观点归于认知科学内的某个特定理论。相反,这个观点差不多在这个领域中的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在视觉研究里,它在马尔和波焦(Poggio)的计算理论,以及吉布森(J.J.Gibson)及其追随者的“直接理论”中很常见。它在哲学的“自然化认识论”方案的几乎各个方面都很普遍。甚至那些持认知的具身和经验进路的人也赞成这种观点。因此,这个观点可以说得上是构成了在认知演化基础的认知科学中“可接受观点”。于是我们就不能忽视这种退回到自然选择的观点。
让我们再次以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颜色研究的案例开始。我们颜色知觉的协同的神经操作机制来自于灵长类种群长期的生物演化。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些运作部分地决定人类共有的基本颜色范畴。范畴的普遍性也许让我们认为它们在某种演化的意义上是最优的,即使它们并不反映某个预先给予的世界。
然而这个结论很大程度上是无根据的。我们可以确实地推断:既然我们的生物遗传一直在继续,我们的颜色范畴就是可行的或有效的。然而,其他物种基于不同的协同神经操作演化出不同的颜色的知觉世界。的确,可以公正地说,人类颜色知觉的神经过程是这个灵长类种群所特有的。大多数脊椎动物(鱼类、两栖动物、鸟类)有着非常不同的复杂的颜色视觉机制。
昆虫类则演化出与其复眼相关的极为不同的构造。
进行这种比较研究的一个最为有趣的方式就是通过比较颜色视觉的维度。我们的颜色视觉是三色的(trichromatic):正如我们已看到的,我们的视觉系统是由三种类型与三个颜色通道交叉联结的光感受器组成。因此,需要三个维度(即我们能作出的颜色区分的种类)来表征我们的颜色视觉。当然三色性不是人类独有的;的确,似乎差不多每种动物类都包括一些具有三色视觉的物种。然而,更有趣的是,一些动物是二色视觉,而另一些动物则是四色视觉,甚至也许有五色视觉(二色视觉包括松鼠、兔子、树鼩、一些鱼类,可能还有些猫以及一些新世界(New World)的猴子;三色视觉有像金鱼这样生活在近水面的鱼类,像鸽子和鸭子这些昼行的鸟类;昼行的鸟类也可能是四色视觉)。而要表征二色视觉需要二个维度,四色视觉需要四个维度,五色视觉则要五个维度。特别有趣的是四色视觉的(也许是五色视觉的)鸟类,它们的神经操作机制似乎与我们迥异。
当人们听到这个关于四色色彩的证据时,他们的反应是问,“这些动物所看到的其他颜色又是什么呢?”若这个问题是在说四色视觉者在看我们所看到的颜色时比我们看得更好,那么这个问题是可理解的但却有些天真。
必须记住,尽管四维颜色空间与三维颜色空间有着根本上的差别:严格说,这两个颜色空间是不可通约的,因为没有办法把四维颜色空间所有可能的区分种类毫无遗漏地映射到三维颜色空间所有可能的区分种类上。当然,我们能够对于这些更高维度的颜色空间的可能是什么样子有一个类比的看法。例如,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颜色空间包含一个额外的时间维度。这个类比中,颜色会在第四维度按比例进行不同程度的闪烁。因此,例如使用粉红色作为在这种四维颜色空间的指示,将并不足以选出一个单一的颜色:他可能不得不说快速粉红色(rapid‐pink),等等。如果说白天活动的鸟类的颜色空间是五色视觉的(这的确有可能),那么要我们去想象它们的颜色经验会是怎么样的,这肯定是失败的。
那么现在应该很明显:鸟类、鱼类、昆虫和灵长类动物的广为不同的结构耦合的历史,已生成对颜色世界不同的知觉。因此,我们知觉的颜色世界不能被看作是对演化提出的某些问题的最优“解决”。确切地说,我们知觉的颜色世界是许多其他路径中一条可能的和可行的种系发生的路径,它是在生物演化历史中实现的。
再次,对代表认知科学中的“已接受的演化观点”的回应将是:“很好,既然存在如此多样的颜色知觉世界,那么让我们承认颜色作为我们知觉世界的一个属性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最优适应。因此,颜色知觉的不同的神经机制不是对相同演化所提出问题的不同的解决方法。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我们的分析必须做得更加精细。这些不同的颜色知觉世界反映了对不同的生态小生境的不同的适应形式。每个动物群体以最优方式使用世界的不同规则。这仍然是一个最优适应世界的问题;只不过每个动物群体都有它们自身的最优适应。”
这个回应仍然是一个更加精致的演化论证形式。尽管优化根据所谈的物种而不同,但观点仍然是知觉和认知任务涉及对世界的某个优化适应形式。这种观点代表了一种精深的新实在论,它把优化作为其中心解释工具。
因此若不在演化解释背景下更细致地审视这个观点,那么我们就无法进一步继续下去。我们不能试图去总结演化生物学当今的艺术(art)状况,但我们有必要去探究它的一些经典基础及其现代的替代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