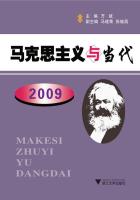中国历史上一些失意的士大夫,很少皈依宗教,而是隐居山林田园,痴迷于艺术-审美活动。即使有的人皈依了佛教,也是中国的佛教,追求当下自我人格的自由,与现实的艺术-审美境界相沟通,而与印度佛教寄希望于“轮回来世”和西方基督教寄希望于“彼岸”、“天堂”不同。由此,具有审美意味的诗性主体的建设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重要命题之一。它在人、自然、社会、宇宙的关系中主张的是和谐而不是对立。这种精神追求,这种发展趋向,在中国学术、教育的奠基时期——先秦时代已经牢固地确定下来。孔子云“从心所欲,不逾矩”。庄子主张“物我两忘”而“道通为一”。禅宗则倡扬“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这种种既现实而又艺术化的伦理与心性之学,在中国传统艺术中演化为“静照”、“妙悟”等把握方式,也成为人生与艺术相融通的诗性渠道。
中国现代美学也传承发扬了这种诗性情怀。现代美学家们融会中西现代思想、理论和方法转化中国古代艺术-审美境界,重构现代的人生理想与精神品格。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以出世来入世的“人生艺术化”思想与学说。“人生艺术化”非以艺术来出世、游世或厌世,而是要求以艺术精神来塑造生命提升人格,超越小我达成大化,追求生命过程的非功利性和生命意义的诗意性。“人生艺术化”思想初萌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最早田汉、宗白华有相近似的表述,但当时缺乏系统深入丰满的阐释,影响不大。20年代初,梁启超提出了“生活的艺术化”口号,并以“趣味主义”精神来诠释,从根本上奠定了“人生艺术化”命题的核心精神。梁启超指出“生活的艺术化”就是“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他强调,在这种“趣味化艺术化”的境界中,实践主体由情而动,有真性情,有大情怀,将小我之兴味与众生、宇宙之运化相融通,最终超越小我之成败得失而达致生命创化之“春意”。梁启超的“趣味主义”哲学和“生活的艺术化”
的思想明确开启了融情感、哲思、意趣为一体的艺术化生活的实践方向。
朱光潜是“人生艺术化”理论的积极倡导者之一。30年代,经过他的诠释与积极倡导,“人生的艺术化”成为一个具有相对确定内涵的命题,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朱光潜提出了“出世”与“入世”的关系问题,主张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以“无所为而为”的艺术精神来涵养人生的理想与情趣。30至40年代,宗白华一往情深于艺术和美的体悟与诠释。他将“意境”的范畴纳入到人与世界的整体关系格局中,提升到人生观、宇宙观的形上层面予以诠释。在中国审美与艺术史上,宗白华第一次深刻地窥见了艺术意境的生命底蕴与诗性本真。他指出意境的底蕴就在于“天地诗心”和“宇宙诗心”,它有直观感相、活跃生命、最高灵境三个层次,也就是从“情”到“气”到“格”,从“写实”到“传神”到“妙悟”。飞动的生命和深沉的观照的统一,至动和韵律的和谐,缠绵悱恻和超旷空灵的迹化,成就了最活跃最深沉、最丰沛最空灵的自由生命境界,使每一个具体的生命都可以通向最高的天地诗心,自由诗意地翔舞。由此,宗白华的意境论不仅是对中国艺术精神的深刻发掘,也是对诗意的审美人格和诗性的审美人生的现代标举,它不仅强调了超越与自由的纬度,也强调了至动而有韵律的生命之美。宗白华的思想学说与成就是中国现代美学诗性精神绽放的颠峰之一。
中国现代美学的这种诗性精神既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审美精神,也来源于西方现代美学的传统,如康德美学的审美无利害性思想与价值论视角,尼采美学的艺术形而上学精神,德国浪漫派美学人生与诗合一的主张等。中国现代美学面对民族的苦难与文化的危局,升华出美与艺术的诗意,主张超越的人生品格与积极的生命精神。这种诗性的光芒在整体上表现为一种情感的深沉、一种生命意义的大气与坚守,从而也构筑了中国现代美学诗性精神的独特品格。梁启超、朱光潜、丰子恺、宗白华等都强调个体生命、群体社会、宇宙大化三者的融合,强调个体生命境界的诗意提升与整体升华。这种精神意向也使得他们对美的理解与阐释常常体现出大气而灵动的特点。如梁启超对中国古典作家的鉴赏就侧重于作家的精神气度与人格魅力,他把杜甫誉为“情圣”,以“All or nothing”为屈原精神的神髓;宗白华对中国传统艺术的赏析则以民族精神、时空意识、生命情调、艺术意境等为中心,着意于体味民族心灵的高旷灵逸。在对现实生存与个体生命的关怀中,这些现代美学家呈现出对人生终极理想与生命至高意义的苦苦思索与追寻,并在现实的艺术-审美的诗性境界中找到了自己的答案。正如宗白华所言:“我们任何一种生活都可以过,因为我们可以由自己给予它深沉永久的意义。”(宗白华《歌德之人生启示》)
此外,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是中国现代美学留给我们的重要精神财富之一。
中国现代美学孕生于民族苦难、文化落后、民众麻木的历史背景中,对于那些先驱者与建设者们来说,这不仅是美学思想、意识、学科自身发展的历史,也必然是为时代大潮所激荡的文化更新史、思想更新史。启蒙、反思、批判,这样一些新的理性精神,在中国现代美学的诸多思想家身上,都可真切地感受到。
20年代,梁启超抗着“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旗帜最早向温柔敦厚、中和内敛的传统审美意识发起冲击,他批评中国的诗教总以“含蓄蕴藉”为文学的正宗,对于中国文学史上“以‘多愁多病’为美人模范”的病态审美理念给予了辛辣的嘲讽。情感与个性的解放成为梁启超艺术与审美的两大基本准则,是对中国封建文化长期以来钳制人性压抑生命的批判。
写于1932年的《谈美》是朱光潜的成名之作。在《开场话》中,朱光潜提出谈美在当时的中国是“太紧迫”了,因为中国人急需“免俗”。谈美就是对那些“俗人”与“伪君子”的批判与警醒。40年代,宗白华深情地呼唤“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哪里去”?他说“中国民族很早发现了宇宙旋律及生命节奏的秘密,以和平的音乐的心境爱护现实,美化现实,轻视科学工艺征服自然的权力。这使我们不能解救贫弱的地位,在生存竞争剧烈的时代,受人侵略,受人欺侮,文化的美丽精神也不能长保了,灵魂里粗野了,卑鄙了,怯懦了,我们也现实得不近情理了。我们丧尽了生活里旋律的美(盲动而无秩序)、音乐的境界(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猜忌、斗争)。一个最尊重乐教、最了解音乐价值的民族没有了音乐。这就是说没有了国魂,没有了构成生命意义、文化意义的高等价值”(宗白华《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