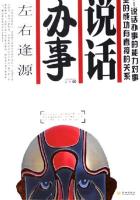终于,上面开始“说”了。
姐姐说,先去的两家果然是赵老师家和王强家。是私下里去各家里说的,大家不好跟着去听,只能事后打探。赵老师对大家说,无非还是说盖的是违章建筑,决不会赔一分钱,早拆早好之类的废话。赵老师给他们看林权证,他们果然说这张林权证早就过时了,没有任何用处。问那些人态度怎么样,赵老师笑答:“来我家了,他还敢怎么样?有理说理呗。咱还怕他们说理?”
到了王强那里,就没有这些细节了。只有一句接一句简单的话。
“就拆。”
“就是叫拆。”
“还是叫拆。”
不过他每次的表态已经有了微妙的不同。最开始是:“说到天边不赔钱就不会给他们拆,这是死章程。谁说啥都白搭。”
后来就是:“不太好扛。还牵着我哥呢。”
然后是:“有点儿扛不住。”
最近的一次是:“不好扛。真不好扛。”
“你说,他说这些个话,是不是不太妙?”姐姐的担忧顺着话筒传过来,“他要是倒了,该咋办?”
当然不妙。很不妙。看来我最担心的状况很可能就要出现了:王强正在被招安,正在准备当叛徒。这些话就是一条条青石,正在为他退下梁山铺成一级级台阶。
但是,能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办法。在我这里,我想不出什么办法。
“不敢想,想想真害怕。”姐姐又说。
“不要紧。”我安慰惶恐中的姐姐,我知道我只能这么说,“走一步说一步,总会有办法的。”
又是周六,我早早地醒了,打开手机,一边想着要不要到张庄去。——自从参与到姐姐家的盖拆事件中来,我就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一到周末,只要没有什么要紧事,我就想去张庄看看。每到此时,老公就会奚落我:“不就是9万块钱吗?值得那么紧张吗?”我回敬说:“请忘记9万块钱的钱数,记住320平米的面积数。本人有史以来还从没有进行过如此大面积的房地产投资。”
正在洗漱,手机响了,我飞奔回卧室接听,正是姐姐,她的声音听起来都有些变调了:“快!快来!大吊车来了!”
“什么大吊车?”
“吊水泥板的大吊车啊。在王强家门口站着呢。要拆王强家的房子了!”
我以最快的速度将必要的洗漱工作和进出口事宜进行完毕,便下楼驱车。还好,7点半,这个点儿的郑州市还不够堵。8点35分,我到达张庄。远远的,我就看见一辆黄色的大吊车在王强家门口站立着。它周边围着一群人。我放慢车速,粗略地看了看,不,是三群人:一群人穿着制服,是公家人。有公安的,司法的,国土局的,城管的。另一群人基本都是我熟悉的那些脸,这群人又分成了两小群,男人一群,女人一群。男人们都是默默地站立着,姐夫、刘低保、赵老师兄弟都在里面。女人们则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着什么。姐姐也在。她除了和旁边的姨妈说话就是看自己的手机——肯定是在等我的电话。她没有看见我的车。还有一群人,算是第三群人,我数了数,有六个,他们手里都拿着镐,看样子也像农民。
没有王强。
本来想把车就势停下,但犹豫了片刻之后,我还是让车远离了人群。我把车开到姐姐家门口,慢慢地走了过来。我是溜着路边走的,尽量不想让别人注意。——我这样一个人,站在姐姐那群人中,肯定会扎眼。
我不想让自己显得扎眼。
怎么才能不扎眼呢?
更深的问题是:我怎么就那么怕在他们中间显得扎眼呢?
在离王强家隔着两户的地方,我站定,打通了姐姐的电话,告诉她我已经到了,在旁边看着呢。
“那咋不过来?”
“看着就行。能看清。”我道。这当然不是能否看清的问题,但轻易地置换概念,这是我的一贯伎俩。
慢慢的,我靠近着。越来越近。没有人注意我。
“上吧,愣着干啥呢。”制服帮的一个人朝着第三群人发话了。那人黑胖,声音很低。但所有的人,我相信,都听到了。第三群人互相看了看,一个年龄大些的矮个子拿着镐,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对其他几个笑了笑,道:“那,来吧。”
他们朝着王强家的房子走去。没走几步——本来离得也就很近——就被护房帮的人给拦住了。男人们没有上,是女人们。女人们伸出手,轻轻地向外推着这几个人,一边推一边凌乱地说着:
“干啥呢你们?想干啥?”
“能轮到你们来拆房?你们敢来拆这个房?”
“人家给了你们多少钱你们就敢来拆这个房?”
“这个钱你们也好意思挣?真是昧良心!”
……
被指责的这几个毫无抵抗的意识,很快就退了回来。他们边往外退边讪讪地笑着,一句话都没有。转眼之间,他们就退到了原地,然后他们一起看着制服帮里那个黑胖的人,似乎是在征求他的意见。但是,黑胖制服没有看他们。他沉默着。制服帮的人全都沉默着。不时有人会离开人群去接打手机,一会儿就再回到他们的群中,接着沉默。完全没有我想象中的双方火并的暴烈场面。
怎么就这么沉默呢?
过了很久,大约有一个多小时的样子,从东边开过来一辆黑色的奥迪A6,从车上下来几个人。一个穿着深蓝色夹克的中年男人下得车来,在车边略站了站,似乎是在看什么,可也不知道他在看什么,有点儿茫然四顾的神情。之后,他走过来。制服帮的人给他闪出一条罅隙,他顺着那条罅隙来到制服帮的最前面,问黑胖制服:“王强呢?”
那个人朝王强的房子扬了扬下巴。
“叫他出来。”蓝夹克的口气不容置疑。
黑胖制服离开人群,对着手机讲了一通,一会儿,王强走了出来。他的神色很平静。他径直朝着蓝夹克走了过去,口中叫着什么主任,伸出了手。两个人都没有笑,就那么冷着脸握了握手。蓝夹克马上指着护房帮的这一群人道:“这是弄啥呢。”是责怪的口气,但是又略带一丝丝暧昧的亲昵。这亲昵不仔细听,是听不出来的。
王强摊开双手,做了个很西式的耸肩动作,道:“没办法,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人群静默。全都听着这两个人的对话。在这种氛围里对话是很有些怪异的。蓝夹克看了护房帮的人们一眼,咳了两声,上前一步,终于开口了:“乡亲们,按照政策,这房子就是违章建筑,必须无条件……”
“呸!按你说的,这全村人的房子都不合政策!你们把俺全村都拆了吧!”
“就是!满口说审批审批,你们上头盖房的时候都审批了?同仁医院的地为啥荒了五六年?”
“光会欺负老百姓!”
“当时盖的时候,你们咋不吭?房子盖好了,你们来叫拆了?”
“啥违章?俺们不知道啥是违章!俺们盖的时候你们不说俺们就觉得那不违章!”
……
沉默终于被打破。人声鼎沸。都是女人们的尖利叫嚷。姨妈的声音也在其中,历历可辨。苍老,嘶哑,愤怒。唾沫横飞的同时还不时搭配上指手画脚的花哨动作。如果一定要找一个词来形容一下此时的她老人家,那不孝的我就只能找到那个不敬的词:泼妇。但是,她的泼让我很欣慰。这个时候,就是需要这样的泼吧?我想起她曾经给我讲过她刚当新媳妇的时候和婆婆对骂的事:婆婆为了给她一个下马威,经常恶骂她“你个小×”,她忍了一段时日终于忍无可忍,就毫不客气地回敬她:“你个老×!”
再看看姐姐,她不行。不要说泼了,她根本就没有开口。就是在那里僵站着,似乎丧失了语言功能。我有点儿急:她怎么就那么安静呢?怎么就不开口呢?
作为制服帮此时的核心,面对着喧嚣的人群,蓝夹克一直表现得很平静,显然是见惯了这样的场面,心理素质很好。他任人们吵着,一声不响。在一个低潮期的时候,他不失时机地伸出双手往下压了压,仿佛在拍打两个篮球,又仿佛一个红歌星在优雅地制止粉丝们如潮的掌声。等到叫嚷声静下来,他便开口道:“乡亲们,冷静,冷静。咱们有话好好说。你们家的厨房都有菜刀吧?”
这话蹊跷。大家互相看看,都沉默了。等待着他下面的话。
“你们都知道菜刀是用来切菜的,不是用来杀人的吧?你们都知道拿着刀杀人不对吧?”他突然提高了嗓门,“这是不用说就知道的道理!所以,这房子,我们不管你们也应该知道不该盖!不该盖的盖起来了就应该拆!”
真是逻辑严密啊,字字铿锵啊,声震云霄啊。蓝夹克慢条斯理地环顾着人群,似乎很为自己语言的精彩而得意。又仿佛是在挑战,看谁敢出来跟他雄辩。
“你比方得不对!”突然,我伟大的姨妈跳了出来。
“咋不对?”蓝夹克微笑着说。
“应该比方说:怀孩子的时候你不管,现在孩子生出来了,成了一条命了,你们却来杀人?你们要杀人家的孩子?嗯?你们不是杀人犯?嗯?”
一瞬间,蓝夹克脸色紫涨,张口结舌。
“对,就是这个理儿!”护房帮们喝彩。
“不审批的房子都得拆?北京故宫当时盖的时候你们审批了没有?你们咋不去拆故宫?!嗯?”我伟大的姨妈继续伟大。
“在路!说得在路!”护房帮们继续喝彩——“在路”是豫北方言,相当于靠谱。
蓝夹克再也说不出话来。此刻,他的手机突然响了。他一边接着手机一边钻进了奥迪车,扬长而去。不一会儿,其他的制服们便也散了。持镐的那几个人也随之散去,只留下那辆巨大的吊车呆呆地伫立在王强家门前。
看着制服帮远去,护房帮的人们顿时喜笑颜开,还有几个人鼓了几下掌,颇有些胜利的喜悦。由赵老师发起,大家当即又聚在一起开了个闹哄哄的现场会,说了半天其实只确认了一点:无论如何,要齐心协力先保护好王强家的房子。
“大家要知道,王强家的房子,现在不是王强家的房子,是我们每一家的房子。”赵老师很有哲理地说,又把脸转向王强,“强,你可千万不能松劲儿啊。”
“强,你是头道关,无论如何不能下软蛋!”刘低保跟着说。
“知道。”王强点点头。
最后,赵老师还特别表扬了一下在关键时刻立下重大功劳的姨妈。智勇双全的姨妈却很快为这份表扬付出了代价:她的高血压又犯了,下午便又开始挂点滴。
战事稍平,但我心里却格外不安。安顿好姨妈,我便又去找赵老师,问他:王永呢?王永在做什么呢?和上头的直接冲突已经开始,这还不是刀刃上吗?如果这还不是刀刃,那到底什么时候才是刀刃呢?
“我也问他了,他说正说着呢。说说看吧。”赵老师道,“王永肯定会用劲儿说的,你放心。”
可我怎么能放心呢?“正说着呢。说说看吧。”这话是如此中立,不带任何潜台词:消极的和积极的,都没有。简直就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说辞。或者说,它的无意义中又有着太多的意义。这样的话,我无法放心。但赵老师却是一副笃定的样子,似乎有王强在前面顶着,他就有理由笃定。我突然想起空调的叫法:一拖二,或者一拖三。在这里,是一拖十五。拖得动吗?我知道,如果我信,我就又犯了天真幼稚病。一旦犯病就得吃药。那药往往会很苦。当然,我也得承认:那病犯起来的时候,确实也比较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