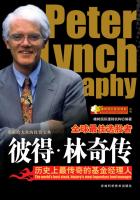闻一多比华罗庚大11岁,早在清华园时两人就有了交往。当时,许多青年人都被闻一多的诗所感动,华罗庚也不例外。他读过闻一多的《死水》,诗中把旧中国比作“一沟绝望的死水”。闻一多的《心跳》更引起华罗庚的共鸣,他最喜欢诗中的这样两句:谁稀罕你这墙内方尺的和平!
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
寄居昆明后,华罗庚与闻一多的交往更为密切。他们常和吴晗、楚图南、王时风等人一起,议论国家大事,抒发个人情怀。在朋友们的影响下,华罗庚开始阅读《联共(布)党史简要读本》、《反杜林论》等书籍,并对国民党摧残民主运动的暴行感到痛心疾首。
一天,华罗庚悄悄地对王时风说:“我想离开昆明,到延安去。”“眼前的黑暗早晚有一天会结束的,你的腿不行,还是搞你的数学,将来数学会有用的。”王时风劝他说。
华罗庚也把内心的苦闷倾吐给闻一多,闻一多告诉他:有志向的中国人哪个不苦闷?哪个不愤怒?许多知识分子已对国民党的统治感到失望,反独裁、反内战、反饥饿是大家的共同心声。中国此时需要的是置生命于度外的民主战士!
1938年,在日本飞机的一次大轰炸中,闻一多头部受伤,一个多月后才逐渐痊愈。1940年的夏天,日机的一颗炸弹又落在闻一多家的后院,幸亏是个“哑弹”,才未造成伤亡。事情发生之后,闻一多一家就搬到乡下的陈家营。在此期间,华罗庚一家也曾来这里避难,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处,闻一多就热情地把自己的房子让出一些地方。这样,两家人曾一度同居一室。
闻一多居住的房子是个土木结构的二层小楼,楼下是灶房和牲口圈,闻一多一家八口住在二楼的厢房和正房里,本来已经相当拥挤,但还是把稍大的一间正房腾出来让华罗庚这六口之家住下。由于两间正房当中没有隔墙,他们就用床单拉条布挡,华家住在里间,闻家住在外间,华家的人去自己的房间必须经过闻家的卧室。
两家住在一起,关系甚为融洽,时常谈谈彼此的见闻。一到晚上,都点着小油灯,苦读夜战。华罗庚忙于钻研数学,闻一多则陶醉于古书的纸香之中,正在撰写他的《伏羲考》。闻一多还常常鼓励自己的孩子们说:“你们应向华先生那样勤奋用功,认真读书,将来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
在这段日子里,李公朴经常到闻一多家商量民盟的工作,在闻一多的介绍下,李公朴与华罗庚也熟识起来,并且成为挚友。李公朴的故乡常州,与金坛仅一县之隔,二人亦称同乡。李公朴的夫人张曼筠后来也回 忆说:“他们如亲兄弟一般。公朴亦常常谈到罗庚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爱国者,一身正气,疾恶如仇,对当时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恨之入骨。”
华罗庚与闻一多同住一室的事情,在西南联大被传为佳话。为了纪念这段生活,华罗庚后来写下了这样四句诗: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1941年10月,联大文学院另找了房子,闻一多一家就先搬走了。虽然见面的机会少了,但友谊依旧。
1944年夏天,为了糊口,闻一多又增添了一门工作———刻制印章。闻一多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位秀才,对雕刻和图章都有研究,并影响了闻一多。当“闻一多治印”的招牌刚刚打出时,一位好心的同事为他写了这样一则启事: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源始,海内推崇。
没想到,刚一开张,便顾客盈门。但闻一多把握一条原则:决不为那些腐败堕落的官僚治印。据说有位官员为得到闻一多的印章,曾派人送来象牙,而闻一多毅然回拒。
在营业之余,闻一多反复构思、精工镌刻了一枚别致的图章,送给华罗庚,图章上刻着这样几行小字: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碜,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
在后来的辗转迁徙中,华罗庚一直珍藏着这枚印章。他常常说,这不是普普通通的印章,而是他们之间患难与共的凭证,也是他们那种崇高友情的凝聚。
1944年,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晚会上,闻一多这位有正义感与爱国心的知识分子,面对着反动势力的威胁,毫不畏惧地站了出来,支持进步青年,在西南联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此,他已经由一位诗人变成了民主斗士。事后,他曾激动地和华罗庚谈起自己的想法:“有人说,我变得偏激了,甚至说我参加民主运动是因为穷疯了。可是,这些年我们不是亲眼看到国家糟到这步田地,人民生活得这样困苦!我们难道连这点正义感也不该有?我们不主持正义,便是无耻,自私!
“要不是这些年颠沛流离,我们哪能了解这么多民间疾苦!哪能了解到国民党这样腐败不堪!”
1944年夏天,在七七事变纪念日的前夕,中共地下党组织在云南大学汇泽堂举行抗战七周年时事报告会,从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觉,他们派人千方百计阻挠集会,三四千人的会场竟然不让装扩音设备。会前,云南大学的训导长宣布:会上只准谈学术,不准谈政治。身为云大校长的熊庆来也奉命作了冗长的发言,他远离会议的宗旨,大谈教学的重要。并说“变”是不对的,“变”只会带来大乱等等。
面对这种情况,闻一多实在坐不住了。“主席,请允许我讲几句话!”会场上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闻一多慷慨激昂地讲道:“今晚演讲的先生,我们都是老同事、老朋友,可是既然意见不同,我还是要提出来讨论讨论。“有人不喜欢这个会议,不赞同谈论政治,据说,那不是我们教书人的事。国家糟到这步田地,我们再不出来说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管,还有谁管?”
接着,闻一多用“学生要管事”的论点驳斥了“学生要念书”的论点,引起了全场轰动。
事情发生后,华罗庚指出了熊庆来的错误,熊庆来很抱歉地说:“是训导长让我去的,我上了特务的当,我不该去,你见到一多,帮我解释一下。”
当华罗庚把熊庆来的话转达给闻一多时,闻一多表示理解熊校长的处境,他很释然地说:“当时,他也不得不这样啊!自然,我的话也太锋利了一些。”
这年9月,闻一多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
1946年春,华罗庚接到了访苏的邀请,而此时的昆明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境地,内战的阴云已越积越厚。李公朴、闻一多等人已成了国民党统治者的眼中钉,特务们还扬言要以“40万美元的重金,收买闻一多的头”。
“一多兄,情况这么紧张,你可要多加小心才是!”忧心忡忡的华罗庚对闻一多说。
“要斗争就会有人倒下去,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就会站起来!形势越紧张,我越应该把责任担当起来。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难道我们还不如古时候的文人?”闻一多倒显得从容不迫。
华罗庚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次谈话竟然成了他们的诀别,国民党反动势力在暗杀李公朴之后,又向闻一多伸来了魔爪。
闻一多遇害之时,华罗庚不在昆明,他是在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上得到噩耗的。当时,他手里拿着报纸,泪水不断涌出。望着窗外灰蒙蒙的田野,怎么也不能相信自己深深敬仰、有患难之交的这位师友已经永远离开了他。华罗庚从内心深处涌出这样的诗句:乌云低垂泊清波,红烛光芒射斗牛,宁沪道上闻噩耗,魔掌竟敢杀一多。
闻一多遇难之时,他的长子闻立鹤为了保护父亲也受了伤。还在昆明的吴筱元不断去医院探望立鹤,并安慰闻夫人,以聊友情。后来,华顺还认了闻夫人为干妈,两家情意愈浓。
30年后,华罗庚在纪念闻一多的文章中写道:“闻一多的死,和我的出走,形成一显明的对照。作为一多先生的朋友,我始终感到汗颜愧疚,在最黑暗的时刻,我没有像他一样挺身而出,用生命换取光明!但是,现在我又感到宽慰,可以用我的余生,完成一多先生和无数前辈未竟之事业。”写到这里,他赋诗表达了自己的怀念之情:闻君慷慨拍案起,愧我庸懦远避魔。后觉只能补前咎,为报先烈献白头。白头献给现代化,民不康阜誓不休。
为党随处可埋骨,哪管江海与荒丘。
4.《访苏三月记》
1946年,苏联科学院将用英文出版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一书,并邀请华罗庚访苏。2月25日,他从昆明乘机出发,途经加尔各答、卡拉奇、巴士拉、德黑兰,3月19日才到达苏联的巴库,后由巴库转机,经过斯大林格勒,于3月20日抵达莫斯科。长达一个月的路途颠簸,使华罗庚心情烦躁,深感辛苦。滞留于巴格达时,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我欲高飞云满天,我欲远走水溢川,茫然四顾拔剑起,霜华直指霄汉间。
在苏联,经过短暂的访问之后,华罗庚于5月12日由巴库乘飞机离开苏联,25日返回昆明,时间正好三个月。1947年,《时与文》杂志上连续刊载了华罗庚长达3万字的日记,题为《访苏三月记》,详细地记载了他的所见、所闻、所感。
访苏期间,最令他难忘的事情便是与苏联科学家的会晤。
在维诺格拉朵夫家,这位著名的数学家与华罗庚促膝相谈,并对华罗庚的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赞誉。他请华罗庚用中文题写书名,华罗庚当场挥笔,除书名外,还写下了“谨以此书祝中苏邦交永笃”一行字。维诺格拉朵夫还在家中招待华罗庚,午饭从一点半吃到五点半。
在庞特里雅金家,华罗庚目睹了这位盲人学者如何克服困难、献身科学。在国内时,华罗庚久闻庞氏大名,并曾用庞氏的《连续群》作为授课教材。可他并不知道,这位盲人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他的母亲抄写成文 的。华罗庚自然很敬重这位母亲,便问道:“你给了你的儿子不少的帮助,那你对数学一定很有研究了。”
“不,我对数学,就像对中文一样陌生,我只是力所能及地帮帮他。”庞氏的母亲很谦虚地答道。
在和舍盖尔的会谈中,对方告诉华罗庚说,华氏的每一种数学方法都极为准确、精密,令他十分佩服。早在苏德战争前,他已着手翻译《堆垒素数论》,战争爆发后,他因参战而停止翻译,由另一位教授巴谢列柯夫继续翻译。舍盖尔还说,他在莫斯科大学的数论课上,讲授了华罗庚的“中值定理”,使学生们大开眼界。
在此期间,华罗庚先后作了《矩形几何学》、《自守函数学》、《多个复变数函数论》等学术报告。介绍了他自己在1942年至1946年的研究成果,受到了苏联数学界的普遍好评。
在苏联所看到的一切,都会勾起他对祖国命运的担忧。当苏联人民载歌载舞,在五彩缤纷的气氛中欢庆五一节时,他在心里说道:“苦难的中国人民,何时才能脱离苦海?古老的国土何时才能焕发青春?”当他看到苏联数千名中学生踊跃参加数学竞赛,著名数学家利用节 假日到处做演讲的情景时,他从内心祈祷着:中国不能再轻视数学、轻视科学了!格鲁吉亚共和国教育部长库柏拉齐的一句话像警钟一样老是在华罗庚的耳边回响:“只有头脑受过数学训练的人,将来才有出息。数学是科学之母,一个国家如果数学不发达,其他什么也谈不上!”
当时,几位苏联科学家还提出让华罗庚延长访问时间,以便为他治好腿疾。华罗庚转问医生:“能不能治好?”“应该能。”医生点点头。“需要多少钱?”“要钱吗?”医生诧异。
“你是说不要钱?”这回该华罗庚惊奇了。他的苏联朋友们听了他们的对话,都会心地笑了。由于华罗庚应邀访美,所以就谢绝了为他治病的盛情。
华罗庚是我国第一位受苏联邀请的学者,这次成功的访问,在国内政界与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自豪地对华罗庚说:“我驻莫斯科这么多年,苏联政府从未请我吃过饭。你一来,我可沾光不少,参加了这么多宴会。你真为中国人争了光,为我们的民族争了气!”傅秉常大使在华罗庚归国前,还拍电给沿途各领事馆,称华罗庚为“国宝”,要求他们严加保护,隆重款待。华罗庚也开玩笑:“ 现在我是处于‘ 奇货可居’的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