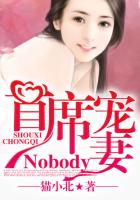调号标在哪里,也是有争论的。标在音节末尾可以区别音节,但是过于松散。标在元音字母上面,能表示声调基本上是元音的音高变化。但是,“iu”“ui”标在哪一个字母上面好呢?这个问题,方案委员会没有做出决定。现在标在后一字母上面,已经成为习惯,这是群众的约定。
方案规定了字母名称,但是没有认真推行。注音字母的名称事实上代替了拼音字母的名称。近来又有用英文字母名称代替的趋势。这是一个先入为主的习惯问题。
问题很多,不能细谈。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改掉一个缺点往往会产生另一个缺点。缺点和优点是共生的。只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
汉语的字母方案一百多年来的演变历程是:从外国方案(威妥玛式)到本国方案(注音字母),从民族形式(注音字母)到国际形式(国语罗马字),从内外不同(国内用注音字母,国外用威妥玛式)到内外一致(国内国外都用汉语拼音),从国家标准(国语罗马字、汉语拼音)到国际标准(汉语拼音:ISO-7098)。
四十年来的经验表明,汉语拼音方案是一座现代化的文化桥梁。它一方面方便人民大众走向文化,另一方面方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我和语文现代化
我对语言学和文字学是外行,我参加文字改革工作是偶然。我的孙女儿在小学时候对我说:“爷爷,你亏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文改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是一个○。”这就是我的写照。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我从国外回来,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书,院系调整后在上海财政经济学院教书。一九五五年接到通知,要我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我被留在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我说我对语文是外行。领导说这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我服从分配,就此改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我业余写过几篇有关语文的文章,提出一些幼稚的所谓新观点;三十年代,我业余参加拉丁化运动,写过一些有关改进拉丁化的文章。这就是我被留下在文改会工作的缘故。
“二战”后,新独立一百多个国家,都有语文建设问题,有的需要规定国家共同语,有的需要设计国家通用文字。文明古国也要更新语文,例如日本战后实行语文平民化,印度制定国家共同语和邦用共同语。国外兴起一门新的学问,叫作“语言计划”,这跟中国的“文字改革”名异而实同。“文字改革”包括语言问题,“语言计划”包括文字问题。文字改革或语言计划,又称“语文现代化”。
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
解放初期,政府以扫除文盲作为建设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在“突击识字”等方法失败以后,把希望寄托于文字改革。
中国的文字改革开始于清末,内容逐步发展,前后包括:一、语言的共同化;二、文体的口语化;三、文字的简便化;四、注音的字母化;五、语文的电脑化;六、术语的国际化。五十年代提出三项文字改革的当前任务:一、简化汉字;二、推广普通话;三、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参看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周恩来总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
一九五五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把国语改称为普通话,给普通话定义为“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会后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我是委员之一。我提出“普及”普通话的两项标准:一、全国学校以普通话为校园语言;二、全国公共活动以普通话为交际媒介。
起初,“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设计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在一九五五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展示四种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草案,没有得到语文界的积极响应。于是在文改会下面成立“拼音方案委员会”进一步研究制订方案。一九一八年公布的“注音字母”(后改称“注音符号”)不便国际交流;一九一八年公布的“国语罗马字”拼写法太烦琐,难于推广。于是决定研究制订更加适用的汉语拼音方案。
“拼音方案委员会”详细研究了方案的原则和技术问题,包括:一、字母形式问题(民族形式和国际形式;译音方案和文字方案等);二、语音标准问题(人为标准和自然标准;方言和普通话的对比等);三、音节拼写法问题(双拼和音素化;字母标调和符号标调等);四、字母的具体安排问题(声母“基欺希”的安排;舌尖前后元音的安排;双字母的减少;新字母的取舍等)。
为了给字母形式问题提供参考,我写了一本小书《字母的故事》,先分篇发表在《语文知识》杂志上,后来出版单行本。我提出“汉语拼音三原则”:一、拉丁化;二、音素化;三、口语化。并从反面阐明汉语拼音方案有“三不是”:一、不是汉字拼音方案,而是汉语拼音方案;二、不是方言拼音方案,而是普通话拼音方案;三、不是文言拼音方案,而是白话拼音方案。这些论点,我写成文章发表在香港《语文杂志》和其他刊物。
汉语拼音方案经过三年的反复研究方才完成。当时从原则问题到技术问题,都经过十分慎重的考虑。最后在一九五八年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公布,后来在一九八二年得到“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成为书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我写的关于拼音方案问题的一些文章,集成一本《拼音化问题》,后来在一九八0年出版。
“汉语拼音方案”是以“音节”为单位的拼写法规则。方案公布之后,我进一步研究以“语词”为单位的“正词法”。经过多年的推敲,形成《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在一九八八年公布。配合正词法,我从五十年代开始主编《汉语拼音词汇》,经过两次修订再版,一九八九年又出版“重编本”。《汉语拼音词汇》的特点是,正文以语词为单位,采用纯字母排列法,使同音词都排列在一起,现在已经成为中文电脑的词库基础。我写的关于正词法的论文有《汉语拼音正词法问题》《正词法的性质问题》《正词法的内在矛盾》等,后来收集在一九八六年出版的论文集《中国语文的现代化》中。
汉语拼音从一九五八年秋季起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小学的必修课,中文辞书(例如《现代汉语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都用拼音字母注音和排列正文,电脑输入中文的新技术采用“从拼音到汉字”的自动变换法。我国语文政策规定,拼音是帮助汉字的设计,可以做汉字不便做和不能做的各种工作,但是并非取代汉字的正式文字。“拼音”不是“拼音文字”。所谓“拼音化”有广狭两义:狭义指作为正式文字,广义指任何的拼音应用,包括给汉字注音,拼写普通话,在电脑上应用,等等。广义的“拼音化”已经广泛推行。
汉语字母的创造是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从现成汉字(三十六个字母)到变异汉字(注音字母),从民族形式(注音字母)到国际形式(国语罗马字),从外国方案(威妥玛方案)到本国方案(国语罗马字),从内外不同(国内用注音符号,国外用国语罗马字)到内外一致(国内国外都用汉语拼音),从国家标准(一九五八年国家公布拼音方案)到国际标准(一九八二年ISO通过拼音方案为国际标准)。
使文字改革跟语言学挂钩
文字改革运动有三个方面:一、群众的文改运动(主张有的激进、有的稳健,有的成熟、有的幼稚);二、学者的文改研究(钻研较深,主张不一,重理论而轻实用);三、政府的文改政策(各个时期有统一的规定)。辛亥革命以来,文字改革逐步前进,但是没有长远规划,缺少理论指导。我是从群众运动中来的一个感性工作者,自己知道知识不足,水平太低,深感文字改革需要跟语言学挂钩。
一九五八年秋季,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力教授约我去开讲一门“汉字改革”课程。我借此机会把清末以来文改运动的历史经验整理一番,从中归纳出一些原则,就我的浅薄了解,尝试跟语言学(包括文字学)挂钩,希望使文字改革成为一门可以言之成理的系统知识。我的这一努力是幼稚的,可是在当时是一种新的尝试,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后来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又约我去再次开课。我把讲稿整理成《汉字改革概论》一书,一九六一年第一版,一九六四年再版,一九七九年第三版,一九七八年出香港版,一九八五年在日本出日文翻译版。
语文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跟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社会长期停滞,语文也就停滞不变;社会急剧变化,语文也发生急剧变化。秦并六国,发生“书同文”变革。辛亥革命,发生白话文和国语运动。在西欧,文艺复兴之后各国创制民族语文。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掀起文字改革。语文变化,可以是无意识的,可以是有意识的。有意识和有计划的变化称为文字改革。
文字改革对语言学和文字学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例如,关于国家共同语:共同语的词汇基础和语音标准问题;异读词的读音规范化问题;词与非词的界限问题;语词的结构问题等。关于汉字:汉字和语词的使用频率问题;汉字的分层应用问题;同音字和同音词问题;简化和繁化问题;声旁的有效表音功能问题;现代汉字的部件分解问题等。诸如此类新问题的提出,扩大了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范围,使文字改革从感性知识向理性知识前进。
关于同音词问题:我认为同音词是语言问题,不是文字问题。在文字上分化同音词,汉字可以做到,拼音也可以做到,但是这只能使“同音词”变为“异形词”,不能使“同音词”变为“异音词”。同音词依旧是同音词。我提出,同音词有“四不是”:一、不能单独成词的同音汉字不是同音词;二、异调同音不是同音词;三、文言古语同音不是现代汉语的同音词;四、语词和词组同音不是同音词。除去“四不是”,同音词的数量就不是人们所想象那么多了。语言有分化同音词的能力;在传声技术时代,这一能力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五十年代把“炎症”和“癌症”的读音分化,把“初版”改为“第一版”跟“出版”相区别,这是成功的例子。在“异读词”的审音工作中,区分了更多的混淆不清的同音词。
关于形声字的表音功能问题:我在分析一本《新华字典》和若干报刊文章之后,发现现代汉字(约七千字)中“声旁的有效表音率为百分之三十九”,如果要区别声调,有效表音率不到五分之一。我写了论文《现代汉字中声旁的表音功能问题》(一九七八)和一本小书《汉字声旁读音便查》(一九七九),说明“秀才识字读半边”根本靠不住。古人造字,只求声旁读音近似,不求读音准确。读音的历史演变,使声旁大都失去了表音功能。声旁表音只有“近似性”,这是中外古典文字的共同现象。
在大约七千个现代汉字中,有基本声旁五百四十五个(不同字典数目略异),其他是滋生声旁。在现代汉字中,能独立成词的“词字”占三分之一,不能独立成词的“词素字”占三分之二。“词字”数量有相对稳定性。这些数据有多方面的实际作用,但是还要进一步研究核实。
在比较多种现代汉字的使用频率之后,我提出“汉字效用递减率”:最高频一千字的覆盖率大约是百分之九十,每增加一千四百字只提高覆盖率大约十分之一。这个规律给减少汉字的字量研究提供了一项统计依据。后来北京大学苏培成教授对“汉字效用递减率”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改进。
传统汉字学研究汉字的形音义的历史演变,实际是“历史汉字学”。为了当前应用的需要,我提出要从历史汉字学中分出一个分支,叫作“现代汉字学”,研究现代汉字的现状和应用问题。一九八0年我发表论文《现代汉字学发凡》。不久,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开设了“现代汉字学”课程,并且编写出版了几种现代汉字学的专著。
其实,现代汉字学的研究在民国初年就事实上萌芽了。当时提倡:废除反切,用字母注音;简化汉字;改进查字法;用统计方法研究小学用字问题。在日本,革新的研究开始得更早。我在《现代汉字学序言》(一九九三)中说:现代汉字学是“播种于清末,萌芽于五四,含苞于战后,嫩黄新绿渐见于今日”。
汉字简化从一九五六年的《汉字简化方案》(五百一十五字)类推成为一九六四年的《简化字总表》(两千二百三十五字)。在七千个现代汉字中,三分之一是简化字,三分之二是没有改动的传承字。这些规范汉字已经普遍用于中国大陆的教科书、报纸和杂志,只有招牌、广告等所谓“社会用字”还处于混乱状态。在台湾,手写行书也用简化字,跟大陆大体相同。香港“繁简由之”,回归之后渐渐改繁为简。根据小学教师的经验,简化的好处是“好教、好认、好写”。简化字的清晰性在电视上极为明显。王羲之的书法中有三分之一是简化字,简化无损于书法。但是简化的好处不宜夸大。汉字的困难主要在字数太多。日本重视减少字数,一般只用一千九百四十五个常用汉字,值得中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