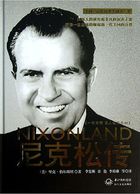我生于清朝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年),后经北洋政府时期、国民党政府时期、一九四九年后的新中国时期,友人喜称我四朝元老。这一百年间,遇到许多大风大浪,最长的风浪是“八年抗日战争”和“十年文化大革命”,颠沛流离二十年。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重庆,一个日本炸弹在我身边爆炸,旁边的人死了,我竟没有受伤。“文化大革命”时期,我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跟着大家宣誓“永不回家”,可是林彪死后大家都回家了。
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是无意中逃过了“反右”运动。一九五五年十月,我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被留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放弃上海的经济学教学职业。过了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反右”运动在上海以经济学界为重点。上海经济学研究所所长,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自杀了。我的最优秀的一位研究生自杀了。经济学教授不进监牢的是例外。二十年后平反,一半死去了,一半衰老了。我由于改了行,不再算我过去的经济学旧账,逃过了一大劫难。“在劫不在数”!
常听老年人说:“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我的想法不同。我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我从八十一岁开始,作为一岁,从头算起。我九十二岁的时候,一个小朋友送我贺年片,写着“祝贺十二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
年轻时候,我健康不佳。生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结婚时候,算命先生说我只能活到三十五岁。现在早已超过两个三十五岁了。算命先生算错了吗?算命先生没有算错。是医学进步改变了我的寿命。
二○○三年冬天到二○○四年春天,我重病住院。我的九十九岁生日是在医院里过的。医院送我一个蛋糕,还有很大一盆花。人们听说这里有一个百岁老人,就到窗子外面来偷偷地看我这个老龄品种,我变成医院里的观赏动物。佛家说,和尚活到九十九岁死去,叫作“圆寂”,功德圆满了。我可功德圆满不了。病愈回家,再过斗室读书生活,消磨未尽的尘世余年。
老年读书,我主要读专业以外的有关文化和历史的古籍,想知道一点文化和历史的发展背景。首先想了解三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因为历代帝王歪曲历史,掩盖真相。考古不易,考今更难。苏联是新中国的原型,中国改革开放,略作修正。苏联瓦解以后,公开档案,俄罗斯人初步认识了过去,中国还所知极少。美国是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由于戴高乐主义反美,共产主义反美,伊斯兰教反美,美国的面貌变得模糊不清。了解真实的历史背景困难重重。可是旧纸堆里有时发现遗篇真本,字里行间往往使人恍然大悟。我把部分读书笔记改写成为短篇文章,自己备忘,并与同好们切磋。
先知是自封的,预言是骗人的。如果事后不知道反思,那就是真正的愚蠢了。聪明是从反思中得来的。近来有些老年人说,他们年轻时候天真盲从,年老时候开始探索真理,这叫作两头真。两头真是过去一代知识分子的宝贵经历。
我家发生过一个笑话。著名的漫画家丁聪,抗日战争时期常来我家。我们一家都很喜欢他,叫他小丁。我的六岁的儿子十分崇拜他。一天,我在家中闲谈,说小丁有点“‘左’倾幼稚病”。我的儿子向他告密:“爸爸说你‘左’倾幼稚病!”弄得小丁和我都很不好意思。多年以后,我的儿子到了七十岁时候,对我说:“其实那时爸爸的‘左’倾幼稚病不亚于小丁。”
老来回想过去,才明白什么叫作“今是而昨非”。老来读书,才体会到什么叫作“温故而知新”。学然后知不足,老然后觉无知。这就是老来读书的快乐。
学而不思则盲,思而不学则聋。我白内障换了晶体,重放光明。我耳聋装上助听器,恢复了部分听觉。转暗、为明,发聋振聩,只有科技能为老年人造福。
“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最好的长生不老滋补品。
希望《百岁新稿》不是我的最后一本书。
二00四年九月一日?时年九十九岁
(《百岁新稿》,三联书店二00五年第一版)
《〈伊索〉的舞台艺术》序
我上小学以前,就听过《伊索寓言》。上小学以后,我看过中文的《伊索寓言》。一九五九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伊索》在北京演出,我看了。一九八○年,这个剧院再度上演《伊索》,我又看了。
两次看《伊索》,感受不同。五十年前,看了以后,我惊叹!第二次看了以后,我悲叹!
惊叹什么?惊叹剧本作者的才华!《伊索寓言》在我的印象里原来像是许多珍宝散乱在桌子上,彼此之间是没有联系的。那年去首都剧场看《伊索》之前,我想,把《伊索寓言》写成话剧是可能的吗?看完以后,我像是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眼前出现了海市蜃楼!剧本作者把散乱的珍宝编织成一幅生动的图画了。图画中每一个人都在紧张地活动,每一只鸟儿都在歌唱,每一头野兽都在奔跑。古老的传说变成有温度、有脉搏的现实生活。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才华!
悲叹什么?悲叹奴隶社会的不幸!
文明古国的希腊原来是必须在两种不幸之中选择一种的充满着“两难”(dilemma)的奴隶社会!奴隶伊索的选择是,追求自由就得死,保留生命就得做奴隶。女奴隶主的选择是,要想生活舒适就不能得到真正的爱情,追求真正的爱情就只有跟着奴隶去受苦。漫长的奴隶时代呵,这是多么令人悲叹的社会!
可怜的伊索!见到你背上累累的鞭痕,我禁不住泪如雨下!我知道,你心灵上的鞭痕比你背上的还要多,还要深!正因为你有知识,所以你受到鞭挞。如果你也一无所知,你不是可以像阿比西尼亚一样去鞭挞别人吗?但你怎肯去鞭挞别人而换取愚蠢呢?
伊索的话,句句是血,是泪!的确,舌头是最好的东西,又是最坏的东西。怎样分辨舌头的好坏呢?第一次看完了戏时,我问自己,我没有回答,就把问题丢开了。当我在一九八○年再次看《伊索》时,我又问自己。我不能再丢开这个问题。我要回答:实践是检验好坏的唯一标准。由于历史服从实践的检验,所以希腊终于走出了奴隶时代。
《伊索》这个话剧是真正的说话艺术。舞台上只有六个人,一种布景,几张桌椅。但北京人艺的演员们,使观众忘记了他们是中国人扮演外国人,是现代人扮演古代人。他们把观众带进了两千五百年前,使观众的心弦跟伊索一同紧张地跳跃。
很高兴听到说,北京人艺要编辑出版《〈伊索〉的舞台艺术》,我对这个剧院很有感情,曾经看过它演出的许多戏。同这个剧院的许多人都是多年的老朋友,像曹禺、焦菊隐、舒绣文、吕恩、于是之、方涫德、杨薇……时光易逝,时光也很残酷,不少的老朋友已经故去,但是能让我欣慰的是,他们在中国话剧舞台上所留下的一个个艺术形象,正如伊索追求自由的精神那样,永不磨灭。
二00八年七月时年一0三岁
(《〈伊索〉的舞台艺术》二00九年新版)
世纪的来客
——《二十一世纪的华语和华文:周有光耄耋文存》前言
我在九十六岁进入二十一世纪。
河北人民出版社在一九八一年出版一本《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第一分册)。编写说明中说:“本书所收的范围,自一八九八年《马氏文通》出版始,第一分册收录三十人。”我被列名其中。到二十世纪末,书中二十九人都作古了,只有我一人走出二十世纪进入二十一世纪。作为一个二十世纪的来客,我要访问二十一世纪的青年们,同他们作“世纪接轨”的谈话。我要了解他们将如何建设二十一世纪,我要告诉他们一些我所知道的二十世纪的故事。
二十世纪是一个光明的世纪,但是又很黑暗。二十世纪是一个智慧的世纪,但是又很愚昧。遗憾的是,黑暗不比光明小,愚昧不比智慧少。二十世纪发生两次旷古未有的世界大战,使千万、千万的群众像蚂蚁那样死去。二十世纪一些军阀以美好的言词残害千万、千万善良的老百姓。这就是“万物之灵”的行径吗?大规模破坏森林,使无数动物无处藏身,迅速灭种。大规模破坏江河和湖泊,使一年洪水泛滥,一年赤地千里,灾难频仍。这就是“现代文明”的表演吗?教育家们喜欢隐恶扬善,青年们容易听到历史的英雄故事,不容易知道历史的悲惨场面。
“二十世纪人”在世纪接轨的时刻,有责任告诉“二十一世纪人”:不要轻信神话,要牢记“前车之覆、后车之戒”。
二000年我出版一本《现代文化的冲击波》,选载我八十岁之后的部分文章。今年我又选辑我九十岁以后的部分文章成为这本《耄耋文存》。这是我所能讲的故事的一部分,内容是文化问题、语文问题、其他问题:我希望二十一世纪的青年们看了之后会心一笑,说一句。这就是“二十一世纪人”的愚昧!
“二十一世纪人”的座右铭是:了解过去、开创未来,历史进退、匹夫有责。
(二00一年四月八日)
学而不思则盲,思而不学则聋
——《现代文化的冲击波》前言
“学而不思则盲,思而不学则聋”。(孔子不及格弟子周有光习作)
我的朋友说:孔夫子明明说的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你怎么改了两个字?
我说:就是由于改了两个字,我成了“不及格”弟子。
言归正传。
我的朋友看了一本清人笔记,告诉我其中一个故事:
袁世凯在山东练洋枪兵,义和拳的气功大师们嘲笑说,我们一发功,子弹打不进,洋枪兵就白练了!袁世凯听了,觉得事关大局,就把带头的十位气功大师请来。袁世凯问:“发了功,子弹打不进,是真是假?”大师们说:“当然是真!”袁世凯说:“好,请到操场去试试看。”十位大师一字排开,作势发功。一个小兵拿出洋枪,向第一位开枪。砰!第一位倒下了!其余九位一齐跪下:“大人饶命!”袁世凯说:“你们回去吧!”就这样,九位大师悄悄地把练功队伍从山东搬到直隶,在那里买通大官,闹成“扶清灭洋”的大乱。
朋友说:清朝末年,两种人最活跃。一种人像袁世凯,利用洋枪,保护皇帝,这叫作“皇帝为体、洋枪为用”,后来自己做皇帝。另一种人像气功大师,依靠迷信,愚弄百姓,勾结昏官,从中渔利。近来伪科学猖獗。义和拳是过去的伪科学。伪科学是今天的义和拳。帝国主义是一种科技文化冲击波。现在我们面对另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冲击波:现代文化冲击波。
他的话,使我闭目深思。清末老一代不了解帝国主义的性质。今天我们一代了解现代文化的性质吗?
我在八十二岁以后陆续对当前的文化问题写了一些探索性的文章,不知道探索对了,还是探索错了。我自己警惕自己:“学而不思则盲,思而不学则聋。”这里选录拙作二十多篇,请读者指教,引我走出盲聋。
一九九九年九月一日时年九十四岁
残酷的自然规律
——《浪花集》后记
张允和有十位姊妹兄弟,前面四位是姊妹,后面六位是兄弟。四位姊妹在初中读书的时候,课余办一个家庭刊物,自己写稿,自己油印,题名为《水》。这是家族和亲友间的联络和娱乐的小玩意儿,“不足为外人道也”。
七十年之后,张允和已经八十六岁,怀念姊妹兄弟和至亲好友,异地异邦,四散飘萍。她重新编印这个久已停刊的《水》,借以凝聚亲情、互通声气。起初她一人自写、自编、自印、自寄,每期只有二十五份。后来亲友中感兴趣的人渐多,增加到一百多份。
想不到这个微不足道的小玩意儿,被有名的记者叶稚珊女士看到,她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这是天下最小的刊物。更想不到被大名鼎鼎的出版家范用同志知道了,他发表文章说,这是二十世纪的一大奇事。于是《水》的潜流,渗出了地面。
新世界出版社总编辑张世林先生,建议把《水》中文章选择一部分,编成一本书,公开出版,以便对这个别出心裁的家庭刊物有兴趣的广大读者,一睹为快。张允和欣然从命,会同三妹张兆和,编成这本《浪花集》。
《浪花集》正在编辑排印的时候,张允和在二00二年八月十四日忽然去世了,享年九十三岁。半年以后,在二00三年二月十六日,三妹张兆和,沈从文先生的夫人,也忽然去世了,享年九十三岁。姊妹两人,先后去世,都是享年九十三岁。九十三岁,是人生的一个难关吗?
我的夫人张允和的去世,对我是晴天霹雳。我们结婚七十年,从没想过会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人。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后来我忽然想起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能进化”。多么残酷的进化论!但是,我只有服从自然规律!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二00三年四月二日,夜半时年九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