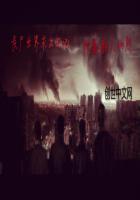进了四川,我们住在重庆的南温泉,当时那里是防空设施最好的地方,蒋介石也住在南温泉。有一回我下班后坐滑竿过江,一个炸弹下来,炸在旁边,力量很大,把我整个人吹出滑竿,我就掉在阴沟里面了。日本飞机过去以后,我才爬出来。我想我一定受伤了,摸摸身上,没什么地方疼,一看旁边的人都死了。后来人家说,幸亏是风把我吹到阴沟里面去了,我躺在阴沟里不敢动,弹片没有打到我。我一生最痛苦的时候,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我只是碰巧没有死掉,四川人说我是命大。
八年以后回来,家里看家的人都找不到了,家里住的都是我不认得的人。我的家完全变化了,什么都没有了,连家里的老房子,人家都不承认是我们的。抗日战争八年,完全割断了我家的历史。
我在重庆的时候,国民党成立了一个政协委员会,每个月要开一次座谈会,每次都请我去,讨论世界大事。周恩来一直在重庆,周恩来的秘书是我的朋友,他是研究经济学的,所以我同周恩来很早就比较熟悉了。那个时候,我们为什么倾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呢?周恩来一再讲,我们共产党是讲究民主的——就是这一条。解放后,我们认为,共产党要建设新中国,新中国当然应该是民主的嘛。开头几年的确很好,比如“文字改革”问题,周恩来就找我们到国务院去讨论,讨论到中午还没完,周恩来就说,在国务院吃饭吧。我们吃饭,就是两荤两素。周恩来说,大家平等。
(《半张破桌,百年风流》,周有光口述,武云溥记录整理。《文史参考》二0一0年第二十四期)
故人风流
当年卞之琳很有意思,卞之琳追求四妹充和,四妹不喜欢他——恋爱的事情本来就很难讲道理,譬如我不喜欢你,要讲出道理来是很难的。卞之琳天天追她,可是他怎么样也不行。
卞之琳追四妹失败了,沈从文追三妹(张兆和)倒是成功了。沈从文也有趣味,三妹那个时候在上海吴淞公学念书,胡适做校长。胡适提倡白话文,就请了沈从文来教学生写白话文。因为当时认为,沈从文写白话文写得最好。沈从文就喜欢上了他的学生三妹,他就写情书给三妹。三妹很生气,拿着情书去找胡适告状,说你看,沈从文是我的老师呢,还乱七八糟写这种信给我。没想到,胡适的思想太新了——胡适说,沈从文他没有结婚,他向你表示爱慕,这没有错呀。
三妹一听这句话,已经不高兴了,胡适下面一句话更糟糕——胡适说,我跟你爸爸是朋友,要不要我跟你爸爸去讲?三妹气得不得了,把信一摔就走了。可是沈从文有毅力——我写给你的信,你看也好,不看也好,反正我不断写给你。后来他们慢慢就好起来了。
沈从文喜欢聊古代的东西,我年轻时候也是读的古书,所以古代的东西我们都能聊。可是我搞文字改革,搞汉语拼音方案,他不感兴趣。他说,用拼音在打字机上打文章,文章是不会好的,因为他自己不会用打字机。
沈从文这个人,脾气很好。三妹有时候发脾气,他就笑笑,也不发脾气,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发脾气。还有就是他的自修能力很好,什么东西都是自修的,他确实小学都没有毕业。我们一个亲戚的小孩小学毕业了,去看他,他说:“不得了,你都小学毕业了,我还没有小学毕业呢。”
我跟我老伴(张允和)的情况,跟他们不一样,我根本没有追求。因为我的老伴是我妹妹的同学,常到我家来玩,我就认得她了。在苏州时,我们经常一起出去玩。后来我到上海,她也到上海,就接触比较多一点。又碰巧,我到杭州,她也到杭州——那时候军阀打仗,苏州到上海的铁路炸了,她去不了上海,可是到杭州的路是通的,所以她就到杭州去借读。我恰好在杭州教书,接触更多了,就开始恋爱。我们这个恋爱,跟今天完全不一样。我们两个人出去,一定要离开一段,不能手拉手的。手拉手在马路上走,有伤风化。古代人讲究举案齐眉,现代没有案了,我跟我老伴就用杯子,每天喝咖啡的时候,举杯齐眉。虽然只是好玩的事情,但这个小动作表示,我们彼此有敬重。男人要敬重女人,大男子主义其实每个男人都有的,所以更要提倡“敬”,这样家庭就可以和睦了。
(《半张破桌,百年风流》,周有光口述,武云溥记录整理。《文史参考》二0一0年第二十四期)
“文革”劫难
抗战结束,从重庆回到上海以后,我进入银行工作,银行就派我去美国。从美国回来以后,新中国已经成立,我本来是学经济学的,这时候改行去研究语言文字学。我不认为改行很困难,比如语音学的知识,我在学经济的时候就已经去旁听过课,这些知识都有。“通识教育”在国外是共识,所以外国人改行都很容易,中国学生要改一个专业却几乎不可能,这样下去是要吃亏的。解放以后我们变成向苏联学习,更糟糕,大学都变成专业学校了。这造成很多麻烦,比如清华大学本来有名气是因为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变成一个理工科的院校,直到改革开放,才又改回来。
一九四九年以后,沈从文的情况也有意思,他对于国际政治不了解,对于中国的政治问题也不了解。所以共产党来了他就害怕,为什么害怕呢?郭沫若公开骂他。沈从文一度精神很不好,后来上面把他派到故宫里做解释员,就是拿一根棍子跟人家讲故宫里的东西,这是当时故宫最低级的工作,但是他很高兴。他不是假高兴,是真高兴。他说他本来要研究古物,可是接触古物很困难,现在到故宫里来,就很方便,利用这个条件能写出书来。他能把不利条件变成有利条件。
后来的“反右”,谁都想不到。一九五六年开了一次大会,认为我们建设新中国最重要的就是知识。许多人回国不知道情况,美得不得了,讲话都是讲民主的,结果就不对了,“反右”开始,他们都被打倒了。我很侥幸,离开上海来到北京,改行搞语言文字。上海是经济最发达的地方,经济学家在上海是“反右”的重点。我有个好朋友沈志远,是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他从莫斯科大学回来,后来自杀了,我都不知道,因为那时候不能通信。我逃过了“反右”的这一劫,他们不跟我翻旧账了。所以有人说我是命大,运气的确好。不是我有远见,是碰巧。我要是留在上海搞经济,肯定要坐牢的。
到了“文革”时期,就不能读书了,我的家也再次迁徙。我被下放到宁夏的“五七干校”,现在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作“五七干校”——这也是学习苏联的做法,认为我们这些旧的知识分子都没有用了,就给你下放下去,不许回来了。
我到宁夏去,规定说可以带字典,其他书不可以带。我带了一本《新华字典》,后来根据字典写了一本小书还发表了,这是字典的用处。另外我还带了《毛主席语录》,因为语录有二十几种外文版,我全都买来,装了满满一大包。人家一看我带的是《毛主席语录》,也不好说什么,我就用这些外文版的语录来做比较文字学研究。除此之外,连唐诗都不让带,那个年代知识越多越反动,看书变成坏事情。我在宁夏待了两年四个月,林彪死了,我们又都被送回北京。
宁夏那个地方,有一百万到三百万政治犯,修了很多碉堡,一个碉堡五千人,是劳改犯待的地方。我们去的那里,有二十四个碉堡,叫作一个站。条件最好的两个站让我们去,是周总理特别关照,说我们这些人是国务院派去的,这两个站要有电灯,还要打一口井。所以我们可以洗澡,还有电灯,别的站都没有,这是优待我们。
许多人去了很不高兴,我是既来之则安之,住得很好。我本来容易失眠,到了宁夏,体力劳动多了,用脑少了,我就不失眠了,这不是很好吗?
我不觉得难过,我说宁夏这个地方,假如不是搞大运动,我不会来看的。现在看到了,中国还有那么落后的地方。落后到什么程度?我们种的洋白菜,吃不完,送给老乡。老乡问:“这是什么东西,能吃吗?”他们没有知识,也没见过洋白菜。
(《半张破桌,百年风流》,周有光口述,武云溥记录整理。《文史参考》二0一0年第二十四期)
大雁粪雨
一九六九年冬天,我随我的单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全体人员到宁夏平罗西大滩“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里原来有二十来个劳动改造站。国务院有十几个直属单位连同家属,共一万多人,占用其中两个站(“一站”和“二站”),我们单位分配在“二站”。我在那里劳动两年四个月,这对我的健康有好处,我的百治不愈的失眠症自然痊愈了。
在那里两年四个月中,最有趣的记忆是遇到“大雁集体下大便”。
林彪死了,“五七干校”领导下令,明天早上五点集合,听报告。早上我一看天气晴朗,开会到中午,一定很热。我就戴了一顶很大的宽边草帽,防备中午的太阳。
快到十点钟时候,天上飞来一群大雁,不是几千,而是几万,黑压压如同一片乌云。飞到我们的头上时候,只听到一位大雁领导同志一声怪叫,大家集体大便,有如骤雨,倾盆而下,准确地落在集会的“五七战士”头上。
我有大草帽顶着,身上沾到大便不多。我的同志们个个如粪窖里爬出来的落汤鸡,满头满身都是大雁的粪便,狼狈不堪。当地老乡说,他们知道大雁是集体大便的,可是如此准确地落到人群头上要一万年才遇到一次。我们运气太好了,这是幸福的及时雨。我们原来个个宣誓,永远不再回老家。林彪死了,不久我们全体都奉命回老家了。
(《拾贝集》,周有光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二0一一年三月第一版)
暮年生活
我的家绕着世界跑了一圈,又绕着中国跑了一圈,最后落定在北京的这间小屋子里。我一直在自己的专业里面做事,直到八十五岁才离开办公室。这样的问题就是,在一个领域越钻越深,钻到井底里面去,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啦。所以到八十五岁我离开办公室回到家里,就不搞专业研究了,随便看书,随便写点杂文,没有计划。
我最近还开了微博,因为这是新技术。前阵子伊朗搞选举,闹得很厉害,就因为他们用手机发微博,把消息都传到外面去了,搞得伊朗政府很被动。将来技术越来越进步,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变成真正透明的,要保密就很困难了。所有的国家都应当透明,这样整个人类就会更幸福。
我也关注新闻,比如好多人学历造假,我很奇怪,我在许多大学教过书,没有一个大学来查我的学历。我有中国的文凭和外国的文凭,全都没有用处。现在人们为什么造假?因为不讲你有多少学问了,就讲你有什么文凭,这是根本的错误。出来一个方舟子打假,结果他让人给打了。方舟子这个人我觉得了不起,他就是受了美国人的影响,在美国读书,我可以批评你,你也可以批评我,到了中国来谁都不可以批评。我们现在学术没有自由,造假的就横行。我认为今天的自由已经比从前多得多,将来还会有更多的自由。
还有“神医”张悟本、道长李一,这些人出来行骗,他们代表的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坏的道德,却没有法律来限制。医学是一门科学,以前苏联人讲科学有阶级性,无产阶级的科学是真的,资产阶级的科学是假的,结果他自己都是假的。我写过一篇文章讲科学的“一元性”,世界上只有一种科学,在外国这是用不着讲的道理,在中国却很混乱。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人家问我:你看中国有没有希望?我说中国当然有希望啦,因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比如明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辛亥革命是中国的大事情,人家说辛亥革命之后来了一堆军阀,搞得一塌糊涂。可是,辛亥革命把“家天下”的思想改变,变成了“民国”,虽然是个名义上的改变,也是巨大的历史进步。辛亥革命就是民主革命,废除专制。我相信中国的发展前景,将来会更好。
(《半张破桌,百年风流》,周有光口述,武云溥记录整理。《文史参考》二0一0年第二十四期)
“傻瓜电脑”的趣事
一九八八年春天,日本夏普公司送我一台电脑,名叫“夏普中西文电子打字机”。我于是开始每天用电脑写作。用了七年之后,这台电脑有些老化了。我的儿子给我买一台新的电脑,名叫“光明夏普文字处理机”,这时“夏普”加上了繁体字。
我们给这种电脑起个爱称,叫作“傻瓜电脑”,因为它有如下的“傻相”:
一、只要输入拼音,自动变成汉字,完全不用学习任何编码。
二、功能键的用法写明在键盘上,一目了然,不用记忆。
三、它是便携式电脑,不占桌子,机内有打印器,写好文章立刻可以打印出来。
这样简便,不就是给我们这些傻瓜用的“傻瓜电脑”吗?
只要注意一点:以“语词、词组、成语、语段、常见人名地名”等作为单位,尽量避免单个汉字输入。它有“高频先见”功能,同音选择极少。它有“用过提前”功能,选择一次,下次自动显示出来。
八十六岁的老太学电脑
我今年(一九九五年)九十岁。我的老伴张允和八十六岁,她热爱昆曲和古典文学,对拼音和电脑原来不感兴趣。以前只有一台电脑,我每天打个不停,她也无法插手。一九九五年春天,她利用多余的一台电脑,把她二十年来的昆曲笔记加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