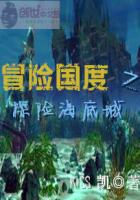本布尔宾山和柯普斯山以北住着一位“健壮的农夫”,要是在旧时,人们准会管他叫羊骑士。他源自中世纪一个最善战的家族,为此他颇为自豪。他是个从语言到行动都相当厉害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在骂人方面和这个农夫媲美的,只有一个住在高高的山顶上的家伙。“天上的父啊,我干了什么要遭此报应?”农夫找不到烟斗时便会这样怨天尤人;在集市上,只有那个住在山顶上的人能和他势均力敌地讨价还价。农夫是个情绪火爆的人,动不动就暴跳如雷,左手乱扯白胡子。
一天,我在他家吃晚饭,女佣人通报,某位欧多纳先生来访。老人和他的两个女儿突然陷入沉默。最后,大女儿用不知怎的有点严厉的态度对父亲下令,“去请他进来,一起用餐。”老人应声走出去,再进来时,表情明显宽慰不少,“他说他不和我们一起吃。”“出去,”女儿命令,“请他到后院坐坐,给他端杯威士忌。”她父亲这会儿已经用完餐,便默默地照着做了,我听到后院的门在他们身后关上——那是一间小房间,傍晚时分,女儿们经常在里面做针线。大女儿转向我解释道,“欧多纳先生是收税官,去年他涨了我们的税,父亲非常生气,趁他上门的时候,把他带到牛奶房,把挤奶女工打发走,狠狠骂了他好一阵。‘我可要提醒你,先生,’欧多纳对我父亲说,‘法律会保护它的官员。’但是我父亲指出,他找不到证人。最后我父亲骂累了,也有点后悔,就提议送他走一条近路回家。他们快走到大路时,遇到父亲手下的一个人,那人正在耕地,不知怎的,这又勾起父亲的满腹怨气。他把那人打发走,又开始大骂税官。我听说这事后,心里难受极了,他竟然如此粗暴地对待欧多纳这样一个可怜人;几个星期前,我听说欧多纳先生唯一的儿子死了,他伤心透了,我就决心等他下次来时,要让父亲好好待他。”
说完,她去邻居家串门,我则慢慢朝后院踱去。刚走到门口,就听到里面传来气愤的说话声。两个人显然又为税收的事吵上了,因为我听到他们来回叫嚷着一些数字。我推开门;农夫看到我,顿时想起他来这儿的善良本意,便问我知不知道威士忌在哪里。我记得看到他放橱子里来着,便把酒取了来。我打量着税收官消瘦、悲伤的脸。他和我的朋友截然不同,看起来非常苍老,既虚弱又憔悴。他不是农夫这种生机勃勃、志得意满的人,而是属于那种在人间找不到什么安憩之地的人。从他身上,我看到了那种充满幻想的儿童的影子,我说,“你一定是古老的欧多纳家族的后代吧。我知道河里有个洞穴,他们的宝贝据说就埋在那里,由一只多头巨蛇看守。”“没错,先生,”他回答,“我是这个家族历代王子中的最后一个。”
我们泛泛地谈起天来,其间我的农夫朋友一次也没有吹胡子,而是表现得非常友好。最后,愁眉苦脸的老税收官站起身准备告辞,我的朋友说,“希望明年我们一起再喝一杯。”“不会了,”税收官回答,“我活不到明年了。”“我也失去过儿子,”另一个人用非常温和的声音安慰他。“可是你儿子可不像我儿子。”两个男人就这样分手了,双方都是脸气得通红,心痛如刀割。幸好有我从中斡旋,否则他们没准还要吵下去,陷入一场关于各自已故儿子的价值的愤怒争论。要不是对所有这些充满幻想的儿童都心怀恻隐,我真想任他们吵下去,趁机记录一段精彩的骂仗。
要是真的吵下去,羊骑士一定会是最后胜出的那个,因为但凡血肉之躯,没有哪个能骂得过他。他只失手过一回;下面就是他讲的这则故事。
某次,他和几个农夫在谷仓背面的一间小屋打牌。以前有个邪恶的女人在这间小屋住过。突然,有个玩牌的人丢下一张A,无缘无故骂起人来。他骂得难听极了,听到的人都吃惊地跳了起来。我的朋友断定,“这里不对劲。他中邪了。”大家赶忙朝通往谷仓的门冲去,想尽快逃出小屋。但是,木头门闩怎么推都不动,羊骑士抓起身边一把倚在墙上的锯子,把门闩锯断。门立刻“砰”的一声打开。就好像一直在拉住它的手突然松开了似的。大家赶忙逃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