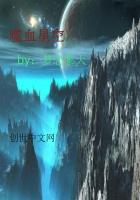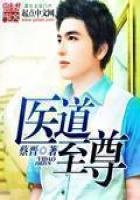(十四)归囚
人人都以为已经死了十几年的小爱德门德终于回到了他的村子,但他发现,他所熟悉的一切都消失了。他失魂落魄地走在原野上,看到了他的父亲,愤怒的情绪一拥而上,便怒气冲冲地扑向老人,用手扼住了老人的喉咙……
25年前,我作为一个牧师,刚刚来到这个村子。村子中有一个人恶名远扬,那个人就是爱德门德。爱德门德是一个脾气暴躁、心肠狠毒的人,时常同几个和他一样懒散嗜酒的流氓在田野间晃荡或者在酒店豪饮。除了那三五个人,他没有一个朋友和熟人,村子里的人每次看见他都躲得远远的,生怕和这个坏蛋有一丁点儿的联系。
那时的爱德门德已经结婚了。他的太太温婉善良,他还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儿子。教堂附近有一小片田地是他租的,但我从来没看他干过活,只有他的妻子一年到头勤劳地耕作,操持着家。
在所有外人看来,爱德门德的妻子是个坚忍可怜的女子,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爱德门德从来不把他的妻儿当人看,一次次地伤他妻子的心。他的妻子始终默默忍受着。在我看来,一方面,那个善良的女人为了抚养自己的孩子,不忍心离开爱德门德;另一方面,她确实很爱爱德门德,她在苦难中一直容忍,就是证据。我想她是凭借着对相爱时的爱德门德的回忆,才一直支撑着。
爱德门德一家的生活十分困苦,尽管爱德门德的妻子不分早晚地辛勤劳作,让他们一家能够吃饱穿暖,但是爱德门德一点儿也没感谢她,反而在酗酒之后,动辄打骂妻儿。深夜里,人们不止一次听到可怜女人的哀求和哭泣声;那个小男孩也不止一次敲响邻居的门,只为了躲避他父亲的暴打。村民们都十分同情这对苦命的母子,但对于他们的遭遇除了同情之外,也做不了什么。
在我的印象中,每个周末这个可怜女子都会带着孩子准时来教堂做礼拜。每次我都看到爱德门德太太带着一身无法掩饰的伤痕坐在她固定的座位上,那个男孩则乖乖地待在她旁边。母子俩虽然衣着破旧,远不如他们的邻居,但总是整洁干净。每个人见到他们母子都友善地微笑示意,或者打打招呼。有时候,她做完礼拜还会站在教堂大门的榆树下和邻居聊聊天,满怀着身为母亲的骄傲和喜悦看着自己辛苦养大的孩子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嬉戏。她那因为操劳而显得苍老的脸因为发自内心的感恩而变得开朗。
大概过了五六年,那个瘦弱的男孩子已经变成了一个壮实的小伙子。他原本纤细的身材和四肢变得孔武有力,而爱德门德太太却饱受岁月的摧残,显得愈发老态龙钟。爱德门德太太的背也佝偻了,渐渐步履蹒跚。每次做礼拜的时候,我看见爱德门德太太都是一个人。她孤零零地坐在老位置上,身边的位置空荡荡的。原本应该陪着爱德门德太太的孩子,再没有出现过。她手中的《圣经》保存得和原来一样完好无损,小心细致地查明、叠好要读的部分。只是她没再露出开朗平和的表情。大家朗诵的时候,我看见她一个人在座位上落泪,眼泪无声地从她凹陷的两颊滑落。邻居们对她还是一样和蔼,但是她每次都躲开人群,悄悄地拉低帽子离开了。我再没见到礼拜结束时她站在榆树下的身影,大概连她自己也不愿勾起以前快乐的回忆。
如果非要深究爱德门德太太逃避人群的原因,大概是令她心寒的儿子。渐渐长大的青年早已不是那个听话的孩子,他不顾母亲的付出,跟他的父亲一样堕落。他和一群无赖混在一起,终日无所事事,听从别人的教唆,疯狂地做着一件件叫他母亲伤心丢人的冒险勾当。倘若那青年有一点点良心,也不会让爱德门德太太伤心至此。可是偏偏这个少年像是刻意遗忘母亲为他所遭受的种种痛苦、忍受的种种折磨一样,变成了和老爱德门德一样让人厌恶的家伙。这不禁让人感叹,有其父必有其子。
然而,对于爱德门德太太而言,不幸并没有到头。她那不成器的儿子被当做犯罪嫌疑人抓了起来。小爱德门德和他的混混同伴在邻近的镇子做了多起案件,一直没被警方抓住。变得越来越胆大妄为的他们犯下了一起劫案。这次他们的好运用光了,警察经过追查和搜索将犯罪嫌疑人锁定在他们四个身上。就这样,不争气的小爱德门德被抓起来,判了死刑。
我永远也忘不了审判的那一天,爱德门德太太在听到判决的那一刻,发出了刺耳的尖叫,就像是她自己被判处死刑一样绝望。那凄厉的惨叫让站在被告席上的小爱德门德面如死灰,直冒冷汗。那个强壮的男子浑身发抖,终于不再无动于衷了。饱受苦难折磨的爱德门德太太在如此沉重的打击下跪在了我的面前,她不知道能做什么,只是祈求万能的主能饶恕她儿子的罪恶,让她能够从这痛苦的深渊中逃脱出去。
看着因为过分悲痛倒在地上的爱德门德太太,我目不忍睹。我眼前是一个被厄运和不幸纠缠的女人,她的心早就碎成一片一片的了。可是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上苍,只是默默忍受着这一切。面对这样可怜的人,老天爷居然没有一丝怜悯。爱德门德太太那心如岩石的儿子一直病恹恹的,执拗地对她不理不睬。就算她不论刮风下雨,每日每夜在监狱哀求也是白费力气。即使小爱德门德逃离死亡,也没有转变执拗的态度。爱德门德太太毕竟老了,她原本不健康的身体在这样沉重的打击之下,更是不堪一击。不久她就染上了重病,即便这样,她依然拖着毫无力气的身子,挣扎着去看望她的儿子。
有一天,爱德门德太太倒在地上,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小爱德门德的考验来了,他的冷漠变成了对母亲的担忧和焦急。小爱德门德终于记起了为他牺牲的伟大母亲。一天过去了,母亲瘦弱的身影没有出现;第二天,他还是没看到自己可敬的母亲;第三天、第四天……再过二十四个小时,小爱德门德就要离开了。这简直是报应!在这个孩子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他却要和自己的母亲永远分开了。
小爱德门德焦急地在监狱的院子里走来走去,期盼着有人能带来他母亲的消息,所有的陈年往事都涌上心头。在醉醺醺的父亲面前保护着自己的母亲,在田地里辛苦劳作的母亲,在教堂榆树下对自己微笑的母亲,他那和蔼可亲的母亲病倒了。这世上唯一一个关爱他的人,病倒了。也许他的母亲要死了,一想到这一点,他就发自内心的懊恼。倘使他还自由,他一定会一个箭步冲到自己母亲的身边。然而此时,小爱德门德只能看着自己手上的镣铐,拼命摇撼眼前的铁栅栏。“来不及了。”怀着这样的念头,小爱德门德蹲在地上,无力地抽泣着。“我,我再也看不见我的妈妈了。”
我来到这个在监狱中忏悔的孩子面前,满怀怜悯地倾听他悔过的誓言和他祈求母亲原谅的话语,听他谈自己未来对母亲的种种奉养计划。尽管我听到这些时就意识到小爱德门德那可怜母亲或许等不到那样的日子了,可我还是像传声筒一样,将这些深情的话语带到重病卧床的爱德门德太太耳边,然后为小爱德门德带回他母亲的宽恕和祝福。当天夜里,小爱德门德就被救走了,很久都没有消息。
小爱德门德走后的两个星期,他可怜的母亲因病过世了。我坚信这个善良坚韧的女子去了天堂,在那个世界好好休息着。我为她举行了葬礼,将她埋藏在教堂的墓地里。虽然没有墓碑,但她的故事世人皆知。她良好的德行为她留下了美名。
小爱德门德走后,我没有收到过他的一封信。这让我几乎以为他已经受不了严苛的刑罚往生了。毕竟他走之前信誓旦旦地保证一旦得到允许就写信给他的母亲。小爱德门德的父亲,依旧终日四处游荡,自从儿子被捕,他就拒绝承认有这样一个孩子。
事实上,小爱德门德还活着,因为他一直待在偏远的地方,所有他寄回来的信,我一封也没有收到。但是他历尽无数艰难,坚持对母亲的誓约回到了家乡,又回到了这个镇子。十四年后,小爱德门德出现在我面前,他一个人回到了这个留着他童年记忆的镇子。
教堂前的老榆树,愈来愈高。阳光透过树荫洒在小径上,小爱德门德想起了童年时的自己。他总是每个周末由妈妈牵着,安静地走进这家庄严的教堂。他清楚地记得,每次做礼拜时,他都和妈妈一起翻开《圣经》,一字一句虔诚地念着。有时候他抬头看着母亲,面色苍白的妇人会俯下身亲吻他的额头,一滴滴眼泪落在他的额头上,他也跟着莫名地哭泣。当时,他一点也不知道这些眼泪的含义。
小爱德门德还想起,有时候他会和邻居家的孩子在路上嬉戏游玩,一回头,就能看到母亲嘴角挂着笑意,温柔地呼唤他。紧接着他想起那个让母亲心碎的自己。那时候不懂事的他把母亲的劝告当做噪音,把母亲的嘱托视为洪水猛兽。他忘不了身患重病的母亲是怎样在监狱门口哀求,企图打动自己的心。懊恼和愧疚让小爱德门德无地自容。
小爱德门德推开了教堂大门,空无一人的教堂里回荡着他一个人的脚步声,空洞而可怕。他环顾四周,教堂并没有什么变化。古老破旧的石碑依然立在那里,他走近他妈妈坐的老位置,熟悉的坐垫不见了,《圣经》也不见踪影。他想,也许自己的母亲已经老到没法一个人来教堂了,也许……他不敢再想下去,即便他知道那极有可能发生,但是他拒绝想下去。他浑身颤抖,越来越觉得害怕,他决定走出这让人心痛的地方。
一出大门,他看见一个老人走了进来。小爱德门德大吃一惊,连忙后退了一步。他记得那位老人认识他,不知道自己会从老人的口中听到什么,恐惧和担忧笼罩在他头上。老人走过时,看着他像对待陌生人一样对自己说了句“晚安”,就走开了。他走出教堂,穿过村庄,看着人们在院子里乘凉。很多人带着对陌生人的畏惧望着他,他试图在人群中找到熟悉的面孔。曾经玩耍的伙伴,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曾经年轻力壮的叔叔,现在变成孱弱的老人。熟悉的人越来越少,没有一个人记得他。
小爱德门德走到他家的老房子,站在门前有些惴惴不安。“母亲”,他脑海中满是这两个字,他在拘禁的漫长岁月里心中一直牵挂的人。夕阳的余晖洒在屋顶,家的样子一点没变。看着院子里的树,他感觉像回到小时候在树下酣睡的日子。他小心翼翼地靠近,听到屋子里传来陌生的笑声。他迟疑了,他惧怕着那个噩耗。就在这时,他好像看到门开了,一群小孩子嬉闹着跑出来,孩子后面还跟着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个让他发自心底畏惧的身影。
这位归囚设想过千百次回家的情形,偏偏没有预料到这一种。他连家都没有了,他那善良温柔的母亲也不知所踪。这不是他想象中的家,他以为他回来的时候能看见妈妈激动的脸庞,能得到宽恕,然后他和母亲幸福地生活下去。他的故乡没有人记得他,甚至他没有地方可以容身。他是个不受欢迎的人,就像个陌生的过客。他曾经忍受的经年累月的寂寞和回家的决心顿时变得可笑。
小爱德门德像泄了气的皮球,一点气力也没有了。他不知道该去哪里,他甚至生不起勇气去寻找唯一可能同情他、接纳他的人。他远离人群,走到记忆里熟悉的草地,蒙着脸扑在地上,像是回到母亲的怀抱里一样。
小爱德门德并没有看见不远处河堤上的人,只是突然听到衣服摩擦发出的沙沙声。他抬起头,看到了那个他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身影。佝偻的背、破破烂烂的衣服无不昭示着对方的贫民身份,小爱德门德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蹲下来,凑近了生怕认错。
“说话!”小爱德门德冲着老人吼道。
老人听到这声音,吓得浑身颤抖、面色惨白。那位老人高声咒骂着退了一步。小爱德门德听见这声音,眼睛里冒出了复仇和兴奋的光芒,他一步步走到老人面前。
“滚开,快滚开!”老人因为愤怒和恐惧扭曲了面孔,声音又尖又利,像是看到了可怕的恶魔。他不停地挥舞着手中的手杖,根本无法控制它落在哪里。
小爱德门德一把夺过手杖,面目狰狞地笑着:“恶魔,你这个恶魔,我终于找到你了,我终于找到你了。哈哈!哈哈哈!”
小爱德门德边说边扼住老人的脖子,任由老人在他手中无力地挣扎。老人最后发出的求救声像是妖魔的咆哮,在田野间久久回荡。血从他的口里和鼻子里涌出来,染红了草地。一切都结束了,小爱德门德看着那个老人——他的父亲重重地倒在污浊的泥塘里,就迈着轻快的步子回到了教堂。
我又见到了小爱德门德,并且雇了他。他发自内心地忏悔、改过,渐渐变成一个好人。直到他去世,村子里也没人发现他就是曾经的那个少年——约翰?爱德门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