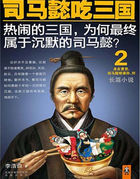听说登高在旺兴,一个月就散掉了几千龙洋,叶福清急火攻心,一头栽倒,再醒来,人已有些魔怔,两条腿也不听使唤,屎尿都不能自理。本以为这辈子就这样废了,期间,吃了一棵登科送回来的长白山千年山参,叶福清竟然重新站了起来。当时叶福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倒是鲁氏在一旁看到了,大惊小怪地喊出了声。鲁氏说,何黑子,何黑子,你快来看,快来看呀,老爷站起来了。何黑子和来宝不知出了什么事儿,冲进屋子,顿时吓了一跳。他们看到叶福清真的站在正屋中间,脸上挂着夸张的笑容。何黑子说,老爷,您大喜了,能站起来,就是病好了。来宝则担心地说,老爷,您身子骨儿行吗?还是躺下吧,别累着。何黑子狠狠地踢了来宝一脚,骂道,你小子会不会说话,老爷明明能站起来了,你干吗咒老爷躺下?我看你小子该躺下。鲁氏不满地瞪了来宝一眼,也训斥说,就是,你这是恨老爷不死。叶福清却摆摆手,和气地说,行了行了,来宝不是那个意思,这我清楚。我说老婆子,你看,我好了,是不是因为登科送来的那些东西呀?鲁氏说,怎么不是?我说过了,你这两个儿子,一个顾家,一个败家,要是登高……叶福清厉声制止说,不要提他,谁也不要提他!从现在起,我只有一个儿子,那就是叶登科。
叶福清怒火攻心,猛烈地咳嗽起来,吓得鲁氏赶紧扶他坐下,又是抹前胸,又是拍后背。过了好一阵,叶福清才消停,他大口大口地喘息一阵,又用拐棍杵着地面说,登高这个畜生,瞎了我那些钱了,供他念书,供他去留洋,到了供出个败家子,我冤哪,我冤死了!叶福清又开始咳嗽了。鲁氏一边照顾叶福清一边骂道,老东西,你就不能不生这份闲气?你现在怪登高有什么用?都是你惯下的,怪谁呀?当初我不让你送登高去日本,你偏不信,一心指望登高学到了洋玩意儿,回来好当官儿,这下好了,登高把孙大炮的玩意儿学来了,会造反了,你呀,等着砍头吧。叶福清脖子一梗,眼睛瞪得像老牛,他冲着鲁氏大吼,我去县衙门和他断绝关系,我和他一刀两断,我凭什么受他的拖累,叶家人凭什么要跟他去砍头?鲁氏见叶福清动了肝火,便好言相劝说,好了,别生气了,怎么说也是你养的,虎毒不食子,你还是别说狠话了。
鲁氏前脚走,叶福清后脚就吩咐何黑子套车,直奔诸城。
路上,何黑子没话找话地说,老爷,二少爷送回大钱了,咱叶家有救了。叶福清说,是啊,儿女都像登科,老人就省心多了。这一次,我一定要和登高划清界限,不能让这个不孝子害了你们这些人。
看眼下这局势,叶家要败。何黑子衡量过,二少爷登科虽然弄了些钱,可是,大少爷登高却在谋反,两下相抵,二少爷那点儿钱,远不足以救叶家的命。何黑子早在大少爷革命之初,就开始谋划后路了。当然,事态不明,他未敢轻动。毕竟世事难料,万一革命党真成了气候,那大少爷可是开国功臣,官势必做大。官运亨通,财源滚滚,这是定例。那时,背叛大少爷的人可就被动了。于是,何黑子决定等。打铁也要看火候儿,火候儿到了,再去淬火,才能干出绝活儿。何黑子一直等到叶福清要和大少爷划清界限,才决定动手。他已做好准备,到了县城,就找乔书吏通融,他愿为内应,与官府里应外合,将叶登高那一伙革命党一网打尽。老何不求富贵,只求一门平安。眼下,何黑子已经不能容忍叶福清一口一个下人了。下人怎么了?何家祖祖辈辈给你们叶家当下人,累得腰杆子都断了,到头来,还是下人。何家人不贱,没有当下人的瘾。从前做下人,那是时机不到,现如今,你们叶家要败了,轮也轮到何家人扬眉吐气了,都说风水轮流转,哼,咱走着瞧吧。
这么想着,何黑子把车赶得飞快,不到晌午,大车已经进了诸城。叶福清说,去马前街,找高掌柜吃晌饭。何黑子犹豫了一下,想说什么,终于没说。大车往外一拐,便去了马前街的兴隆客栈。
客栈高掌柜已经看到了叶福清从车上下来,但他还是闷着头,啪啪地拨弄着算盘,就像没看见叶福清一样。叶福清说,老高,你忙什么呢?高掌柜说,不忙什么,盘盘账。叶福清有些光火,他不相信高掌柜听不出来人是谁。这个混蛋,这是犯的哪路邪?叶福清说,高玉宝,你连规矩也不懂了吗?高掌柜这才抬起头,不冷不热地说,叶福清,你到我们陈家的铺子里嚷嚷什么?这是你撒野的地方吗?叶福清愣住了,什么?他拉住高掌柜的胳膊大声质问,你说什么?你说这是……陈家的铺子?高掌柜甩开叶福清的手,还是不紧不慢地说,怎么,你家的两个少爷没对你说吗?他们伙着把这个铺子给卖了,对了,顺便告诉你一声,你在诸城所有的铺子,都被二少爷卖了,你再也不是东家了,你现在就是一个顾客,顾客你不会不懂吧?高掌柜回头看看店伙,店伙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叶福清听了这话,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一黑,便栽倒在地。
何黑子叫了两声老爷,忽然想起了路上做好的打算,他也不急了,一屁股坐在店墙下的一条凳子上,不高不低地说,老高,来碗茶水。
高掌柜说,何黑子,你不会也像我,换了主子吧?何黑子嘿嘿一笑,手指高掌柜的鼻子尖说,老高,亏你还在诸城混了这么久,怎么一点儿小道儿消息都没有?济南这几天不是抓革命党吗?你想啊,济南抓了,诸城要不要抓?那你说,诸城要抓谁?高掌柜傻傻地问,抓谁?何黑子说,叶登高呀,他是诸城最大的革命党,不抓他抓谁?
高掌柜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如果官府要抓登高,那陈冰如会怎么样?陈冰如可是兴隆客栈的老板,换句话说,她也是我老高的老板。陈冰如要是谋反,我老高会不会连坐?高掌柜冒出了一头冷汗,他战战兢兢地掏出两个龙洋说,老何,这两个龙洋归你。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找我,有我老高在,你来就管用。何黑子说,这还像句话,这样吧,一会儿把叶福清弄到旅店里,我们出去喝几盅,如何?高掌柜眼睛转了几转,打着哈哈说,哎哟,晚上盘点,没空儿,改日吧。何黑子拍拍钱袋子,不无抱怨地说,你个鸡巴老高,太不实在了。好吧,你不去,我自个儿去。
何黑子把叶福清背到车上,去了祥记大车店。何黑子熟门熟路地找到梁掌柜,介绍了叶福清的身份。梁掌柜听说是登科的父亲,自然不敢怠慢,急忙派伙计请了郎中,给叶福清诊治。梁掌柜忙了半晌,再找何黑子,却不见了人影儿。梁掌柜疑惑地暗忖,这个老何是不是不想在叶家做下去了?
到后半晌时,叶福清醒了,看到身边都是陌生人,挣着身子要走。梁掌柜拦住叶福清,说了自个儿和登科的关系,一番好言相劝,总算把叶福清留在店里。看看天晚,梁掌柜布置小伙计,给叶福清预备酒菜,梁掌柜亲自作陪,两人喝了几杯酒,吃了些牛肉。当晚,叶福清就住在祥记大车店里,梁掌柜里外照应,一直等叶福清睡熟了,梁掌柜才回到自个儿房里,疲惫地睡下。
等到天亮,梁掌柜准备了洗漱器具,一脸笑容地走进叶福清的睡房,却傻了眼——叶福清不见了。梁掌柜赶紧派人四下寻找,找了半头晌,派出的几伙人都无功而返。梁掌柜有些急,朋友的老爹,出任何事都是不义。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得找到叶老太爷。梁掌柜把店里的事托付给大伙计,自个儿便奔了县衙。他要去找杜捕快出出主意。
刚走到县衙门口,就看到一群衙役围着一个人在取笑。梁掌柜近前一看,坐在地上的正是叶福清。叶福清逐个看着衙役们,认真地说,我真的要和我大儿子叶登高划清界限,一刀两断,永不来往。瘦衙役说,老头儿,你糊涂了吧?你大儿子可是留过洋的,这样的儿子你都不要了?叶福清说,他是革命党,我不敢要了。胖衙役说,老头,你儿子是不是革命党我不知道,我光知道他是我们陈太爷的女婿,你在衙门口儿这么说,陈太爷知道了,会不高兴的。另一个衙役也说,老头儿,你还是走吧,你这么说话,最好不要去见陈太爷,会出麻烦的。叶福清不肯走,抱住胖衙役的腿说,这位兄弟,你帮帮我,我儿子回来了,我让他给你钱。胖衙役说,你都不要儿子了,谁给我钱?叶福清讨好地说,我还有二儿子,他叫叶登科,一身绝世武功,现在是济南府尉衙门的捕头,他会给你钱。一听到叶登科,衙役们都变了脸。上次杜捕快的事,他们都记忆犹新。衙役们一哄而散,只剩下叶福清一人,坐在地上喘粗气。
梁掌柜上前拉起叶福清,一溜儿碎步往回走。一直回到祥记大车店,梁掌柜才和颜悦色地说,叶老太爷,你不要乱走了,登科说了,他明个儿就来接你,你安心住下好不好?叶福清固执地说,我要去找陈大老爷,我大儿子是革命党,我要和他一刀两断,划清界限,你帮我好吗?梁掌柜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他暗想叶老爷子是不是疯了?梁掌柜让郎中给叶福清下了镇静药,又派人去济南找登科。
到了晌午,叶福清醒过来,梁掌柜便让人把饭菜送进房中,自个儿亲自服侍他。酒只有一盅,饭管够儿,菜却是硬菜,鸡、鱼、肉、蛋俱全。正吃着,小伙计进来,伏在梁掌柜耳边说了几句话,梁掌柜赶紧起身往外走。门帘一挑,陈世林已一步跨进门内。
陈世林上前看了看叶福清的饭食,一脸和气地说,叶财主,一向可好啊?叶福清神情有些恍惚,想不起陈世林是谁,见他友善,就把一个酒盅放在陈世林面前,客气地说,喝一杯?陈世林也不客套,端起杯子,一饮而尽。叶福清说,大兄弟,你是做什么的?我看你不像个种地的。陈世林说,是啊,我不种地,可我一直对种地感兴趣。听说你有不少好地,怎么样?收成还好吗?叶福清一摆手,一脸辛酸地说,别提了,家门不幸啊。
叶福清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把登高革命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陈世林听完,良久无语。陈世林喝下一杯酒,便扭头去看窗外。一朵闲云悠然飘过高空,一只鹰徐徐盘旋,经久不动,像是什么人挂在那里的饰物。陈世林不无伤感地想,可惜一个叶家,几代人的艰苦奋斗,现在就要家破人亡了。这就叫世事无常啊。
唉,陈世林又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有一定的需要,眼下我老陈已经是知天命的年纪,想的就是含饴弄孙逸养天年。官做到七品,于人是不满,于己是知足。唯一的遗憾,是膝下无子,几十年官场拼搏,积攒下万贯家财,到头来却成了外姓人的囊中物。当官图的是什么?归根到底是为了子孙后代,他娘的!陈世林叹息一声,又和叶福清碰了一杯。看看痛心疾首的叶福清,陈世林的心理又平衡了几分。他想,有儿子又怎么样?到了手的钱财,还不是要散掉?叶家的铺子、银子、地、牲口将来都要悉数旁落,这时的叶老财主会是什么心情便可想而知了。陈世林知道,这笔财富他也有份儿,而且数目不小。
眼下,这个叶财主已经接近崩溃,这就等于上天替他老陈扫清了发财的障碍。登高不足虑,他正愁找不到买主儿。登科也同样不足虑,他只要现钱,地这玩意儿他还嫌累赘呢。陈世林觉得一切都清楚了,便倒背着手,一脸悠闲地离开了祥记大车店。外面很好,一切都很好。日头晒着街道,风吹着柳枝,石板路面上,几只蚂蚁正在悄然忙碌,几只野狗正在相互追逐,大概是其中某一只正在发情。陈世林感慨地想,狗也和人一样,都是为情所困哪。
得知父亲被何黑子扔在祥记大车店时,登科正在侦办一起私通革命党的案子。案子不大,但油水不小。光是从疑犯家里搜出的金银细软就装了满满三大车。登科事先选派了心腹衙役,把其中一车干货转移到田家庄藏好,剩下的两车拉回府尉衙门,让府尉处置。案子初破,人犯都没审结,大量善后工作没做,登科自是走不开,登科无奈,只好请梁掌柜妥善安置好老父,待他有隙,便回诸城处理相关事宜。
一天忙下来,登科有些累了。他胡乱吃了饭,买了些熟食回到住处。初冬天气,屋里有些冷清,登科抱来柴火,在灶房里生上火。火慢慢地烧旺,照得灶房里通明一片。登科的心情渐渐好起来,他把买来的烧鸡撕开,边吃边喝。酒是凉酒,喝进肚子里很冷,登科有心不喝,却管不住嘴。望着通红的灶火,登科得意地想,这才是我叶登科应该过的日子,有酒有肉,有成车的金银。算算时间,用不到天亮,一车金银细软便到了桂珠儿手上。足足一千五百两黄金,外加一万多龙洋,还有上千两纹银,折成土地,那将是上万亩良田。一桩案子便有如此多的进项,再办上十桩八桩,恐怕桂珠儿那个钱库嫌小了。如果叶家的祖上知道他们的后人叶登科这么能赚钱,一定会羞愧万分。特别是父亲叶福清,从小到大就偏向老大登高,恰恰应了那句话:偏养的儿子不得济。登高不但分文不赚,还把祖上的基业都卖了。时至今日,老爹该醒悟了吧?登科不无得意地想,眼下谁要是在爹面前说登高的好话,一顿臭骂恐怕是免不掉的。哼!
登科又想到了何黑子。这个狗奴才,一声不吭,竟然丢下主人私自跑了。风没吹草没动,就以为叶家要败了,你也太势利了吧?叶家有二少爷在,哪那么容易就败了?要说何黑子,也是叶家的首席奴才,这么多年怎么就没有长进呢?连个形势都看不透,简直就是头蠢猪。行,你不仁别怪我不义,下次碰面时,你要是断了胳膊腿儿,不能说我心狠手辣。
第二天,手下人报告,革命党头目遇罗汉一伙正在开会。登科决定马上动手抓人。
登科跳过面前那堵矮墙,进入那个盯了很久的院落,快步走向后院。这是一个封闭式的四合院,青砖房舍和院墙,靠近窗前,栽着一棵庞大的枣树。时至初冬,枣树上挂着成串的红枣,高阳之下,闪着诱人的赭红。屋内有人在高声说话,登科悄然驻足,听得出,里面的人正在历数满清的罪恶——满清残酷统治下,人民麻木愚昧,粗浅的愚教流行,太平天国即便成功,那种不合时代、社会的宗教思想也很难促使社会发展进步,需要彻底改造。义和团更不用说了,对现代文明抱着敌视的态度。可见蛮族入侵乃至统一对于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破坏作用,历经多年都无法恢复。这不是倒退吗?
登科听完这段话,咬咬牙,又退回到前院。他打开院门,几十个武装捕快持枪冲进来,跟着登科直扑后院。登科踢开屋门,见十几个身穿长衫的男人依次坐在一张很大的条桌前,一个辫子光光的中年男人正站在条桌前慷慨陈词。见登科等人进来,那人厉声喝道,什么人?怎么敢擅闯民宅?想干什么?登科冷笑一声,不无讥讽地说,问完了吗?不等那人回答,登科便沿着条桌,在屋内走了一圈,边走边叫着在座人士的姓名:钱光群、谢永顺、郑旭生、卢杰、栗克夷,还有你……登科走到发言人的面前,大声说,遇罗汉,你这个济南府最大的革命党,啊?都在嘛,不用我费力了,这就叫一网打尽,明白吗?那位叫遇罗汉的男人说,你凭什么说我是革命党?证据呢?登科凑上前,猛然甩出一个耳光,把遇罗汉打倒在地。登科说,娘的,我怎么没说别人是革命党?看你长得丑吗?来呀,都给老子带走。
几十个捕快蜂拥而上,用枪逼住在场的人士。登科说,先生们,只要你们出钱,我保证不再追究你们的谋反责任。
这一天,登科坐镇这个小院落,不时把手下的小捕快派出去催款。到黄昏时,已经有几万个龙洋叮叮当当地堆在脚下。登科按捕快人头,每人分了一百个龙洋,其余的都装进一个樟木箱子里,让人抬到门外的车上。两个心腹捕快并不开口,直接把车赶往田家庄。另一个刀条脸的捕快上前问,剩下的几个乱党怎么处置?登科瞪了他一眼,骂道,猪啊,这还用问?刀条脸唯唯诺诺地退下。没过多久,里面便传出一阵口号声:革命党万岁!打倒满清政府!
登科等刀条脸提着腰刀出来,便冷着脸下令,回衙门。
登科把遇罗汉带到府尉衙门的问事房,马上过堂。登科让人送上茶水和点心,还有味得轩的烧鸡。登科扯下一条鸡腿,大口大口地吃,还客气地招呼遇罗汉,哎,老遇,你也吃,吃吧,到这里,别客气。遇罗汉并不客气,也扯下一条鸡腿吃着。遇罗汉说,要是有酒就好了。登科说,有有有,马上就来。登科吩咐下去,没多久,一瓶汾酒就送进来了。登科给遇罗汉倒上酒,自己也满上,一边和遇罗汉碰杯一边说,想不到你老遇这么爽快,行,对我的脾气。
两个人吃着喝着聊着,完全不像是生死对头,倒像是两个老友把酒言欢。喝光了一瓶汾酒,遇罗汉说,叶大人,你想问话,问吧,趁着我高兴,也许还能透露点儿什么。登科说,这就对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对不?遇罗汉笑了笑,并不言语。登科说,老遇,你把济南府的革命党名单写在一张纸上,你就可以背着手儿,从这里出去了,怎么样?如果想弄一笔钱,也可以,一万以内,我说了就算,怎么样?遇罗汉说,鸡不错,再吃几口。登科满脸赔笑地说,好吃就吃,不要客气。遇罗汉撕下一块胸脯肉,一通狼吞虎咽。登科轻轻地拍着遇罗汉的后背说,慢点儿,慢点儿,我又不和你抢,当心噎着。遇罗汉吃完鸡肉,抹抹嘴角说,要名单是不?拿纸笔来。登科如获至宝,赶紧命人拿来纸笔砚墨。遇罗汉捉笔在手,一通狂草。很快,遇罗汉把笔一扔,又把剩下的半只烧鸡抓起来。登科说,剩鸡就不要吃了,来人哪,再给遇先生送只整鸡进来。
登科抓起那张纸,看都不看就往外跑。他把那份名单拿进知府衙门,双手呈到知府黄曾源面前。黄曾源拿起来一看,脸色登时变了。黄曾源说,这是什么?登科说,这是革命党要员遇罗汉的供词,黄曾源把那张纸往登科面前一拍,怒道,你眼瞎啊,看不出这是什么?登科抓起那张纸,一脸茫然。遇罗汉一手狂草,俨然天书。登科尴尬地抓着头皮说,太爷,狂草我不认识啊。黄曾源气恼地抢回那张纸,指着上面的字迹说,这头一个,就是我黄曾源,第二个,就是你叶登科,怎么,你是抓还是不抓?登科一握拳头,怒道,狗娘养的遇罗汉,敢耍我。登科一边走一边发狠,不让你脱两层皮,我就不是叶登科。
闯进问事房,遇罗汉还在慢条斯理地啃着烧鸡。登科一把打飞了那只鸡,一巴掌拍在遇罗汉的眼角上,遇罗汉惨叫一声,仰面摔倒。遇罗汉捂着眼角,爬起来走到登科面前,微笑着说,叶大人,还有没有新鲜的招数?满清政府的捕快只会打人吗?登科大叫,来人,给他钉上。一个壮汉抄起一把铁锤,把一根手指粗的铁钉钉在遇罗汉的左手心上,遇罗汉脸涨得几乎要裂开,两片嘴唇抖得像鼓面上的浮灰。登科和善地问,遇罗汉,好好想想,你家里人会不会出两万个龙洋来救你?遇罗汉说,不可能了,这些年,为了革命,我父亲、兄弟姐妹都和我划清了界限,现在我大祸临头,没有人来救我。登科说,没关系,那你就等着上菜市口吧,临死前,想吃什么你就跟我说。
到吃晚饭的当口儿,登科让捕快们都出去了,他自个儿坐在遇罗汉面前,饶有兴趣地吃着那半只鸡。登科忽然想到了大哥登高。这个不知死的鬼也是遇罗汉的同志哩,如果有一天,与大哥在此相遇,那该说些什么呢?鸡是要吃的,酒也要喝,可是这刑罚……作为国家的要犯,大哥进来也不可能不用刑,真到那时也确实难办。各为其主,都是倔脾气,自然谁也不会服谁,不会为了信仰让步。唉,难办哪。
登科回到住处,看到井改子来了。登科倒也不惊奇,只是冷冷地问,你来干什么?身上痒痒是不?井改子说,当家的,你屋里没有别人吧?登科不耐烦地说,哪来的别人?登科打开房门,也不让井改子,自个儿一步跨进去。在地桌上摸到火镰,打火点上油灯。登科说,你来看看,到底有没有别人。井改子一边进门一边给自己找台阶下,井改子说,好啦好啦二少爷,叶二哥,你不和我耍混头儿能死啊?登科在灯下看到井改子挺着一张粉团儿似的脸,便不再埋怨了,他把井改子抱到床上,恶狼似的扒衣服。井改子打了登科一下,心里却有些得意地说,几天不见女人,就把你急成这样了?狼似的,还要把人吃了?登科也不说话,把井改子当成布袋,摔过来,又摔过去。井改子刚才还一肚子怨气,被登科一折腾,只剩下快活了。她紧紧地抱着登科,大声地鼓励说,当家的,使劲儿,用力,看你能让我飞上天不成?登科并不答话,只是疯狂地撞击着井改子,很快就把井改子逼进高潮,爹一声娘一声地叫,刺激得登科撞得更猛了。
终于平静了,登科翻身倒在床上,呼呼地喘着粗气。井改子蛇一样缠上来,轻轻地亲吻着登科的胸脯。井改子的气息淡淡的,有些脂粉味道。手指热热的,快速划过胸腹,直接握住了登科的命根儿。轻轻地捏着,像揉搓着一根嫩藕。登科忍不住伸出手,抚弄着井改子的后颈。井改子说,想我没有?登科说,想你干吗?一天忙都忙死了,没那个心情。井改子用力一握,登科便嚎叫起来。井改子说,再没口德,我就废了你,信不?登科赶紧说,信信信,你这个臭娘们儿什么事儿干不出来?井改子还是死死地握着登科的命根儿,冷冷地问,钱呢?登科装聋作哑地说,什么钱?井改子稍一用力,登科赶紧说,有有有,在柜子里锁着呢。井改子翻出钥匙,打开柜子,抓出里面的袋子一倒,几千个龙洋哗啦啦地掉在地上。井改子捧起那些白花花的龙洋,喜形于色地问,当家的,都是咱的吗?登科故作恼怒地说,不是咱的,难道你还要和别人分不成?井改子跳上床,没头没恼地亲着登科。井改子说,好样的登科,不到两个月,你就赚了这么多钱,你可真是我的好男人。登科说,怎么,赚不到钱,就不是你的好男人了?井改子抱着登科撒娇说,嗯,你是我的好男人,没钱也是我的好男人。登科说,明天你拿上钱,给我滚回诸城去。井改子说,为什么?登科眼一瞪,骂道,傻屄,这还用问?我天天抓革命党,保不齐革命党不会派人来杀我,就凭革命党那几头蒜,还拿我没办法,可是,对付你,他们就绰绰有余了,你要是不想死,就听我的话,回去。现在是你死我活,我们不得不防。井改子说,当家的,我真的不想离开你,我不走不行吗?换个住处不行吗?登科说,不行,明天天一亮就走,一刻也不停留。井改子无奈地说,好吧,不过,你今天晚上要好好陪我,弄到见血也不能停。登科说,行行行,我陪你就是。
这一夜,登科竭尽全力与井改子折腾,一直到井改子昏睡过去才作罢。看着熟睡的井改子,登科暗想,这就是命啊,井改子苦苦地爱着一个男人,可是,男人却不爱她,最多把她当成玩物。到了关键时刻,大把大把的龙洋去了别人手上,她只拿个零头儿,可这个傻女人还高兴得要死。井改子其实就是个死人,用不了多久,革命党会杀上门来,那时,替他叶登科死去的人,势必就是井改子。登科想到井改子平日的好,心中忽然有些不落忍,他从床缝里抠出一锭金子,不露痕迹地埋到龙洋堆里,明天,井改子见了金锭,会变得更乖。这样很好,井改子会心甘情愿地离去。让一个女人带着笑容去死,就是男人最大的成功。
最后,登科也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见自个儿已经升至山东省尉衙门道台,手下有数千名捕快,他骑着快马,率众扑向一个村落。那里有一大批革命党人正在集会,其中有很多人都是本省及外省的财主。登科暗喜,命人将院落团团围住,然后开始逐个拿人。可是却奇怪,拿出来一个,是老爹叶福清,再拿出来一个,还是老爹叶福清。登科有些急,都是老爹,找谁要钱呢?登科一急,便骂出来声来。登科说,操他娘的,我哪来的那么多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