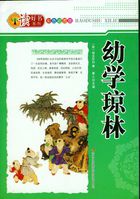三、内卷化视野下的乡村政治关系
村民自治是一种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农村开始了一场新的社会变革,即在农村建立家庭联产承包形式的生产经营责任制。生产方式的改革,使原有的农村三级管理模式不再发挥作用。面对分散的个体农民,治理方式的变迁也相应地凸现出来。如果仅仅采用原有的治理方式,对广大农村社区进行管理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同时,为了改变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迫切需要在政府与农民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于是,村民自治这种新的治理方式应运而生982年,全国人大重新修订宪法时在第111条明确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一)农村政治发展的两种类型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的规定:“乡镇政府对于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乡镇政府不得干预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这实际上表明,乡村之间传统的支配型关系已经不能再进行下去。所谓指导不是领导,就是可以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指点,对它们的工作提出原则性的意见,而不是对日常事务进行干预。所谓支持和帮助就是对村民委员会依法对村庄社区提供的各种公共产品,如举办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维护社会治安、调解民间纠纷、建立和完善生产及生活方面的社会化服务以及宣传法律、法规和国家方针政策,执行村规民约等方面,乡镇政府都要尽量给予实际支持和帮助。处理两者间的关系应该采取协商洽谈的方式。
实际上,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以及权力系统所存在的“压力型体制”,使乡镇干部、村干部乃至农民仍旧被锁定在这种行政主导性极强的行政关系的阴影之下,他们很难适应这种变化。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很难达到法律界定的理想状态。这种不适应主要形成了两种关系:
1.支配型乡村关系
(1)直接干预村委会的民主选举。如滥用职权,不依法办事,干扰和破坏选举工作。不组织民主选举,长期剥夺农民的民主权利,或虽进行选举,一旦当组织意愿与选民结果发生矛盾,强行任命村委会成员;违反法律和法定程序,随意撤换任期未满的村委会主任及其成员,把内定的人任命为“代村长”,不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同意、通过,侵犯农民的罢免权,甚至向外招聘村长。潜江市第四届村委会自1999年9月28日换届选举以来,截至2000年5月1日,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主任,当选后被撤换(含免职、停职、降职、精简、移任他职等)的达187人,占329位村主任的57%。加上其他被撤换的村委会副主任、委员,共有619位村委会成员被撤换。海南省的许多地方已经实行外聘村长;广东省饶平县采取公开招考、择优录取的竞争方式,从1997年的50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中挑选了60人到各管理区办事处担任“村官”997年9月到1998年初,四川省宜宾市采取公开报名、公开答辩、民主测评、择优试用的方法,在近400名报名者中选拔了50名优秀人才,全部异地分配到50个贫困村任职,甚至有的乡镇干部直接去当村长。
(2)派乡镇干部进村直接经手和督办村政。其中又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派工作组进村,实行大兵团作战式的突击行动。另一种是常年性的分片包村,乡镇干部按系统派往各片,由分管系统的政府领导成员兼任片长,有关办公室负责人兼副片长,片上设有办公室,也就是说,乡镇干部都要一身二任,既要做好本职工作,又要负责包村工作,与村干部一起促成各项村政的完成。(3)掌管村委会财政。如建立了“村的乡管”、村会计集中办公,后又建立“双代管”制度。所谓“双代管”,就是村级财务由乡政府管理组织统一代管,既代管资金,又代管账目。村里的收入上交,政府给每个村留有零用钱,花完了报账再领,做到每月一清一结一兑。各村的账务账目集中存放在“双代管”办公室。自治财务完全被乡镇政府管了起来,就等于捆住了村民自治的腿。
这样,乡级政府对村民委员会以“命令”代替“指导”,村民委员会在村级事务中缺乏并丧失了应有的自主性,主要工作在于完成乡镇布置的任务。“指导、支持和帮助”在许多地方变成了命令———服从关系。因此,“加强基层政权”的含义对于乡镇干部来说,往往被认为是恢复农村改制以来基层政权失去了的控制能力及权力。
2.放任型乡村关系。
这种关系正好与支配型乡村关系相反。乡镇政府对村委会放任自流,对其缺乏应有的“指导、支持和帮助”,以至于出现安徽省某县2个村没有选举村委会3年竟然没有人过问的怪事。一方面,一些村委会出现“过度自治”,即力求摆脱乡镇政府管理的倾向。一些村委会在利益的驱使下,往往不愿接受乡镇政府的“指导”;有些村委会干部甚至认为“我是本村群众选举出来的,我只对群众负责”。村民自治就是本村村民的行为不受任何制约,而村委会作为村民的合法代言人和代理人,有权决定自己的内部事务,没有必要接受乡镇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于是,他们对承担的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的职责,抱着消极、冷淡的态度,甚至与乡镇政府明争暗抗。相当多的村民认为自治就是自由,可以随心所欲,连一些本来应尽的公民义务如计划生育、上缴税款、服兵役等也规避履行。另一方面,出现自治权的异化问题。即由“村民”的自治演变为“村民委员会”的自治进而发展到“村委会主任”的自治,一些品行不端、作风恶劣的村干部一旦攫取村委会的权力,便为非作歹,鱼肉村民,侵吞集体资产,成了为害村民的“村霸”或“庄主”。一些村委会长期被宗族或恶势力所把持,村委会陷入瘫痪。乡镇政府不愿趟村里的“浑水”怕“引火烧身”,招惹麻烦。
由于乡镇政府与党委同构,政府是在党委领导下的政府,从某种意义上说,乡镇党委与村民自治关系的紧张,可以等同与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关系的紧张。但它们之间仍旧具有特殊性,即乡镇党委与村民自治的紧张可以表现为村委会与党支部的紧张。在村委会与党支部的关系上有三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村委会越权而党支部无原则退缩。村委会片面强调自治而不要党的领导,认为自己是全村人选举出来的,而支部仅仅由少数党员选举而出,自治就应该由村委会说了算,结果事无巨细一切由村委会说了算。党支部或受其控制,或不敢发挥作用。第二种是党支部越权而村委会退缩。表现为党支部过分强调党的领导,村里一切都要村支部同意,把村级财务管理权完全集中于村支部,或违反法律随意任命村干部,或开除村委会主任的职务。第三种是村委会与党支部处于严重冲突状态,两者都想把自治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造成分庭抗礼的态势。这三种错误倾向都反映和折射出乡镇党委与村民自治关系的紧张。
(二)农村政治关系的法律探源
1.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关系在法律上的漏洞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的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于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这一规定十分明确地从法律文字上揭示了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关系:(1)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不是简单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上对下的行政命令。(2)村委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不是一级行政组织,乡镇政府不能把大量的行政指令强加给村委会。
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实行村民自治之后,乡镇政府和村委会要由”领导”关系变为“指导”关系,但是具体什么是“指导”关系,没有明文规定。“领导”和“指导”的区别在法律上不清楚,概念很模糊,而目前我国又没有相关的处理“乡村关系”的法律文件,因此如何处理乡村关系就要取决于地方干部的认识水平。对于很多乡镇干部来说,传统的指挥命令的办法是最容易的,这就造成了村民自治和传统的政府统一控制的管理模式之间的不一致。
3.村委会和村党支部在法律关系上的模糊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一方面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另一方面又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不久,中央又颁发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明文规定:村党支部“领导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共青团、妇代会、民兵等群众组织”。这些法律漏洞,形成了乡镇、两委各取所需的局面,至于什么是“领导核心作用”、村支部如何“领导”村委会却没有明确提及。这些没有操作性的条文,根本无法调解乡村、两委的利益冲突。
为了解决村两委问题,一些地方开始推行村委会主任、村党支部书记“一肩挑”的做法:要求村支书必须参加村委会主任的竞选,一旦当选,则自然村委会主任、村党支部书记“一肩挑”。一旦落选,如果村委会主任是党员,则由其担任支书;如果是非党员,则发展其为党员再担任村支书。但“一肩挑”却解决不了两委的角色、功能等问题,容易导致两者角色和功能的混同;实施起来造成了只能由党员担任村委会主任,从而剥夺了非党农民、不愿入党农民的被选举权力。这种做法也容易导致乡村关系紧张。
(三)寻求法律的解决途径
乡村政治关系表明:目前适应村民自治和民主的制度建设及法律规范化的程度远远不够,需要进行大量的改革和建设。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法律无疑具有优先地位。建议制定有关法律,用法律条文来具体规范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之间的关系,从而保证村民的真正自治。这个法律应该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一条一条地具体划分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之间在财务和事务上的权力和责任。村级的财务和村级的人事权要明确划归农民自治管理,乡镇不得向农民进行任何在国家法律规定以外的摊派和征收。
(2)要保障乡镇对村级事务的“指导”,使空洞和模糊的“指导”明确具体起来。可以设定由乡镇向各个村派出联络员或助理,帮助村委会进行文书处理、法律协助,处理经济事务等,其目的是沟通与乡镇的联系,但这些人不得干预村庄社区的内部事务。
(3)鉴于乡镇政府对村委会选举干预较多,法律应该明确制定在选举中避免乡镇干预的程序和办法。比较好的办法是规定在县或县以上政府成立常设的选举委员会,根据国家的规定制定适合本地的选举办法,并主持村委会的选举和各种补选、罢免工作。这样可以避免乡镇对选举的直接操纵。在选举期间由选举委员会向各乡镇派出经过培训的选务人员和各乡镇共同组成乡镇一级的选举委员会,监督选举的进行。选举委员会在没有选举、补选和罢免的情况下,可以做调查研究和培训干部的工作。常设的选举委员会也可以帮助乡村逐渐培养起一批懂得选举和了解地方选举情况的干部。这种做法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世界各国的地方选举都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主持的,这样有利于制定一个统一的选举办法,使选举更加公平、公正,而且避免乡、村的人为操纵。
(4)设定规范的村委会成员的罢免程序。有些村委会成员由于本人辞职、生病、刑事问题、工作失误等原因而自动或被动离职,对此要规定一个比较规范的罢免和更新成员的条件和应急程序。
(5)确立社会对政府实行村民自治监督的法律制度。形成一个由人大代表、新闻媒体、专家学者以及农民及各界群众代表组成的对于村民自治和选举的观察监督体制。
(6)从法律上加强对乡镇政府行为的约束,明确规定村委会在哪些方面有权拒绝乡镇政府违法施政的行为。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不受侵犯,促使乡镇政府学会用民主的方式管理、组织农民,建立新型乡村管理体制。
(7)对于乡和村党组织如何领导村委会、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在村级事务中,二者的权力如何划分、怎样进行分工合作,在法律上应把原则性的规定变得细化、规范和完善。
总之,在基层民主已经走过了近20年的今天,从法律的角度反思和梳理乡村的紧张关系,对于完善法律体系,提高民主的质量,建立小康社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四、农村宗族的影响
中国农村社会历来是一个较为松散的、粗放管理的社会,农村宗族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内卷化。在社会转型的历史条件下,沉寂多年的中国农村宗族势力在一些农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苏,对农村社会生活产生了诸多深刻的影响。农村实行改革以来,部分乡村基层组织涣散、社会秩序局部松垮和宗族组织有一定的联系,从历史进程和法制建设的角度看,宗族势力代表了一种落后的社会力量,它有其危害性,从这一点上讲,农村宗族确实加深了农村社会的内卷化。
(一)宗族的概念及其扩散
传统意义上的宗族,是指农村中按男性血缘世系聚族而居及按宗法规范结合而形成的特殊社会组织,其内部是按血缘辈分划分等级,族长可以利用强制遵守的族规对宗族内成员进行控制。
宗族本来是一个相对固定的概念,随着社会发展,其内涵开始隐性地出现一些变化。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宗族组织曾经历过上古宗法制,中古重视族望的宗族制和宋元以降“敬宗收族”的宗族制等主要发展阶段。在发展过程中,“家国同理同构”的社会关系模式曾使宗族成为社会基本的构成单位,而宗族式的互惠互助关系则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的主要特征。到了明清时期,宗族的平民化使宗族成为乡村地方自治的基础和前提、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必经中介。但对于遇事从权的中国人来说,制度规定与具体运作之间存在着充满玄机的解释空间,男性血缘世系经常为一些特殊因素(如男性人赘、养子承继、寡妇招夫等等)所扰乱,始终保持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而且家族人口的繁衍和迁徙所促成的宗族分化也时有发生。这种宗族扩散是非常缓慢的,甚至是昙花一现。